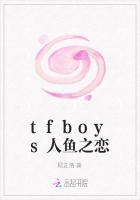那一晚回来,我们瘫坐在沙发上,试图卸下身心里隐形的物质,那些痛苦拉紧着神经与时间。命运把这个男人带到我身边,我要陪他一起忍受种种没法说清楚讲明白的尴尬与屈辱。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生的些许意义,内心涨满从卑微苍凉里生出的爱。那种爱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让人承受与坚守。我们抱在一起,像两个流浪的孩子,瘦骨嶙峋,眼睛湿漉漉地流出许多茫然和谅解。荒凉的原野与我们一臂之隔。我们拼命把自己向对方的身体里挤去,从每个毛孔彼此流入。像两张拼图在寻找自己镶嵌的位置。我似乎在他的眼眶里看到了前世的自己,为了这样的男子从蛰伏到燃烧的模样。
“家明,为什么此刻看着你被时间磨损的背影我的内心会不断颤抖呢?我们过去的爱,是散落了吗?为什么要对这个世界臣服?”我俯下头低低地说着。爱情在这沉默里是这么无足轻重。
今晚的家明,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脑中闪现的记忆,太疼了,与他现在的距离太疼了,我感到自己的骨头正撞在冰冷的墙壁上。他低头,泛青的面颊越来越看不到轮廓,身上的苏打水味道愈加浓郁起来,夹在手指间的香烟快烧到指头了,而他还一动不动地低头。我靠着门,也是一动不动。时间是什么呢,当一切都毁坏殆尽,我们还要计算什么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和这个小男人僵持多久。世界对他全是误解,他为什么还要费尽力气去解释,去实现那些飘在风中的遥远?我站在他的背后,始终没有再向他走近,在昏暗里不想看到一个男人一副被人戳穿的表情。
我转过身,又轻轻向自己的卧室走去。
白昼大把的阳光砸在周六十一点的刻度上,棕黄色的窗帘色彩被调得明快许多,浴室里脱水桶急速运转了一会儿又停下。我从没想过自己有天会睡得这么晚,就像自己没醒过一样。
我起身拉开了窗帘,明晃的光线猝不及防地进入卧室。我探头出去,家明正在隔壁的阳台上晒他昨天泡在桶里的上衣和内裤,神情落寞得像一只骆驼。那些甩落的水滴很轻地敲打在兰草和芦荟上,时光不断绿着。刚想开口叫他,脑子里突然又塞满了昨天早上不欢的场景,那些从枕头里飘扬而出的羽绒封住了喉咙。我感觉身体一下子又变得晕晕沉沉,昨天真像场噩梦,我敲着脑壳,试图删除那些图像,它们却亢奋地逼过来。凝固在树梢的阴影全洒了出来。
“筱鱼,我们年内就贷款买房吧。”我当时正从卧室的衣橱里取出上班要穿的制服,家明就在客厅里一边看着早间新闻一边说。
我慢慢拿出套在衣服里的架子:“再等些时候吧。家明,你不必太在意我妈的话。”
“可是,我……”他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往杯里倒着,“筱鱼,我想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明天是我们……”
“家明!”我打断了他,“我们还年轻,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不急的。”
“我答应过妈的。”他放下手中的牛奶瓶,走到我的卧室,很认真地看着我。
“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再提她!”心口不知哪儿冒出的一团火要把整个人点着,我顺手抽出床上的枕头向这个傻男人扔去。那么轻薄的物体顷刻间破了,绒毛纷纷扬扬。整个清晨似乎还陷在浓雾未散的阴暗里。
他哑然站了许久。我揉了揉额头,让自己静下来。他稍后缓了过来,一字一顿地对我说:“筱鱼,你变了。”
“变的是你!何家明,你已经跟从前我在‘蔚蓝水系’里认识的那个男人不一样了!”我气急地说,“现在的你就像一个挣扎在房子、工作和婚姻旋涡里的奴隶,我真的不愿你是这个样子。”
“筱鱼,我只是想更好地爱你,知道吗?”他走过来,伸出左手想抚摸我的脸颊,被我用力地甩开。
我沉默地看了他一眼,便冷冷地把制服放进袋里,连着挎包提出了卧室。
他跟了出来,从鞋架旁拿了把伞向我递来。“天气预报上说今天还会有雨,你带上这个吧。”
我没有理他,直接开门走了出去,并且把门重重甩了过去。整个房子的心脏似乎在那一刻跳了出来。
“家明,其实变的不是你,而是我们。”家明晒完衣服从阳台离开,我的内心突然感伤起来,这个小男人,我让他平白无故地咽了不少苦。
出了卧室,我来到了客厅,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自己爱吃的菜肴。家明坐在位子上用一只手捂着上衣口袋正等着我。不知不觉已经认识五周年了,真的好快呀,我坐在对面细细瞅着家明,发觉这个小男人也渐渐成熟了。他今天穿着很正式的西服,打着领带,嘴边的胡茬刮得很干净。在他旁边摆着一束很艳的红玫瑰。
我看着他的脸,脑中溃烂的伤口逐渐愈合。清晨如海滩一样吹来了清风,我的目光中汹涌着很深的歉意。
他此时并不看我,只是朝着我的座位呆呆望着,然后从身边抽出那一大束玫瑰花轻轻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想叫他的时候,他又从紧按着的上衣口袋里拿出精致的红色小盒,是那个我曾期许过无数次的爱的认证。他慢慢地开启那个心形的小盒子,向我递来。这个小男人哭了,泛红的眼眶向桌面滚落下一颗颗很重的液体。我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悲伤。“筱鱼,筱鱼!”他放下戒指盒的那一刻不断嘶喊着我的名字,但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难以逾越戒指以外的地方。
似乎所有的光线顷刻间全都聚集在那颗镶着小粒水晶的戒指上,那样明亮的光线,璀璨得一生仿佛只有一次。
我高兴地看着,神经却一瞬间紧绷起来,一束光牵引着我向最后的谜底靠近……
昨天傍晚下班时,天空真的又下起了这个夏末蜇人的雨水。我用挎包遮住头顶,跑到停靠站。公交车送走了一拨人,后面不知又从哪涌上一拨人,拥挤地塞满了车厢。密集的人群真是城市的罪恶。便利店的老板娘懒洋洋地靠在自家冰柜上看着大雨滂沱落下,一只拖鞋在台阶下面翻转了过来,她用肥硕的右脚搔着左腿的小腿肚,神情木讷。卖水果的小贩在货摊上加固着大伞,一摊脏水若无其事地向他脚边蔓延着。远处煎饼店的香味来势汹汹,招揽了不少在街道上空腹避雨的客人。那些撑开的小花伞单调地开着,颜色总是那么几种。这个时节的雨天潮湿而焦躁,我很不喜欢。
包里的手机动弹了一下,打开,是家明发来的短信:“筱鱼,下班后,我来接你吧,我们再去‘蔚蓝水系’,去找回过去的我们。”因骨子里自小养成的执拗,我在早上燃起的火焰到现在也还没浇灭,只是视线再次落到“蔚蓝水系”四个字上时,内心固执的城墙瞬间塌了下来。
一辆闪着空车灯的出租车这时缓缓地开来,我顺手把它拦了下来,湿漉漉地钻了进去。司机似乎今天心情也不太好,车子在雨中滑行得很快,像极了自己疾驰的情绪。很快,车子从立交桥下穿过,很快,又开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很快,就要向前面的环岛驶去。我从包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打着:“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已经打出租车准备回去了。家明,我想我们还能找回自己,只要时间慢点改变我们。”
看着短信发出的图标消失的瞬间,耳朵里突然“轰”地一响,一种嗡嗡声不断盘旋在脑中。那声音似乎尖锐地要撕开身体,仿佛一双无形的大手正用力撕烂世界,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所能感觉到的是自己此刻成了一枚殷红的果实,泡在深不可测的雨水里。一束束灯光剧烈破碎着,射向我,锋利如刀。从前的影像混杂着家明的脸不断闪现,重叠,又分开,那么强烈而眩晕的痛感,清晰,尖利,又渐渐模糊。我想大声嘶喊,却始终发不出一丝声响。
夜色吞没了世界最后一道微亮的光线。无边而冰冷的城市,尘埃飞扬。
我落魄地回到住所,从挎包里取出钥匙开了门,此时身体只剩下疲倦。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透明的鱼正向家明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