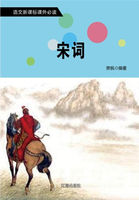我们学校宿舍楼就在兰博基尼旗舰店上头,每晚我和维兰蹲在兰博门口的台阶上撸串时,背后一面玻璃之隔是兰博基尼概念款新车,身前十余米处停着一排旧款,再往前二十米处,或者往上看二十米,延安高架上下总会不时看到那些驾驶着拆了消音器的超跑,轰隆隆一路超车的飞车户。
“你坐在车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蹲在台阶上撸串,看你开着法拉利来买兰博基尼。”
“车在远处,你猜里面是个女司机。车靠近了,你暗自揣测漂亮女生的另一边是她干爹。车门开了,你发现一年方二十的高帅富在你面前打开了车门,接过女生怀里的baby,叫了声老婆。从头输到尾的你,只能恨恨地说一声,车真丑。”
这样的段子总能收获无数挥手说再见的表情。据说卖烧烤的马哥已经开着路虎、开了第三家窝窝头(副业)分店—据说不知真假,反正我四级还没过。流泪说再见。
“唉,还是我家大郎好。”维兰扒拉扒拉烧烤盘,翻出最后一串鸡皮,就着最后一点儿啤酒泡沫,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去了。
大郎是她男朋友时川的旧摩托,全名龟元大郎。
刚考来上海的时候维兰和时川经常吵架,维兰天天问时川成绩如何blabla,一言不合就吵个天翻地覆。维兰说,高考了还以为数学是考两个半小时,现在复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月考,问你你还骂我,傻×吧你。
维兰关了手机,穿着高跟鞋就往外滩跑。音信全无。五个小时后开机,时川打进来,维兰绷了半天没绷住,哭着说脚后跟磨破了,地铁关门了,自己迷路了。十里洋场的旧灯光,熟悉的景致各有各的美,陌生的道路却总是相似的。
时川哽咽了半天,压着喉咙说,你说你是不是傻×。
维兰又开始号啕大哭。时川最怕这一招,老老实实听维兰又骂又哭诉地说了自己半小时,不知道怎么哄,只会嗯嗯啊啊,最后保持沉默。维兰说,你说话啊。时川又是沉默好一会儿,然后慢慢道:“对不起啊,我没法骑着大郎去接你了。”
最后还是我接回来的。
我于是成为这场异地恋的调剂品。时川听说过我们逛街打车打半小时、堵车堵半小时后,用充满不屑的口气说,真磨叽,想当初我骑着大郎,城东城西四十分钟嗖嗖的。
对此维兰不置可否,只是说,拆了消音器的大郎轰隆轰隆的引擎声的确比路上的超跑响多了。
时川和维兰是同一高中、同一年级。高二维兰过生日的时候,时川问她想要什么,维兰说想吃中山蛋筒。那天正好城西区停电,找了几家小卖部蛋筒都融成半截了,时川顶着38摄氏度高温直接扭到最高码往城东开,往那边找,结果还是没赶在上晚自习前回来,时川开着大郎就进了学校。就跟所有的叛逆少年一样,时川早把大郎的消音器给卸了,引擎一开震天的轰隆声,直开到教学楼下。维兰的教室在一楼,真是全年级震动,维兰的班主任还在上着物理,几个胆大的都已经站起来看了。那天黄昏是所有青春都有的黄昏,火烧云的背景和绿茵茵的操场,天将暗未暗,鸟儿低叫着飞回巢,路灯刚刚亮起。时川把帽子一摘,扒拉着头发,一身依然是白衬衫牛仔裤,邪魅地笑了下,然后像送货似的,把一个冷冻箱从后座卸了下来,“砰”的一声放地上,大喊一声“维兰,生日快乐”。时川往后瞟一眼,操着地方口音大喊别跑的保卫叔叔还远远追着,“大郎跑啊,大郎。”时川拍拍车屁股,吹着口哨绝尘而去。全班哄叫,被班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拖堂拖了一个小时,下课又拎着维兰教育不休。维兰气得满眼泪花,好不容易出教学楼门口,眼泪汪汪地踹了冷冻箱两脚。一打开,一箱融得半截不剩的中山蛋筒,乳白色的奶糊上漂浮着还没融尽的巧克力,升腾出来的冰气在路灯下发光。
毕竟时川家里是副校长的亲戚,最后背了个处分。
那一定是时川最好的时光,摩托车后头坐着自己最心爱的姑娘,吹的牛逼、许的诺言不需要见到就能闪光。
哪怕日后开着兰博基尼,都不会忘记摩托车上构建过的未来。那时候你拥有一切。
如今几年后的维兰,跟的士司机争执着是否绕路,被听不懂的上海话气哭,打开车门却再也看不到冷冻箱。如今的维兰,在陌生的城市里拦车、坐地铁、穿着高跟鞋奔跑,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让她奔向她的英语课、第二外语课、兼职地点,而曾经驾驶着大郎风驰电掣的时川却关在高复的课堂里寸步难行。
高中的时候老师想过千百个方法拆散他们。两个人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手都搞得轰轰烈烈跟偶像剧似的,影响实在太恶劣了。有次闹分手时还是冬天,两人都绷了一个星期,谁也不理谁。时川闷不吭声的,某个中午推了维兰到球场踩出巨大的“WL,sorry”。球鞋进了雪迈不动步子,他就把鞋子脱了,光脚踩完,和好后直接进了医务室。这事闹得校园情侣争相效仿,谈恋爱闹分手求复合个个都跑到足球场,那场子踩得,第二年开春草全死透了,球场寸草不生。
老师想方设法棒打鸳鸯,但两人闹分手闹得也太频了,都不知道从何下手,看都看累了,拆来拆去拆到了高三。老师罢手了。
这招最狠,无招胜有招。高二高三分手都是玩儿,高三才遍地是早恋的坟墓。两个人成绩差距大,维兰是出了名的勤奋,高中时秉承着闻名全年级的十二个小时法则,一天一定学习满十二个小时,勤勤恳恳地吊在尖子班。而时川是个在高中混日子的二世祖,哪怕维兰为他补过再多的课抄再多的笔记,成绩永远不及维兰的五分之一。
但时川不在乎,时川从没想过上大学,或者说,考哪儿去哪儿都行。他妈妈是全市闻名的煤老板,他以后也是小煤老板。煤矿生意,有资源、懂人情就足够了。维兰恳求地看着他说:“真的不需要好一点的学历吗?”时川无奈地看着她:“真的不需要。”
时川就是提不起学习的兴趣。他说:“你是不是嫌弃我配不上你?”维兰说不是,他说:“那你觉得我养不了你?”维兰不说话。两个人吵架吵到绝望。你都不能想象高三的情侣吵架吵得多绝望,未来无法掌控带来的茫然和惶恐,让人在忙成机器的时间罅隙里,稍微想到一丁点儿都要战战兢兢。维兰的高中每年都有手牵手走向阳台的情侣。
心灰意冷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时川载着维兰时从高架的长坡上翻了车,维兰一骨碌翻下来,从小腿到大腿划了长长的一道口子。缝针的时候时川就在门外,维兰说算了,真的彻底算了,不要再见了。时川在门外大喊大叫,你不开门我就把车给砸了。维兰撇开头忍着泪,憋着不说话,闻到烧焦的味道也不敢回头看,医生叹息说:“小姑娘,不要怕。”一针一针地穿。维兰说,打了麻药是这样的,皮还是你的皮,你能听得到针穿过皮肤的声音,刺啦刺啦,线穿过皮肤的摩擦感,可是你不痛,就像你失去了痛觉。她咬着书包带一直在淌眼泪,不敢看自己的腿。
她醒来的时候,眼睛肿成桃了,有人坐在床边椅子上。她意识模糊地又涌出眼泪来,哑着嗓子说:“嘴巴苦。”那人翻窗户出去,她心忽然就沉了下去。然后眼睛一点一点清晰了,看到了光、看到了房间,守着沉甸甸的心看着那人翻窗户回来,靠近,坐着,低下头,高鼻深目,不笑—时川把剥好的冒着冷气的中山蛋筒递过来。就像意料之中的那样。维兰很疲惫,问:“你把大郎砸了吗?”
为这一句话,时川硬是送大郎去修—修大郎的钱都够买二郎三郎了。我曾经多次看着维兰在穿上长裤前抚摸那条长长的疤痕,清晰,深刻,有突起。深的部分还是深褐色,膝盖以下的线条是深粉色。因为这个,拆线时,时川几乎是跪在她床前承诺愿意为了她考出家乡,考个大学,之后还在维兰父母面前又跪了一次。遇到她之前,他从没想到爱。遇到她之前,他从没想过把自己轻松的生活推向未知和痛苦。
结果那年高考,维兰填报了艺校,时川选择了复读。他说:“为了你,我考去上海吧。不做小煤老板的话,我要怎么养活你呢。”维兰说你确定吗,时川狠狠心,把大郎的钥匙给了她。维兰说:“好,我帮你记着,在上海等你。”
老师们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结局。
刚开始,时川总是很迫切地想和维兰见面。他总是要求维兰稍有空闲就回来陪他,不然他就翘课、就不吃饭、就砸车。于是维兰一次次回来,聊起大学、聊起新的生活—那你呢。
时川又不愿意维兰回来了。他们还能说什么呢,打电话、见面他们能说什么呢—过去的同学现在怎样怎样了?不,时川会有压力;你成绩怎么样了,模拟考什么时候?不,时川会有压力;我现在去哪儿兼职,我报了什么什么社团?不,时川会有压力。
维兰从此变成了时钟,一切都围绕着时川转动。刚开始时她患上了强迫症一样每天无数个电话,问时川的成绩、问他的复习计划,多次吵架之后,她变得患得患失,小心翼翼—说自己在食堂吃了什么,体育课跑了几圈。其实她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说,但她仍要维系着这流水账的交流。
久而久之,时川就受不了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当初摩托车后头那个吃冰激凌的姑娘是怎么变成比他妈妈还啰唆的人的。他们当初,冒着大风大雨骑着大郎穿越半个城市只为吃一条烤鱼,偷偷翘课去看演唱会,熬夜一起看世界杯,有说不完的港剧美剧英剧动漫要一起追,有一抽屉的课外书等着交换。
当初爱到恨不得把自己的冰箱、MP3、影碟、相册全部送给对方,拼命填补那些相遇之前的空白,如今抽根烟、逛个街都要隐瞒。
和大多数迈入大学的高中情侣一样,他们没有熬过第一个学期。
刚认识他俩时,有次吵架后,维兰说,我真担心他为我做这个决定,会让他恨我。高中的时候,他俩不知道第多少次分手时,维兰不想理他,说快要熄灯了要回寝室睡觉了,时川指着一溜的灯光,说,你要是不和我好了,我把这一学校路灯都给你砸了。然后时川一连砸了十六盏。学校罚他自己装回去,维兰默不作声地在下面给他扶梯子。他旋着灯泡,天黑了,灯泡一盏盏照亮脸,时川最好看的就是侧面,高鼻深目。他看着慢慢发亮的灯泡,说:“哪天你要是真不和我好了,我把整个学校的灯都卸了,全给你。”
分手前,维兰做了个梦,梦里时川真的把一个学校的灯泡都卸了下来,给她。但天太黑了,灯卸下来后,他却找不到她了。他们听到彼此的声音,却找不到对方。
维兰浑身发凉地打电话给时川,时川接电话,问:“你又怎么了?”声音很疲惫。
维兰提出分手。
她早就听说,高复那儿有学生跳了楼,时川的妈妈也早就打电话,说时川每天睡不了两个小时,做不出题时已经开始拿着裁纸刀往自己胳膊上划血道子了,求她放过他。
时川不同意,说别闹了,分手了我还读什么,一个劲儿求维兰回来好好说。维兰咬定了分手。时川说:“那你把大郎的钥匙还给我。”维兰说:“扔了。”第二天时川就砸了大郎,图片转得满微博都是。
你等着,时川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两个人没有说话,断了联系。但维兰的计时已经成了习惯。
维兰偷偷回去过一次,趁着小长假,围着围巾、戴着口罩,摸着学校四周的栅栏摸了一圈,好像时川随时会像高一一样,把书包一扔,一手托着维兰一手攀着跳下来,开着大郎轰隆隆地离去。她一根根摸着栅栏,摸到手也凉透了,走到夕阳西斜,终究什么也没有。
时川最后没有考到上海,而是去了北方。
时川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维兰已经学会了抽烟。上海下了第一场雪,圣诞节。她说,就像缝针时知道时川会翻窗进来一样,她知道时川会找她。维兰留下了这一天的时间,坐在兰博基尼门口抽烟,看着面前车来车往,等。时川的电话晚上来了,整个人说话都和以往不再一样,像是淬过火一样。他说:“我是时川。”时妈妈给他在老家包了一层的五星级酒店庆生,大厅里觥筹交错,中年亲戚在包房里搓着麻将,露台上亲戚的孩子放着烟火。他走出来,可以看到江景,河堤边一溜的小灯。
两人沉默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可能两个人都在流泪。电话里说话都有沙沙声。
时川说:“你那儿下雪了吗。”
“嗯。”
“我这儿昨夜下冰雹了。”
“嗯?”
“维兰,”时川轻轻地说,“我脚心疼。”
是啦,是那次下鹅毛大雪、他光脚踩出她名字的冬天,送到医务处时校医眉头都拧起来了,说恐怕要生冻疮,这样一来,年年都要脚心疼了。果然第二天时川的脚就疼了起来,到春天了还打不了球,维兰天天帮他涂药油。维兰叹口气说:“以后可麻烦了。”
时川在电话那头笑,说:“我当时心里可高兴了,想,那你年年都要在我身边了。”
维兰抹抹泪,说:“钥匙我没扔,可惜你车已经砸了。”
“你等等!你等等!”时川叫起来,隔着电话,我都听到了时川七姑六婆的叫喊声:时川你去哪儿.。
两分钟后,坐在维兰身边的我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响彻云天的轰隆声—果然很响。
“虽然没有大郎了,但我后来拿还没砸坏的零件拼出了一个龟元小次郎。嘿嘿。”
我听出了时川的哭腔。
他说:“你要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