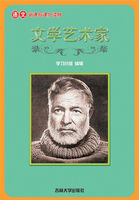1.
她养了一只白猫,头顶趴着黑蝴蝶。
她裸露着左肩上花纹繁复的鳞翅目,拿着一本黄历念得有板有眼。
“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2.
和所有失恋症候群的人一样,阿希闭门不出已有大半个月了,除了定期上门打扫的钟点工外,只有我时不时地去看看她有没有发霉变质。
夏至过后,整个夏季濒临鼎盛,几日不见雨水,空气干燥得好像一碰便会裂成碎片。阿希打电话给我,说家里冰箱坏了,好多没有到保质期的食物,都因为存放不妥而变质了。
就连爱情也是。全怪这天气,惹人心浮气躁。
她在电话中简略地向我讲述了这件事,语气平淡得好像这只是某一个跌宕起伏的电视剧情节般发生在别人身上。最后还不忘吩咐我带一盒冰激凌过去,外面天气太热,她懒得出门。我望着胳膊上被晒出的黑白分明的痕迹,明知作用不大却还是擦了厚厚一层从网上淘来的真假莫辨的防晒霜。
楼下的月季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出了一头不止,开败了的花零散地挂在枝头上。自从住宅小区的物业因为经费纠纷搬走之后,花圃和草坪就再也没有人打理过了。枝杈疯长的景观树和茂密的杂草滋生了不少蚊虫,顺着没关紧的窗户或者纱网的漏洞钻进房间。夜里总能听见若有若无的嗡嗡声盘旋在自己头顶,即使用被子把自己裹得大汗淋漓,也免不了露出的手和脚被叮咬得痒痛难忍。所以每晚睡之前我总是会喷大量标有“微毒”警告的驱蚊花露水,可收效却甚微,连日下来嗓子里像放了红炭,喝水都觉得疼。阿希在电话中嘲笑我,说别没灭了蚊子先把自己给毒死了。
托她失恋的福,我们又能像以前一样,花一整天时间在一起满嘴跑火车地瞎侃,从邻班某个男生的风流韵事,扯到时尚杂志里又推荐了哪些化妆品。一直到说完了所有的话题再无话可说,便坐在一起画画,直到天黑。自从阿希谈恋爱之后,这些时间大多数分给了男朋友,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放假,我总是自觉地找借口推托三人一起的活动。我想这是我对她的体谅,不想也不懂如何做一盏瓦数超大的灯泡。偶尔她夜里打电话给我,也是说和男朋友闹了别扭一直处在谁也不愿意率先开口的冷战状态。阿希的男朋友换了好几任,吵架的借口也无非是那几个,再没什么新鲜的花样。每次听得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就让她不要多想,过些日子自然会好起来。她也就应承下来,互道晚安,也许她并不需要安慰,只是想找个人倾倒一下苦水。
我和阿希的关系就这样不咸不淡。既不是推心置腹的闺密,也不是表面应承的同学。彼此都因为一些不可或缺的琐事被需要着,虽然没有足够的分量,但缺少了就会因为那份空洞感而产生不安。
3.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阿希家所在的小区了,但徒步进入的方式始终让门卫将我和来做清洁卫生的钟点工混为一谈。说来也不奇怪,在这里看着价值不菲的名车进进出出,耳濡目染,穿着普通的人自然就显得可疑起来。他审视的目光总让我心虚,好像我才是真正心怀鬼胎的人。
“请出示证件。”每一次他懒散地说这句话的时候,都会附加一脸睥睨的神态。而这一次,他是对着我身后的人说的。我回过头去,一个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绑着黄金流苏的大红色木盒,显然是来送礼的。
“你是来找谁的?经过同意了吗?”
“打电话联系过了……喏,这是名片。”中年男人诚惶诚恐地掏出一张卡片来。显然上面的职位并没有多么了不起,门卫只是看了一眼,没有接下。
“身份证押这儿,或者驾驶证也可以,出来的时候取。”
“哦,还查得这么紧啊,又不是什么坏人……”中年男人可能觉得受了侮辱,迟迟不愿意将证件拿出来。相比之下,我总是忙不迭地把学生证扔给他,然后快步离开。就怕他将我和那些攀炎附势的人归为一类。中年男人又争辩了几句,最终还是妥协了,拿出钱夹里的证件递给了门卫,然后小声咕哝着“狗眼看人”之类的话。他从我身边经过,越往前走背驼得越厉害,好像已经做好了随时点头哈腰的准备。
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却不知道为什么。
阿希开门的时候还是吓了我一跳,见惯了她化妆的样子,反而不适应她素面朝天。我像打量陌生人一样看她,她却一点也不见外,接过我手中的炒面,就去厨房拿筷子。我看着满地板扔的画纸和衣服,还有垃圾桶里溢出来的纸杯,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过了。
“钟点工没来?”
“没,心情不好不想叫她来,看见我这副样子又要跟我妈告状了……这面怎么没味儿啊……”她吸溜着面条,含混不清地跟我说。
“你这两天要忌口,我就叫他别放辣椒和香菜。”我心疼地看着那些五块钱一张的水粉纸被她踩在脚下,一边捡着还没遭殃的纸,一边数落她,“你真是自作孽找罪受,要去文身干什么,又不是打耳洞那么简单,感染了怎么办……还庸俗地文个蝴蝶,你就不能更有品位一点吗……”
“怎么几天没见就变得这么啰唆了,瞧你那点出息,疼的人又不是你。再庸俗这图样也是你画出来的,我喜欢就行。”她的头发凌乱地盘在脑后,袖子也脱下来一边,露出半个肩膀来。她半个月之前文的图案因为细节复杂还在脱痂中,看起来像是一只灰扑扑的大蛾子。
那是一只黑斑伞弄蝶,事实上,大多数弄蝶并不比蛾子好看到哪里去。
4.
诚然,我和阿希都是一所普通美院的学生。
所谓“普通”这两字,就是指学校聘请的老师既不是艺术家协会大名鼎鼎的教授,历届学生中也从没出过风光的新秀。而在这里的学生也不见得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喜欢画画的。除了一部分家境优越完全不用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只想填补人生必经之路的人之外,就是成绩实在无可救药又碍于面子不想去上大专的人,凭借“艺术生”的身份和本科搭个边儿。
我和阿希的区别就是她是前者,而我是后者。如同她能将法国巴黎的进口颜料闲置到晒干,我却只买得起超市货架上几块钱一盒的水粉还要用得小心翼翼。
和模特、播音之类的艺术生不同,他们的家长总是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别人:“我家孩子去参加了某某选秀上了电视,或者给某某杂志拍过平面”。而我的父母却耻于承认我迄今为止努力做到的,“给言情小说作过插图”这样的话不管怎么说都显得毫无底气,一点值得夸赞的成分都没有,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总是一致对外地搪塞过去。后来对此我也羞于启齿,画画成了我的痛处,一旦戳中就痛不欲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我做了走到这一步的选择,现在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或许是我强迫自己要忘掉它,一遍遍地擦去脑海中的细节让它变得模糊不清,不要再用残留的尖角刺伤人心。
很久以前,他逆光站在走廊里,午后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他的眉目就在阴影中和心里珍藏的每一幅画面都重合了起来。心跳、脉搏、呼吸,就连穿过袖口的风都欢欣雀跃。我为这场面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多想把他留在画纸上,让这一刻的时钟永远不要走动。
我心中澎湃踊跃的悸动呼之欲出,他口中的利剑也迎面而来。
“别做这些没有意义的正经事了,好好努力看书吧。”他说这话时的笑容到底是友好还是怜悯,像一枚轻飘飘的柳叶针,一下子就泄了我的气。然后转盘上的指针加速,日光也冷却了下来,他还是站在我面前,手里捏着一半被我当作素描本的笔记本,笑意盈盈。那一瞬间我只是觉得冷,发自肺腑的,好像一腔热血都流逝了,只剩下被渐渐冰冻起来的躯壳。
“如果你也不能理解我的话,”我在内心挣扎,“我凭什么捆绑你的心,要你承认我哗众取宠讨你欢心的伎俩。”
“没错。什么也依凭不了。你只不过是我喜欢的人罢了。”那时候觉得,再也没有比获得自己重视的人的肯定更重要的事情了。直到所有的羡慕都化为怨恨,笔下柔和的线条都成了刚毅冰冷的棱角。唯一没有随着命运流失掉的,就剩下手中的画笔了。
不,还有一样没有变的。
越过我头顶的目光,它带着和我如出一辙的炙热,落在了我身后的阿希身上。
5.
大概是高三末尾,闲暇时间我会和阿希坐在操场上看着低年级的学生打羽毛球或是跳绳。这种闲暇无非就是逃了没有老师监考的随堂测验,或是压根听不懂的地理课。临近毕业的夏天里班主任彻底地将我和阿希放弃了,再怎么努力也毫无起色的成绩只会拖升学率的后腿,索性将我和她调至教室最末的位置。那里有和我们一样的人,上课睡觉聊天玩手机。别人都在埋头抄笔记,我们却闲得无所事事。但只要侧过头去,就能从后门看到对面的教室,刚好斜对着他的位置,能看到他垂着眼、专注认真的侧脸。
就是那时喜欢上他的吧,猛然暗生的情愫蠢蠢欲动。而他也会偶尔回过头来朝这边张望,久久地注视着,直到我尴尬地撤回视线。也是从那时开始会错意了吧,我的近视让我不能捕捉到他目光的焦点,天真地以为他看的是自己而不是坐在不远处的阿希。
不过也没有关系,总能通过某种方式被联系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跟阿希很少再说到关于他的话题的时候,这份目的不纯的情谊已经变得难舍难分。
阿希从来只穿各式各样的高跟鞋,衬得她的双腿更加修长。她也总是怂恿我买相同的款式,我便去网上买仿真度较高的来穿,虽然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但舒适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忘了多少次脚上被磨出血泡,贴着许多创可贴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有时候恨不得脱了鞋子提在手上,就像用鱼尾换了双腿的小美人鱼一样,每一步都踩在利刃上。后来时间久了起了茧子,就再也没有那样疼过。
她坐在双杠上的时候总喜欢把鞋子甩在地上,我学她的样子赤脚在空中晃荡。我总是出神地看着远处更加年轻的姑娘们,她们梳着马尾,露出额头,一脸素净的模样。穿着简单的运动装和白色的慢跑鞋,用长裤把腿遮得严严实实。
我低下头看我和阿希的脚,因为经常穿高跟鞋而有些拇指外翻的迹象。这是所有爱美女人的通病,如同一个不可磨灭的标志一样。我说不清它代表了什么,但就是和那些女孩子不一样。既不是与众不同的骄傲,也不是无法回到过去的叹惋,而是一道分水岭,将我推向了逆反期。
阿希就是一个更加标新立异的旗帜,带着我张牙舞爪。她打耳洞、染头发、化妆,她做一切我曾经不敢做的事情,我便见样学样地模仿,我以为只要能够成为她,就能获得她所拥有的。
但是也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天赋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到的,比如她的美貌和高傲。亦如她用再好的画笔也不能像我一样流畅地绘制线条。
“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阿希。
她的脸上泛起了两坨红晕,然后轻盈地跳下双杠,背对着我。
“张少华。”像港剧里面的名字一样,我想就是他没错了。阿希用鞋尖蹭着地上的沙土,我看到一块漆皮被磨掉了。
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6.
我很少看见阿希露出疲态。仅有的几次是她一个人蹲在台阶上面抽烟,见我来了就把烟在地上摁灭,然后大笑着调侃我说:“你怎么穿着校服裤子来了,一会儿见我朋友多丢人哪。”由于总是阿希埋单,一切娱乐活动的安排我都对她言听计从。我这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从黄昏那一刻开始的。
夕阳坠落,华灯初上。斑斓的霓虹渐次亮起和流动的车灯交相辉映。摊贩们陆续在街边摆出形形色色的商品。能用很便宜的价格淘到好看的衣服和耳针,还有各式精致的小夜灯。运气好的话还能遇上贩卖蝴蝶标本的人,还可以买到用木框镶起来的大翅凤蝶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