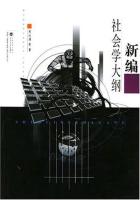(2004年2月20日)
陆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一直非常怀念我们这位老同学、老战友。
我和陆平同志都是1934年进北大的,他在文学院,我在理学院,他住东斋,我住西斋,本来无缘相识,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把我们聚在一起了。他是东北流亡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会上常慷慨陈词,有时声泪俱下,闻者动情。他心直口快,敢想敢说,大家亲昵地称他“大炮”。他比我大一两岁,对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同学关怀备至,我们也敬仰他,把他当作老大哥,学校里一些活动,我们都跟着他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先后离开北平,从此天各一方,一别12年。只有从晋察冀来延安的同志口中知道一点他的消息,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学都很惦记他,常常谈起他。
1949年4月我作为嫩江省青委书记,参加韩天石同志率领的东北代表团,到北平出席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受到陆平同志的热情款待,多年暌离的老友把手叙旧,快何如之!
1953年5月我从苏联回来,到重工业部钢铁局工作。当时,陆平同志已调哈铁任局长,不久,他就回到铁道部任副部长。这期间大家都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作,虽时通音问,而来往很少。
1957年“反右”之后,中央决定调一批干部到高校工作。当时曾点名要我去成都地质学院,由于冶金部不同意,几经争论,把我留下来。后来,得知陆平同志调到北大任校长、党委书记,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勤于思考、勇于开拓的人,干一行爱一行,遇事钻研,工作扎实,他又在北大教育系学习过,老同学见面谈起来,庆幸北大得人。但是一场社教运动搞得大家都很被动,陆平同志一直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接着,“文革”妖风否定一切,颠倒是非,北大首当其冲,陆平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从未动摇对革命的信心。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着手整顿乱局,解放干部,陆平同志才从牛棚里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于“文革”蒙冤这一段经历,他一直不愿谈及,好像有些精神负担。不久前,看到他的女儿在《纵横》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讲到他的这种心情,读后心潮汹涌,久久不能平静。
“文革”过后,满天乌云尽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阵春风,使得大家心情舒畅。从1980年起,“一二·九”时期北大老同学每年聚会,陆平同志一直积极参加,后来因体弱多病,90年代后期就很少参加了。他住院时,我几次去看望,他还很乐观,不料2002年冬竟一病不起!八宝山送别时,正是“一二·九”运动67周年刚刚过去,老同学抚今追昔,感慨言系之!
陆平同志毕生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他的革命精神和实干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