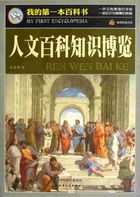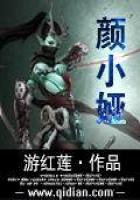(2000年1月23日)
了且比我大十几岁。我是在河大附中读高中时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在河南大学读书,同时又是《大公报》驻豫记者。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公报》派他到宛西考察,他写了一组文章《镇平自治区》,详细介绍了彭锡田在镇平搞地方自治的情况。
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印象中,彭锡田是大好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提出“自卫、自治、自富”的口号。第一是创办民团,建立地方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对付土匪骚扰;同时,在百姓中成立“诉讼委员会”,打官司前先在这里进行调解,主张和为贵,实际上是做思想工作,要大家搞好内部团结。第二是发展经济。镇平地少人多,人民生活水平低。他带领人民发挥传统优势,办手工业传习所,利用麦秆编草帽辫,风行一时,一直推销到武汉一带。还发展玉石雕刻。玉石出自南阳独山,独山玉是很有名的。目前镇平的玉雕仍为河南一大特产,澳门回归时,河南送给澳门的礼物玉雕九龙晷就是镇平生产的。第三是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了且的文章对这些都做了详细的描述。记得文章还谈道,国民党政府派去的县长没事干,只能“花落讼庭闲”,形容得好,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了且去采访时,同彭锡田见了面,进行了交谈。在宛西,彭锡田的威信很高,人们对他十分崇拜,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因为他给百姓带来了实际利益。彭锡田属于乡村建设派,实行的是山东邹平的一套,但比邹平的更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可惜后来彭锡田被反动派买通其卫士给杀害了。了且的这组文章在《大公报》上连载了好几个月,影响很大。
了且同我大哥相熟,我大哥对了且很推崇,多次向我讲到了且。有一次,我到河大图书馆借书时,查到了了且写的书《大人物的把戏》,于是借出来看了,记得是揭露抨击当时官场黑暗的,写官场如何乌七八糟,给我印象很深。
了且同我大哥都在现代中学任教,那时的校长姓王(即王子珍)。我对现代中学颇有好感,当时就认为他们是倾向进步的。我有个同学叫赵进科,我们同住在一个寝室,他的弟弟是现代中学的学生,曾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该军失败后,他又回到现代中学学习。赵的弟弟到我们寝室时讲现代中学,讲他参加抗日同盟军的过程,给我印象很深。
还有你们的母亲次云。我在河大附中读书时,同河大学生在同一座楼上课,常看见你们的母亲。别的女大学生都比较年轻,次云岁数比一般女生大一些。我们想,这大嫂这么大的年龄了还在学习,真不简单。这时有人介绍说,她是张了且的夫人。了且是1932年河大毕业,我大哥是1934年毕业,同年我由河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1934年至1937年,我在北大期间同大哥常通信,对了且的情况知道一些。大哥说了且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还是倾向进步的,并说1936年了且当了现代中学的校长。我还有个中学同学、好朋友胡子云也在河大读书。那时,我同他一直有通信联系,他也对我说,现代中学那几年仍然保持着比较好的状态,是进步的。
七七事变后,我从北平回到开封,经常看到了且。那时他为了抗日救亡一天到晚开会,很活跃。他活动能力强,共产党的公开代表刘子厚(当时化名马致远)常通过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当时我们返豫的平津同学成立了“平津同学会”,积极开展救亡活动,我也常开会,会上同了且常见面。当时我大哥也很活跃,很积极。
将现代中学从开封迁到南召县,是中共河南省委,具体说是刘子厚、范文澜的意见。因为当时省委决定把伏牛山中的南召县作为省委重要的工作区域,以备将来在伏牛山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1937年8、9月间,我在开封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到南阳,成立“宛属平津同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到了南召,先后任南阳特支委员、南阳中心县委委员及南召县委统战部部长等职。这个阶段,我同了且也有不少接触。现代中学是1937年底迁往我的故乡南召县李青店的,你们全家也是那时去的。记得你们去后,住在我家过厅里。从我大哥的院子到二哥的院子原先走过厅,你们去后就封了过厅走角门了。
王锡璋、党及辰、胡子云这批年轻的大学生共产党员,都是党组织派到现代中学当教员的,在办现代中学和开展南召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员中还有一位叫刘梅村,这人很好,虽有严重的肺结核,但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最后死在现代中学。刘梅村到李青店现代中学,党组织是信任他的。他从监狱出来没带组织关系,我们仍把他当党员看待。当时党组织对他的过去做过了解,认为没有问题。
当时现代中学还有两个延安派来的教员,一个叫徐进,是刘子厚介绍来的,另一个是女同志李焕生(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党校教务长),从陕北大学来的,由范文澜介绍给了且。我们在现代中学的学生中还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现代中学成为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群众说它是“小抗大”,说李青店是“小延安”。
现代中学迁到李青店后,了且回去过几次,但都没有久停,他忙于外边的活动。听大哥讲过,他让了且多在外边上层活动活动,疏通一下,为南召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了且也常对大哥说:你们放手干,我在外边顶着。南召自治派的实力人物李益闻也专门找了且谈过,让他多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记得1940年4月,当局在镇平召集各县有关人员开会,李益闻派我去参加。我明显地感到反动派对南召的压力加大了。后来他们点名要我大哥到洛阳省训团受训,李益闻专门嘱咐我大哥,让他到洛阳后先找了且商量,看如何对付这局面。南召进步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河南省党部一伙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他们一方面多次派特务到南召进行监视和破坏,另一方面不断给别廷芳、李益闻等地方自治派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南召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为此,李益闻也专门找了且谈过,让他多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做解释工作,说南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都赤化了。这方面,了且做了许多工作。李益闻并不是共产党,可反动分子不断告状,后来干脆说他是共产党地委委员,给他戴上了红帽子并枪杀了。
大哥他们到洛阳省训团受训时,省里专门点我去受训,他们为我打了个掩护,说我到西南联大读书去了。这时,组织上指示我们转移。1940年9月,我到南阳乡下杜河的舅舅家住了一个月,接着同表兄及其一位友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往西安奔去。当时,路上已很不平静,经过镇平、内乡、淅川,都没敢进城。过武关时,那里前一天刚杀了人,我们是硬着头皮过了关。
解放后,我知道了且同中共地下党有关系,曾策动张轸起义。以后,我们见过多次面,也有通信联系。我的信件和个人日记都没了,在“文革”中烧了。我几十年的工作日记能保存下来应归功于秘书,他把着钥匙拒不交给造反派,因此才保留了下来。
记得1953年我在重工业部钢铁局工作时,了且同次云到北京来,我们见了面,他详细地同我谈了他的历史,特别是策动张轸起义的过程。记得那时了且在一个学校(湖北省军区军政干校)工作。以后我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忙得很,主要是搞武钢、包钢建设。1958年“大跃进”武昌会议时,我到武昌看过他。那时忙,喝杯水、见见面就走了。打倒“四人帮”后,我到武汉,把了且、次云及另外几个老朋友请到我那里见了见面,吃了顿饭。1987年他去世前三天,我去看他,他已卧床不起了。对了且,我们过去有所评价,现在看来还是符合他的实际的。这个同志的一生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过来的。他的处境并不顺利,也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但不论面对什么困难,他都比较乐观,始终保持创业者的勇气。我们佩服他意志坚定,是个很坚强的人。他对旧社会的一套参透了,年轻时写《大人物的把戏》,那是开始。了且能在旧社会那么复杂的环境下保持进步的思想,没与那些人同流合污,的确不容易,真是出污泥而不染。
前年我到新乡看到段雅亭,曾在南召工作的老朋友,都认为在那种环境中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不容易,是冒风险的。年轻时有冲劲闯劲,可能想到;年纪大了,还能做一番事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太不容易了。了且同张轸的关系开始得早了,是在抗战前。后来策动张轸起义,了且确实是立了大功。
纵观了且的一生,应该说是走向革命的一生。“左”的思想占上风时,对这一批有功于革命的人员的待遇是不够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