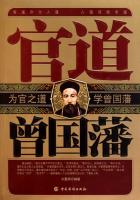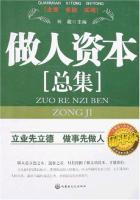说》、《皇帝的新心——“超越内在说”再论》等。他们认为“内在”就不可能同时是“超越”的,“超越”不能同时是“内在”的。他们的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自熊十力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也包括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的余英时)以“内在超越”来解释传统儒家而言的。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但总的说来,否认儒学“超越内在”说者不赞成儒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以这个立场看,李申因认为儒教是教,所以,似乎是倾向于肯定儒学的“超越性”的。此外,郝大维、安乐哲二位虽不赞成儒学具有“超越性”,但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这里我们专就“内在超越”或“超越内在”问题谈谈学者们的分歧。
不赞成儒学“内在超越”者,例如冯耀明在《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在”说》
中认为:“超越”一语在柏拉图哲学中的典型用法“涵有外在(beyond)及分离(separate)的意思”,“超越”即同于“外在”,怎么能以“内在超越”或“超越内在”
来释说儒家思想呢?说“超越内在”即等于说“圆的方”。严格的超越的观念,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是一个深刻而重要的观念,它是在逻辑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语境中存在的,这样的观念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它与“对中国古典典籍的解释无关”。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即使在今天西方学术界中,这样一种诉诸神学、科学和社会理论中的超越观念也不怎么时行了,已经没落了。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现代新儒家以“内在超越”解说传统儒学思想,要么是将“内在”与“超越”两种根本对立的东西捏拿在一起,形成一个不知所云的东西;要么是将根本不相应的一套术语去说明另外的东西,似乎是以西方的观念体系去解释儒家。
事情果真如此吗?在我们看来,以上观点一方面主要是批评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观念,另一方面也同样没有跳出西方学术的基本路数。比如,认为“内在超越”说是把客观的创造实体或超越原则与主观的自觉心灵或自由主体等同起来,认为这种将“宇宙心灵”
与“个体心灵”浑化为一的“心灵”是“皇帝的新心”。其实,这里与其说是在说明“内在超越”根本是莫须有,还不如说是在批评儒家的最基本的观念。因为,将“宇宙心灵”与“个体心灵”浑化为一的心灵不就是“仁者”的“心灵”吗?“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心外无物”等等,都有这个意思。说“内在超越”莫须有,不就是说儒者的这些观念是莫须有吗?我们当然不能说儒学中的这些观念就毫无问题,不应加以批评。可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些观念究竟何所指,而千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乃至民间百姓为何有这样一些观念?它们仅仅是魂落乡间里巷的孤魂野鬼的奇思妙想吗?还是在这些观念的背后有更深刻更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
汤一介认为,“天道”是超越性的问题,“性命”是内在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属于形而上的问题。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形而上的问题是“超言绝象”的;“超言绝象”自然不可说,说了别人也听不懂,只能自己去体会,所以孔子提倡“为己之学”,而反对“为人之学”。“天道”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通于人之内在之性,故《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性”同样不仅是内在的而且可以通于“天”之超越之性,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继孔子之后有孟子,他充分发挥了孔子哲学中关于“内在性”
的思想,并以人之心可以通于超越性之“天”。他说:“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人本然所具有的“四端”的充分发挥,则表现为仁、义、礼、智之善性,这样就可以达到对超越性的“天”
的觉醒,而实现内在之人心与超越的天道同一。宋明理学在更深一层次上解释孔子提出的“性与天道”的问题,使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的特征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程朱的“性即理”和陆王的“心即理”虽然入手处不同,但所要解决的仍是同一问题。程朱是由“天理”的超越性推向人性的内在性,以证“性即理”;陆王是由人性之内在性推向“天理”之超越性,以证“心即理”。
汤一介指出,我们是否应该在发展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的同时,也引进或建立一套以“外在超越”为基础的哲学理论呢?对人类社会说,人们除了应要求以其内在精神来提升自己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同时也应承认有一种外在的超越力量可以帮助或推动人们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这不仅因为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曾对人类文明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而且这种哲学和宗教对建立较为合理的政治、法律制度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哲学能充分吸收并融合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和宗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使中国哲学能在一更高的层次上自我完善,也许它会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如果东西哲学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构成包含着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和以“外在超越”
为特征的西方哲学,那么东西哲学不但可以以多种形式相会合,而且将使人类的哲学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发展。
刘述先认为,宗教信仰向往“太和”(ComprehensiveHarmony)的境界。
有人认为,在自然世界之中,老虎杀羊,这就否证(falsify)了自然中有太和的说法。这种驳斥是犯了典型的范畴错置的谬误,它背后隐含了一种单向度的思考,以为通过经验推概的标准就可以判断宗教信仰的真假。试问哪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不知道经验层面老虎杀羊的事实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太和”的向往与信仰。由此可见,“太和”的理念并非建立在经验推概之上,也不会因为它不符合经验观察到的事象而失效。事实上没有人会否认世间充斥着众多彼此矛盾冲突的现象,而这恰恰是人类追求宗教信仰背后的一个深刻的动机。故此基督教寄望于他世的天国;佛陀看到众生之相残而发心追求解脱之道;孔孟的儒家思想乃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据乱世”,所以公羊家才要格外显出对于“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向往。也恰因为儒家不甘心把泥足深陷于“内在”之中,才会努力去追求“超越”的信息与理想。
刘述先指出,儒家式的内在超越形态的确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而令超越的信息不容易透显出来。但这并不表示,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型没有严重的问题。基督教的上帝表面上可以保持其纯粹的超越性,其实不然。因为上帝要与人以及世界发生关联,就不能不进入内在的领域而受到这方面条件的局限。
既然上帝往往要通过启示给予人类指引,而被挑选来传达上帝信息的先知又是内在于此世的人,他们也必须用人的语言才能传达超越的信息,那就不能保持纯粹的超越性了。如果肯定超越的信仰就必须否定内在的准则,否定人在自己的生命之内可以体现神圣的光辉,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这样看来,外在超越说乃不能不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如果要维持超越的绝对性,就不能不否定内在标准的自主性,如果超越内在于人性与世界之中,则外在超越已变质而为内在超越,有许多事情要依靠人自己的判断而不能仰仗不可知的超越,则外在超越说并没有它所声称的胜过内在超越说的优势。事实上,外在超越说与内在超越说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来的两种学说,这由检验西方神学发展的线索便可以明白。
在这个问题上,李申《中国儒教史》一书用了近一百五十万言来申说辨析。
如果抽去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及制度,仅仅从学理上来分析这些观念,当然是很不够的。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国家组织就像儒教的肉体,而儒教就是君主制国家的灵魂”。而要辨明这一断语所可能引起的误会,就要说明这些观念究竟何所指。因此,我们需要说明现代新儒家对“超越”的特殊理解。
关于“超越”一语,按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一术语的使用情况,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超越即超验,不可经验之意。康德认为,超出一切可能经验之上、不为人的认识能力所能及的便是超越的,如上帝。第二,指人可超然于生存环境的主观精神力量或意志力,这种意义上的超越是非常泛化的,相当于超过、高于、超然等等。然而,在第一层含义中,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超越”的,可它透显出的另一层意思是神性。在康德的哲学中,认识论与伦理学恰恰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认识论是不关心神性的,它关心的是客观原则,所以必须有“自在之物”存在。只有在伦理学中,上帝的存在才是必然的。这些,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种《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中知晓。
但现当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在基本品格上是一致的,他们更为关心的不是认识论,而是价值论、本体论问题。这样,“超越”一词也不是在认识论上讲的,而是从他们的本体论-境界论上去讲的。因而,所谓的“超越性”指的是神性、宗教性。儒家所追求的境界,“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其至也,虽圣人也有所不能焉”(《中庸》),从这个意义上讲,终极的境界也有难以经验的地方。本体-境界为何具有神性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儒家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最基本的观念——“天人合一”。
依据这样一种思想,高高在上的天道与人的“良知”、“本心”是相通不隔的,如果天道、天具有神性,那么,说人之“良知”、“本心”也因此获得神性,应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天具有神性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论述。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在儒家看来,“宇宙心灵”和“个体心灵”可以浑化为一,原来,所谓“天”,是形上义理之天,并不是指的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而“天”也是一个本体论-价值论的概念,其认识论意味是十分淡薄的。而如果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尽心、知性、知天”,又把天看成外在的客观存在,便显得难以理解,像“心外无物”这样的说法就只能是疯话了。
因此,超越性与宗教性虽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在现当代新儒家的心目中,两者是相通的。因为,超越的“天”完全没有认识论意味,而只是价值之源。
如果超越性被理解为神性、宗教性,而天人又是相通不隔的,那么,以“内在超越”来解释传统儒家的思想便不是不可理解了。余英时亦对“内在超越”
说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同,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个性特征是“内在超越”。“内在超越”的特征就是认为超越的价值源头与根据在内而不在外,这就是所谓“为仁由己”,“依自不依他”。不过,尽管超越的价值之源在内而不在外,但作为价值之源的心灵却又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正是由于这种相通(或云“合一”、“相感”等),使个体的“自省”、“自反”、“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成为必要,这就是道德修养功夫上的“内转”。也就是因为这种相通,使在“内转”基础上的“外推”(推己及人、推恩)成为可能。“内转”与“外推”统一起来,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内在超越”。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往一复的循环圈。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天人相通合一,就只能回答说,这是儒家乃至传统中国人根本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所以,现当代新儒家认为,“内在”与“超越”并不是直接对立的。“超越”
(神性)可以同时是“内在”的,换句话说,超越的价值理想追求,可以通过人的修身增德而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红尘中实现;相反,对六合之外的事,“圣人存而不论”。这样一种超越,的确与西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它不需要也很难得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方式的“证实”,而需要的是儒者的身体力行,自己体悟、体证,自证自信。对于内在与超越的关系,刘述先将之比作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有限(内在)与无限(超越)有着一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现代的特殊的条件去表现无穷不可测的天道。这样,当我们赋予理一分殊以一全新的解释,就可以找到一条接通传统与现代的道路。”这样,“超越”与“内在”的统一性不仅不是儒学理论上的缺失,反而是它接通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