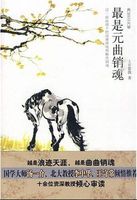纪事
决心南调海南。在宜昌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年会上,全部谈的是现代人的处境,而这种处境又是被那种官话、套话、大话铸就的;在学术界,几乎听不到任何真切的声音了,哪怕理论思考上还远远谈不上深刻,只要还是在努力说自己的话就好。
哲学与现代人处境
一
这个题目是1988年拟定的,当时以这个题目作过几次演讲,并且写成了一篇长文,但始终得不到发表的机会,最后只好以片断的形式分别以《哲学与人的处境》和《何处有哲学自己的家园》为题发表在1988年5月2日的《光明日报》和1990年第3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书林》上。
应该承认发表了的那两个题目都不好:离开“现代人”,何谈“人的处境”?离开“现代人处境”,又何谈“哲学自己的家园”?
我们哲学上的空疏浅薄,一言以蔽之,皆在于不能直面与“现代人处境”息息相关的“当代”这一事实。以前说哲学是时代的反映,黑格尔加上一句,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的毛病,在于把“当代”这样一个繁复多样的“生活世界”概念化了。它同时也意味着生活在“当代”的人的概念化。认识当代的人,不能从人的概念出发,而只能从当代人的存在样态、行为方式出发;也正是当代人的存在样态与行为方式才构成了“当代”这一概念。哲学总要揭示时代与人的关系。“本质”一词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它可能在“本质关系”的名义下把时代与人的关系抽象化为一种普遍必然的同一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志于哲学思考的人就不再深思时代与人的“本质关系”。当旧有的揭示这种“本质关系”的概念、范畴、方法、模式都无助于我们对当代的认识时,哲学也就处于危急与挑战之中。
“现代人处境”只能通过对理解“当代”这一概念体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意义剥离才能显示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在历史地重现并使用旧有的范畴与概念中解构其传统规定性。而且必须牢牢记住,有助于形成新的“当代”观念的领域不在思维与逻辑,甚至不在对“自我”、“主体”概念的重新确立或“反思”方法的重新规定。“现代人处境”绝对是个逻辑在先的问题,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思路也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清理。
我在思考时代与人的关系中,有两个自我拟定的立足点,一是坚持时代的客观性,就是说,当代所能让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是时代自身所呈现的样态,不能主观化地归结为主体的观念或表象,甚至不能再像康德那样从主体的观念、表象出发追问“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就此而论,主体、自我、反思、先天能力是一些远较“当代”虚假的范畴,它们如果有意义的话,也须首先放逐到“当代”这一生活世界中去,并在当代的人与人的交往中给予重新规定。我把我自己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哲学思考和艺术作品都规定为是有助于对“当代”的理解的作品;同时也只站在当代的立场去理解外国的哲学和艺术,而不管这样一些作品实际产生于什么时代。
再就是坚持个体的真实。尽管我们都生活于当代,但“当代”的现实性又只存在于个体那里,也只有对个体来说,“哲学与现代人处境”才成其为问题。个体的真实不是指为我所感知的观念或表象多么真实(贝克莱)、我对我的观念、表象的怀疑(笛卡尔)或怀疑的怀疑多么真实(斯宾诺莎),甚至也不是指我所感觉到的“我”在肉体与精神上多么统一。个体的真实,作为一种需要努力达到的东西,只意味着必须从过去有关“我”(这一指称)或“个体”(这一名称)的规定性中走出。
任何人一经命名,就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名称矩阵”中确定了他的位置。利奥塔曾指出,人所具有的唯一“同一性”就是他在一个语句世界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同一性;社会集体的文化和教育越是反复强调这一位置上的这个人(固定指称词)在肉体和角色上的同一性,这个人的自我认同也就越强烈。哈贝马斯也认为,肉体同一是前习惯水平,角色同一是习惯水平;角色同一把具有“肉体”物征的“我”的性别、年龄、体质符号化了,使“我”只作为一个无个性特征的角色承担者存在着。作为一个小例子,这里可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几乎要在所有的表格上填写自己的性别、出身、成分、是否受过奖惩以及家中是否有人被镇压等等;条目越分越细,目的显然是为了使“填写者”(这个具体的人)的名称(如陈家琪三字)与众不同,而不同的途径却恰恰是通过高度同一的符号化过程来实现的;当你与你的性别、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有了一种自我认同时,你也就变成了一个毫无个性特征的角色承担者,比如一个“黑五类”、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从过去有关“我”或“个体”的传统规定性中走出,不仅是说作为个体的“我”永远有独立于我的“角色”的一面,而且是要表明“我”作为一个指称,哪怕再固定,在语句世界中与其他语句的连接方式也是自由的,并不存在某个绝对的规则来限制这种连接方式;而且无论在何种连接方式中,“我”都可以把隐藏在特殊角色与连接规则后面的“自己”寻找回来。这看起来是在谈论指称“我”以及“我”在语句世界中的连接方式,实际上人的自我认同只能在语言交往中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才能实现,而个体的真实又只表现在语言交往与社会化过程的“断裂”或“空白”之处。这里我想引用两段有关诗的论述来说明客观性和个体性这两个原则:好的诗句完全像是自我流淌,作者被湮没在诗句中,而不是让诗句从属于作者的创造;不知是谁说过,“诗就是从翻译中被遗弃了的那种东西”。以此设想,个体的真实就是那种在所有有关个体的名称、指称、定义和语句规则中被遗弃了的东西。
二
通常所说的“现代人”指20世纪的人,我们这代人大都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人称我们为“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或“中国革命中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为了更鲜明地突出特点,也有人自称为“四五的一代”以和“五四的一代”区分开来。但真正使这代人在名称、角色以及自我认同上发生混乱并终于发现几乎任何指示性语句都遭受到颠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从1919年到1989年总共七十年,我们出生于40年代末,到1989年,已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生活了四十年;进入90年代,世风大变,于是前四十年作为生命的一页也就揭了过去,那一页上的我们基本是自我认同的,也认同社会集体的文化和教育所反复确定下来的那个“我们”,如长在红旗下、造反小将、四五英雄、学术中坚等等。
当这一页揭了过去的时候,我们已不再是我们。
我们是谁?
当然,谁也无权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出现。问题就出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但我们还得把“我们”作为一个词语的惯常用法来使用,同时也说明像“我们”这样丧失了自我认同的人,绝非只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上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当代。
“当代”并非一个一下子显露其全部意义的概念。在我看来,“当代”如此真实地呈现在面前,其标志就是我们用于理解、把握、说明、规范“时代与人的关系”的全部指示性语句和认知性语句统统失效。我们可以把这种失效简称为哲学因其无用而死亡;与哲学的死亡相关连的,就是我们在前四十年间所形成的信仰、理想、热情和价值的崩溃。
哲学的死亡可能会使一些人想到“后哲学”或“后现代”这样几个聊以自慰的词,但丧失了未来的我们面对的却是既无伦理热情,又无“天职”观念的经商热潮以及在这一热潮中只以攫取财富为目的的狂热,甚至包括可怕的凶残和渐渐逼近着的骚动。在对技术、工具的迷信以及把一切都转化为手段的急功近利中,我们看不到“后哲学”或“后现代”所应该具有的那种理智上的冷静与无奈,因为这种冷静与无奈是以对人的再现能力与创造能力的界限的洞识为前提的,而且这界限不再是过去所说的绝对与完美,不是我们所曾憧憬过的共产主义或大同世界,而就是面对的现实,即我们的当代。
当我们缺乏任何有力的范畴来规定自己的当代时,倒是大量出现的文学作品更贴近于我们的现实。这使我想到古往今来,生当末世的思想家们总以“补天”为己任,而只有穷困潦倒的诗人才直面现实这一事实,也许这就是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颜元、戴震与曹雪芹的差别。我得承认,就是现在,就对“当代”的心理的、情绪的真实感受而言,哲学距离艺术还差得很远。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但我怀疑的是这猫头鹰恐怕永远也起飞不了了。相对于哲学的真正的现实就体现在这里。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用上帝已死,或过去的标准失去了效用而新的标准尚未建立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独特存在。“旧篱已去,新墙未筑”,“旧篱”真的已去,“新墙”真的待筑吗?“当代”弥漫于我们四周,我们无从看清,但又无可逃遁;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弥漫使思想建筑物一批一批地倒塌,所以才急于“筑墙”,而我却必须通过清理使倒塌后的地基更其显露,就是说,让“旧篱”真的“已去”,且要说明“旧篱”是在怎样的地基上建构起来的。这里确有一种理智的冷静与无奈,但既无“看透”的彻悟,也无“顽主”的潇洒,当然更无意“补天”——无才无德而已,这也是我为自己私下确立的另一准则。
三
谈东西方哲学的比较和交流也好,谈文化发展的特点及走向也好,都只能从我们立足的“当代”出发;“当代”决定了我们想看到什么和能看到什么,“当代”也给了我们一个只属于当代的情感方式,在理智的冷静与无奈后面,那种只属于个人的情感方式才是一种剥离掉价值判断后所遗留下来的真实。
让我们先从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也”;另一方面却是众皆“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结果是既无叹息之声又无正义呐喊的真实说起。这说明,自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甚至创立共和的旗帜已渐趋显露其只不过是另一批口号的面纱,同时也说明尚有另外的口号可资利用,这就是回到传统文化。自由、民主、平等曾打败过传统文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因为随着这种打败,一个政权被推翻了,而另一个政权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改造以至“文化革命”中扫荡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