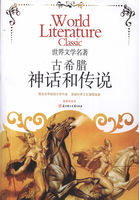人道主义者说“人创造了历史”。但这句话很含混:可以理解为历史是人类行动的总和,这意味着历史具有属人的或理解为非自然的属性,但又不是某些个人有意创造的;还可以理解为历史是某些个人或集团有意识地进行谋划和行动的结果,这就排除了任何超人类个体(包括上面提到的人类行动的总和)所能起到的支配作用;再有就是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人有目的创造的,但人的目的又必须从其所属的特殊的社会集团那里获得解释。作者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很不确定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性固有的趋势,是历史进步的条件,这里强调的是某种非意愿所能左右的必然力量(人内在固有的本质的现实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无产者是世界历史的推动者,这里强调的是无产者主观意愿(翻身得解放)在决定历史方向上的决定作用。作者说,马克思的观点最后可以归结为“历史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所造成的无意识的结果”,按此种理解,全人类的解放就在于使“无意识的结果”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蓝图的实现,即使人类(实际上指的是无产者)从“自在”(initself)达到“自为”(foritself),因为“自在”(自然)本来就与“自为”(精神)具有同一性,历史不过展示出了这一过程而已。
不管怎么说,“人创造了历史”意在肯定历史的可理解性,它所依据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历史是一个不同于自然本身的过程,所以历史必定是“被创造的”,如果没有神,创造历史的就只能是人。人道主义者们说,无论在人创造历史时“非理性的”或“无意识的”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人们可以对历史进行道德的或理性的判断本身就足以证明历史是一个可以体现出主体动机的过程;不管这种动机来自何处,只要主体的动机起着作用,人们就可以对其作出理解。
非人道主义者指出,引出“人类内在本质”或“世界精神”之类的范畴纯粹是为了使历史成为可理解的,为了用“异化”、“堕落”、“拯救”、“复归”之类的模式来确定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来达到对当代社会的存在形式展开批判并鼓吹采取行为改变它们。所以一切人道主义对于历史的看法只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是历史一定时期的产物,根本不具有客观真理性。他们说,历史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完全不是有“内在的可理解性”(intrinsicintelligibility)。他们对此提出了三个层次上的理由:第一,人们理解力是受人性的限度限制的,我们一开始就存在于一个对其起源、性质与命运一无所知的宇宙之中;第二,我们是被一些明显先于我们的意识或理性的情绪性力量推动着的;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在于我们用于交谈或理解的语言——原先以为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却是因为我们根本未发现语言问题是个问题。比如当我们说我们“思想”或“认识”时,“思想”或“认识”这些词语本身并不透明,而且充满着歧义性。所以我们是在用我们根本不曾理解的东西在进行交流和理解。索绪尔最先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既取决于它与同一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关系,又取决于它可以兑换的思想或观念;一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并不是先验确定的,而是只有当此符号被运用时,这种关系才出现。
同样,一符号与其可兑换的思想符号也不是确定的,它取决于赋予符号以意义的一方与世界之间所建立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指的符号与事物的关系,而是符号作为一种“音响图像”(acousticimage)与“思想”(thought)间的“神奇统一”(mysteriousunion)。这样一来,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与符号作为一种音响与思想间的关系就成了常常分离着但又相互遮蔽着的关系。作者说,把语言认为是理解个人及社会存在的关键本质上导致了对真理的拒绝。为了使语言对于它所意指的东西具有一种从属意义,索绪尔求助于一种对当下显现在思想中的东西的捕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一点“当下的真理或确定性”(thepresenttruthandcertainty)。对此,德里达愤怒地谴责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谎言”。德里达说,这种谎言源于言说者以为语言的意义对于言说者自己是自明的。他说,语言的意义只在语言的不同运用中,所以根本无所谓“当下”。同样,“世界”本身就是一文本,也不存在任何先于语言与表达的纯粹意义。只有那些认为时间是从过去不断走向现在的人才会相信有一个“现在”或“当下”,而一切人道主义者的谬误就在于站在“当下”(亦即自己的立场)去评述有关进步、开化、文明或真理问题。德里达说,索绪尔的“当下”是建立在一符号与尚不存在的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必须确定一种超出各个使用者之外的“当下”,这实际上仍是把主体的体验当成基点,并从体验出发来寻找“原初的、基本的真理、理性或逻各斯”。
这样一来,如果语言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或原初的意义的话,那么任何传统的有关“真理”的梦想就会全都破灭了。德里达由此“再造”(recasts)了自己的真理观,这就是意义对所有人的同值;赋予语言以意义的与被赋予意义的东西之间的差别的消失;主体与任何决定着主体的东西之间界限的消失,以及任何意义上的秩序与结构的解体。这就是真理。德里达说,它把一切可能性都敞开在每个从决定论的牢笼下逃离出来的人的面前,大家看到的就是那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绝对机遇”(absolutechance)和“始发的不确定性”(geneticindermination)。
人们马上提出的问题就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以及每个人是否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们预先就把人道主义或与人道主义有关的学说作为前提接受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作者认为,人们只有靠语言才能进行交流这一点并不能说明被语言所决定了的东西就与在另外一种社会结构下被决定了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说,语言与人们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人际关系处在完全不同的秩序之下。语言关系是不能比喻为家族相似的。语言既不是社会结构的典范,也不具有社会现实中那种物质的强制性,所以尽管语言对个人的确定性含义被消解了,人仍旧相信存在着某种超出语言之外的秩序,其中包括那种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多数人的语言”。
作者对语言问题的讨论还有许多耐人深思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加转述,只能说,作者在最后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切记不要把哲学上对“人的终结”的讨论转变为在现实生活中对促进人的死亡的被动性的鼓励,切记不要认为各种非人道主义的学说都在怂恿人对人的野蛮与非人性。切记不要从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另一种形式的独断论,不要忘记谦虚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因为说到底,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过程的话,那么一切自然生命的湮灭,或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与繁衍方式的湮灭,说不定本身就是“自然界”“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对所有诸如此类的“谋划”都一无所知,所以任何从根本上使人感到绝望的东西也就同时从根本上带给了人希望。
原载《社会科学动态》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