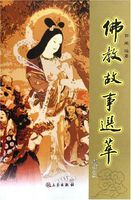嗨!这些人明知自己就像不关心马铃薯的价格那样,并不关心他们以后是否会再见到那些人,却当着他们的面大声哭泣,于是我就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虚伪。而我得到的回答是:哈!一个新西兰人的热爱是外露的;是表现在他眼睛里和嘴巴里的。”航海家P·狄龙船长经常苦于这种表示热爱的喧闹演出,他告诉我们,他怎样设法以恰当的方式来应对他们。他说:“这在新西兰是一种习俗:当朋友或亲戚在长期分离后再见面时,双方要互相触摸鼻子并流下眼泪。我经常彬彬有礼地遵奉该仪式;因为我假如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破坏友谊,按照新西兰文明教养的规矩,就会把我看作与野蛮人不相上下。但不幸的是,我的冷酷的心无法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轻易流泪,因为我不能像这些新西兰人那样制造出此类感伤的液体;只好用口袋里的手帕在双眼上按一会儿,同时用当地人的语言偶然号叫一声,以符合表达真正悲痛心情的全部效果。这个仪式对陌生的欧洲人是不用的;但对我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如他们喜欢称呼我的,我是一个Thongatamoury,也就是说新西兰人,即同乡人。”此外,我们还读到,“新西兰人见面时富有情感性,但离别时一般并无外在的表现。在见面时男人和女人都会在一起相互按压对方的鼻子,同时眼泪汪汪、低声反复诉说着自从上次见面后发生的种种有关彼此利益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沉默的悲痛。如果见面双方是长久分别的近亲,则按压鼻子和哭泣就得持续半小时。如果见面双方是偶然熟悉的人,则仅仅鼻子碰一下鼻子就分开了。这种行礼叫作宏伊,其含义为嗅。很像东方的食盐习俗,用于消弭敌对双方的仇视。在宏伊时嘴唇从不接触,这不是接吻”。
此外,在安达曼群岛上的土着人当中,“亲戚们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未见之后,为了表示他们在见面时的高兴,要相互用手搂着对方的脖子坐下来,流泪并高声叫喊,让外来者觉得在他们身上一定发生了非常悲痛的事。实际上,他们在表示高兴时和他们死了亲人后表示悲痛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哭泣大合唱由女人开始,但是男人们迅速加入进去应和,很快就可以看见形成三组或四组人在这样齐声哭泣,直到彻底筋疲力尽,他们才不得不停止”。在印度比拉斯布尔地区的蒙格利塔西尔部落里,“有一个必须遵守的习俗,当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亲戚们聚在一起时,要由女人们痛哭流涕并大声号叫。比如说,几个月在外的儿子现在回到了父母的家,他先要跑去触摸父母的脚。当他坐定下来后,母亲和姐妹们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依次将双手按在他两个肩头上,大声哭泣并呜咽着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多少有点重要的事情”。在印度中部几个邦的乔汗人部落里,礼节要求女人在迎接远道而来的亲戚时必须哭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两个女人相互看见时,她们要一起哭泣,两人都要把自己的脑袋搁在对方的肩头上,双手则放在她的腰部。在哭泣过程中,她们要交换脑袋的位置两到三次,并彼此按照辈分相互呼唤,或母亲,或姐妹等等。而万一家里最近死了人,她们就高声呼唤他或她:哦,我的母亲!
哦,我的姐妹!哦,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是我——不幸的我,代替你去死?当女人和男人一起进行哭泣礼时,她用手抓住他两边的腰部,并把脑袋搁在他的胸膛上。男人不时发出高呼: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当两个女人一起哭泣时,按仪式的规定,年长的那个应当首先停止哭泣,然后要求她的同伴也这样做,但如果弄不清到底谁的年纪大,她们有时会一起哭一个小时,激起年轻观众的笑声,直到最后有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走上前去告诉她们中间的一个人不要再哭了,她们才停了下来。”
用痛哭流涕来表示欢迎的习俗看来在南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也很普遍。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地区居住着图皮人,在他们当中,礼节要求如果有客人进入他应当受到殷勤接待的棚屋时,他要坐在主人的吊床上,并留在那里独自沉思一段时间。然后,屋子里的女人们会走上前来,坐在吊床旁边的地上,她们会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大哭起来,并对客人表示欢迎,她们一边痛哭一边赞扬他。在进行这些表演的过程中,也希望客人与她们一道哭泣,万一客人无法流出眼泪,至少可以发出深深长叹,并尽可能做出非常悲痛的样子。当图皮人出于礼貌规矩严格安排的这些仪式正式进行之时,主人却一直像是个不感兴趣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走近客人并与之攀谈起来。查科地区有一个印第安部落林古阿人,“当他们在一段时间没见到一个人后再次看见他(她)时,会使用一种奇特的殷勤待客方式。其内容如下:这两个印第安人会流下眼泪,然后再开始说话;不这样做就会是一种侮辱,或者至少证明这一次见面是不受欢迎的。”
在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卡贝卡·德·瓦萨描述了看来居住在如今得克萨斯海岸外一个岛屿上的两个印第安部落中奉行的类似习俗。他说:“在该岛上居住着说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一个叫卡波基人,另一个叫罕人。他们有一个习俗,当他们有时彼此相识和彼此见面的时候,先要哭泣半个小时,然后才互相说话。接着主人首先站起来,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客人,后者拿了东西,过一会儿就离开了。有时候甚至等客人接受礼物后,两个人都离开了,却连一句话都不说。”17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尼科拉·佩罗多年在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他描述了一群苏族人到他们的朋友渥太华人村子去作客时的情景,他们“刚刚到达就开始按照习俗,当着所有见到的人的面哭了起来,目的是向他们表达见到他们时感到的明显高兴”。实际上,这个法国人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充当了这种似乎悲哀的欢迎表演的对象,或者毋宁说是受害者。他受新法兰西总督的派遣去处理生活在密西西比河那一边的印第安诸部落的事务,他把自己的营地驻扎在河岸上,并在这里接待了来自阿耶奥人的使者。阿耶奥人是苏人的邻邦和盟友,他们的村庄在西面,距这里有几天的行程,他们希望与法国人建立友好关系。
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些印第安人与可怜的佩罗之间的这场会面。他们当着他的面痛哭流涕,泪水从身上直淌下来;他们的口水和鼻涕流在他头上、脸上、衣服上,他们的热情拥抱差一点让他呕吐,在这过程中他们一直非常悲痛地尖叫和高喊。最后,送给他们几把小刀和锥子,这才使得喧闹的洪流不再倾泻而出。但因为没有翻译,他们根本不能使人明白其意思,这样直到他们回去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几天后,另外来了四个印第安人,法国人听得懂其中一个讲的话。他解释说,他们的村子沿河上溯大约九里格远,他邀请法国人到那里去作客。法国人接受了邀请。客人到达时,妇女们都逃进森林和山里,一边哭泣一边向太阳张开双臂。总算出现了二十个男性长者,递上烟管请佩罗抽烟以表示友好,并用一张水牛皮把他抬进了村长的家。把他放下来后,他们和村长就开始在他面前按通常的方式哭了起来,他们的泪水、口水和鼻涕弄得他一头湿漉。当这个必不可少的仪式结束后,他们擦干眼睛和鼻子,再向他敬献了一筒友好的烟。法国历史学家补充说:“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如此哭泣的民族,他们的欢迎礼伴随着哭泣,他们的离别礼也是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