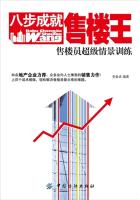其实,礼貌举止中有许多内容和威慑力密切相关,如握手是我们通常的善意表示,它的原始含意就是“手里没有武器,不可能对对方实施攻击行为”。碰杯也是如此,在两个互不信任的首领之间,这一行为表示“我没在你的酒里下毒”,在最初,碰杯双方的确要把自己酒杯里的酒倒出一点给对方。至于更传统的下跪,则表示“我慑服于你的权威之下”。正如一个通过尖牙利齿确立优势地位的动物,不需要对每个“臣服者”都穷追猛打一样,有威慑力的人也不必对每个慑服于他的人都盛气凌人,他甚至可以表现得更为礼貌——因为礼仪也是威慑的一部分。
在古代,帝王和贵族是礼仪的专有者,孔子所说的“礼不下庶人”正是这个意思。
到了现代,教养和礼仪也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一个为富不仁的家伙只能得到“暴发户”的讥讽,而那些谦恭处世的大人物才更受尊敬。这其实是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表示自己的优势地位明显,用不着和低下的人计较。很多女权主义者激烈抨击所谓“绅士风度”,正是因为在她们眼里,这是“男性霸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在身份平等的人群中,礼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路遇时,我们让别人先走;碰撞时,我们抢先道歉;在比赛或其他场合获胜时,我们谦虚地恭维对手。这就表示着:“我是一个绅士,是这个社会体系的维护者和受益人。”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那些乞丐们为什么要遵循这一道德体系行事呢?他们不是受益者,为什么还要维护它?
第一个原因是:如果他表示出愿意依从强势者的道德,做个“合作者”,就比较容易得到怜悯。
第二个原因是:他不敢过于违反这一道德体系,因为除了道德,这个社会还有法律武器作为威慑。前者是一根胡萝卜,后者是一根大棒。当两者发挥效力时,这个乞丐就会照此行事。可是,如果胡萝卜的引诱和大棒的威慑都不足以抵御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欲望时,这个身份低下,毫无地位可言的乞丐也许就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可怕威慑力的罪犯。当然,他通常会受到惩罚,但无论是犯罪还是惩罚犯罪,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要大于容忍一个乞丐的浪费。
由此可见,“乞丐的礼貌”也是值得赞赏的,值得鼓励的。
该不该废除死刑?
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许多过去似乎天经地义的规则都受到了挑战。例如,“杀人偿命”,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死刑是对罪大恶极的罪犯的最合理的回报,然而现在这一观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
对于死刑的最根本质疑是:谁有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一个凶犯剥夺他人生命是错的,那么剥夺这个凶犯的生命的合理性又在哪儿?对死刑持质疑态度的人们还指出:死刑完全剥夺犯罪者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由于这一严酷惩罚的不可逆转性,一旦发生冤案便难以挽回等等。由于以上理由,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美国的一些州也是这样。
这些置疑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看到,死刑尽管不可能消除犯罪,可是它的威慑作用对一个社会的稳定确实是重要的。当然,仍然有些人心怀侥幸,甚至不顾送命的危险而犯重罪,死刑并不能震慑住所有人。但是,比较之下,终生监禁之类的震慑力显然就更弱。
死刑意味着什么?它是表示开除某个人在世界上继续生活的权力。如果这个人已经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人们是否应该行使这个“开除权”?想一想,在一个小圈子里,一个人得罪了大家,人们可能会不理睬他,把他开除;在一个组织里,如果某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该组织,他也会被开除,死刑与这些不同的是,它不但“开除”某人,而且从肉体上“消灭”某人。这似乎有些专横和残酷,但却是不得不然的,因为这是唯一可靠的“开除手段”。
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者、民主党人杜卡基斯主张废除死刑,他一度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于布什。但是有记者尖锐地提问:如果有人强暴并杀害你的妻女,你是否仍然坚持这一主张?他十分尴尬,表现令人失望。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他最终输掉竞选的原因之一。
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许会遇到更多尴尬,比如一旦发生战争,是否要抵抗?如果即使经过审判我们也没有杀死一名重犯的权利,又何来未经审判就杀死对方士兵的权力?
其实,“谁有权剥夺他人生命”也许根本就是个假问题。我们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对等回报上的。死刑的实际含义是:人有自卫的权力,如果某人对他人或公众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政府和法律不过是代表公众完成这一回报而已。
“死刑应废除”的假设前提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性区分利弊,并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遗憾的是这很可能是错的,人类的非理性观念和行为十分普遍,尽管不愿意,但我们必须承认指给我们正确方向的老师不是道德和理性,而是欲望和禁忌。
死刑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消失吗?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每个人都能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自由,废除死刑才顺理成章。而这至少在现在看来还只是奢望。
死亡也是合理的吗?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更重要的生命。其实,最为我们厌恶的,似乎也是最不合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有一死。我们该不该寻找一种技术,使我们能永久地活下去?
衰老和死亡,这似乎是一种耻辱,但又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像人这样的生物实际上注定要变老和死亡,因为我们的细胞似乎由它们的基因“编制了程序”,逐渐地经受着被称为衰老的那些变化。
衰老有某种用处吗?衰老有什么益处呢?
生命的最惊人的特性,除了单纯的生存之外,就是它的适应性。在陆地上、海洋里和空气中有生物;在温泉里、咸水里、沙漠上、丛林里和两极的荒芜地区以至各处都有生物。为了获得这样的适应性,基因结合物和基因性质本身必须发生经常性的变化。
单细胞生物进行分裂,两个子细胞都有着原细胞所具有的基因。如果基因能够作为完善的复制品通过一次次分裂永远传递下去,那么,原细胞的性质就决不会发生变化,不论它的分裂和再分裂有多么频繁。然而,复制品并不总是那么完善;有时会发生无规则的变化(变异),而且逐渐由母细胞产生不同的品系、不同的变种,最后形成物种(进化)。某些物种在某种环境里比其他物种能生存得更好,因此不同的物种占据着地球上不同的小环境。
有时,各个单细胞生物之间互相交换染色体。这种原始形式的性行为导致基因结合物的改变,而这又进一步加速进化发展。在多细胞动物方面,两个生物互相合作进行有性繁殖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变异能单独造成变种外,不断产生带有基因的幼体,也能形成变种。结果,进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而新形成的那些物种能更容易地散布到新的小环境,或者使它们本身更好地适应旧的小环境,从而比从前能更有效地利用小环境。
因此,其关键就是产生带有新的基因结合物的幼体。某些新的基因结合物也许很拙劣,但它们的寿命不长。那些非常有用的新的结合物能够“成功”并排除竞争。然而为了办得更成功,带有“未经改进的”基因结合物的较老的一代就不应留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肯定,上了年纪的生物总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死去,有的是由于事故造成,有的是由于生命消耗殆尽所致,但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这个过程。
其早期几代具有预定要衰老的细胞的那些物种会更有效地促进新陈代谢。幼体就会进化得更快而且更成功。我们能看到我们周围的生物长寿所造成的不利因素。能活数千年的红杉树几乎灭绝了,长寿的象几乎没有短寿的老鼠那样能适应环境;或者说,长寿龟没有短寿的蜥蜴那样能适应环境。
为物种(甚至人种)着想,似乎最好是老了就死去,而让幼者生存。这令人感到很遗憾,但事情似乎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