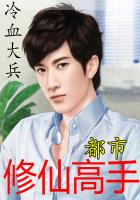介绍一个著名人物时,往往采取生平介绍法,即生卒年月,家族出身,学习经历,师从何人,有何作品及不平常的遭遇等等。同样,介绍一种思想,也要看它的出身甚至基因,这和马克思早期成长过程的诸多材料不是一回事,况且那些耳熟能详的资料也不用再重复。我是出于对马克思思想家族背景的认识,来分析这一伟大精神创作还有哪些我们没有大胆探索过的区域,也许这可以叫作“回一次老家”。
一、综合性吸收的典范
我们习惯地以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是最大的,这在历史的角度是没错的,但是从逻辑的角度,我们看得还是太窄。黑格尔本人曾经说过:“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古希腊的“三贤”,而亚里士多德又是集中的代表,因此,我们有更多的文本和学科体系都直接与他连在一起。比如《形式逻辑》就是很重要的一科。那么,在这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人文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给学生上课,一讲到哲学,总是要先告诉他们: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样抽象的定义,对一个没有多少生活阅历和观念积累的年轻人来说,我保证他们只有“言词”上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外在的判断语。我主张,今后不要这样急功近利,不是要讲马克思嘛,还是从他思想的老家讲起吧。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正因为自由,我们就不能怕麻烦,允许所有的人去思考任何自己能想到的事情,从任何的角度来追问所有的问题。好了,一连串的烦恼都来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应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问题大多有答案,而且只有一个答案,比如:1+1=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它一般没有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的解答方式,而正是因为它们最终谁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具有功利性和有用性。但是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们爱智慧是不是就能成为有智慧的人呢?显然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有智慧,实际上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
翻开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互相争论,但是争来争去不但没有结果,反而越争问题越多,哲学非但没让人聪明,反而让人越来越糊涂了。有人可能会嗤之以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但它们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但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比如“我是谁”的问题。成龙有一部电影叫《我是谁》,主人公大脑受到伤害,失去了记忆,结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我们没有受过伤害的大脑来说,如果仔细追问,也不见得能回答出来,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逐渐成熟,身体也在不断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那么我与自身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与推敲的。
《圣经》关于亚当犯原罪的说法实际上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智慧的痛苦。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智慧的痛苦就在于此,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哲学问题正是从这里导出的。人始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千百年来人们上天入地,建功立业,改造环境,繁衍后代,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一理想,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路。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也是人成其为人的先决条件。也难怪有人把哲学叫作“关于死亡的学问”,而哲学家就是“经常练习死亡的人”。如果我们从这里引领学生走入哲学的殿堂,开始愉快的精神旅行,最后再得出哲学的规范定义,效果肯定要好上十倍。
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与学生们讨论哲学问题,所以人们称之为“漫步学派”,也叫“逍遥学派”。据说他的全部著作多达一千多卷。他的学问内容广泛,涉及逻辑学、自然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几乎覆盖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是《工具论》、《形而上学》、《论灵魂》、《政治学》等篇章。难怪黑格尔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同时也吸取了他的思想精华。这种博大的胸怀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善于吸取别人的思想精华的,后来的马克思更是如此。这一点,柏拉图就完全不同,他对以往的学说不屑一顾,只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哲学领地丰富而自由的表现。
对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亚里士多德评论说:德性不只是一种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行为。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勇敢是什么,而是还要成为勇敢的人,不仅是要知道正义是什么,而还要成为正义的人。我认为,马克思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种以身践行的品质。曾有人指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距离要比与黑格尔的距离还要近,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因此,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理解的时候,用不着去人为地建立体系,因为在所有我们认为缺少文本的地方,都有他的行动做出了有力的补充。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取是大家熟悉的,况且后面还有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对于康德还是要说一说,因为我们在正面宣传教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样一顶帽子总是让人觉得不太恰当,也太简单。我们都知道,没有康德的“二律背反”就不会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绝不是只接受了黑格尔的现成果实,况且这种果实也不是直接能拿到的,他必定对黑格尔的“艰难跋涉”是非常了解且高度认可的。实际上,康德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开路人。从恩格斯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确认这一点:“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著名学者邓晓芒在2004年将康德的“三批判”直接从德文译成了汉语。他说:“我深感康德哲学代表着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理性传统,那种对语言、逻辑的一丝不苟和严肃认真,那种对问题、矛盾的穷追不舍和殚精竭虑,那种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超越精神,都令人惊叹。这种优秀传统,我们今天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和诠释学中,在现代西方一切思想大家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但如果没有经过康德哲学的训练,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肯定不会深入。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康德哲学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以往的哲学都流入到它里面,以后的哲学都从它里面流出。”
不难体会到,这样一位公认的思想大师,我们只把他当作不可知论者实在是不公平。在我看来“不可知论”这个哲学概念就值得怀疑。尽管现在的公共课教科书已经去掉了这个内容,但是,在其他非官方圈定的教材中,以及学术领域内,一说到不可知论,仍然是西方的休谟和康德、中国的庄子。我认为,把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表现,也就是心物二元论,定为不可知,有一种武断消极的意味。我们随便翻开一本教科书,都能看到这段著名的引语,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我们看,这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不可知论”这个所谓术语。只是在这段话之前说过:“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而在这段话之后才提到:“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在我看来,不管是对休谟还是对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等等哲学的评价,“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这才是落脚点。羞羞答答,并不是有什么短处而不好意思直接承认,而是就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说,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能接轨。他们(至少是康德)要为自己的学说负责,而这种学说又与工业无产阶级这个社会实践的“大写的主体”相距较远,因而只能谨慎前行。“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当众加以拒绝”,那只是面子问题,是从学术尊严上考虑的。况且,恩格斯已经断定“新康德主义”和英国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那么,剩下的还能是什么呢?只能是“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为“为我之物”了。如果康德活到马克思那个时代,他仍要坚持“自在之物”的永恒性(这从康德的著作中并不能直接看到),那时,我们再给他一个“不可知论”的恶名也不晚。我想,这样一个顽固不化、令人讨厌的学人绝不会是康德。那好,我们以后就把“不可知论”这顶帽子给他摘去,以便发现和吸取他思想中更多的精华。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对那些“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是怎么说的呢?马克思在谈到实践这个概念时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能不能说“神秘主义”就是“不可知论”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当我们对一个客体还不能做出确定性判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神秘感。实际上迷信思想都是这么来的。我们先来分析马克思的这句原话,“神秘主义”或“神秘东西”“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也就是说从神秘到不神秘,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只要了解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那么,神秘的东西就可以换一个词来描述了,那就是“尚未被认识的东西”。
在我看来,马克思从康德那里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比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少。特别是从康德的宗教哲学那里,应该获得了更大的教益。因为正是这一部分是专门研究人的。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意志,其核心就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在方法上运用了黑格尔的路径,但是黑格尔的异化观点,在内容上要比康德的论述离现实生活远很多。康德认为,有了自由意志的人就会有信仰,宗教是从道德里推出来的,有了道德就一定会有宗教。但道德比宗教要更基本,它是宗教的基础。道德本身可以没有宗教,但宗教不能没有道德。道德本身是自足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会逐渐地走向上帝,走向宗教。他的这种理念和主张,也是他以身践行的。因为当时的神学家、教会都谴责他,说他把道德看得比宗教更基本。他的书也因此遭到查禁。国王亲自批示,禁止他以后谈宗教问题。康德还写了一份检讨,说我保证作为您的臣民,以后再不讨论宗教问题。但过了两年,国王死了,而康德在检讨中打了埋伏,作为你的臣民,我不再探讨宗教问题,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臣民,你已经死了嘛。康德后来又探讨宗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