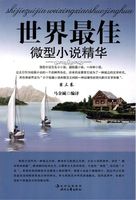仇梅进门看一眼公公,就把目光落到病房的花篮上。她一个一个数了数花篮,没忘把邻床的花篮也数进去,然后指着花篮对丈夫说:“哪个送的都记下了吧,人家有事要如数偿还的,懂吗?“
“记下了。那是肯定。”秦怀阳尽量抹仇梅的顺毛驴。
“我马上有优课评比,忙着加班备课。”仇梅脸子冷冷地自言自语。秦怀阳心里一阵疼,但疼过之后还是想给仇梅作揖,求菩萨保佑:“好的,这里有我顶着,你安心备课吧。”
仇梅从一进屋还没跟秦木石打招呼呢,临走前站在秦木石床头,但她不敢看一眼公公的眼睛,因为秦木石的眼睛里充满着对儿媳妇的愤怒。仇梅没有任何称呼交待说你想吃什么就叫你儿子弄什么吃,山珍海味他都能买得起,他有的是钱。”
秦木石知道好歹,点头答应说:“你忙吧。”
仇梅转身走了,前后不到十分钟。
邻床一个老太婆问“她怎么空着两手来去呀,是你儿媳妇?”
秦木石说”我的冤家。”
秦怀阳听了心酸,躲到一个角落里数了数信封里的钱。
正像仇梅说的,这些人情债都要还的,但起码眼下可以贴补爸爸的住院费了。但钱进了医院全变成龟孙子了,医院就是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的。秦木石病情不稳,手术还不能马上进行,必须把血压等指标控制好。原先没病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査出癌症来了,墙倒一齐推,破鼓一齐擂,什么都来了。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秦木石简直跟城里的富人似的,一身的富贵病,其实那是一种综合症,但必须把三高稳定住才能动手术,否则会很危险。这样一来,就怕秦怀阳的钱少了。一天一遍对账单打给秦怀阳,钱像让天狗偷吃的月亮,见鬼似的缩小。手术还没做呢,又要再去交钱。
催交单子是秦怀阳不在爸爸身边护士递给秦木石的。秦木石识字,看完单子,等儿子回到病房,就对儿子说简直比拦路抢劫还狠,这病不治了。治也治不好,瞎让你背一屁股债。”说着就把腿伸下床,要走。
秦怀阳摁住爸爸:“你别瞎操心,我不会欠医院钱的。”
“你到哪去抢银行呀?”
“这你别管。”
秦木石安静下来。
秦怀阳走出病房给孙兰打电话请你来时再带点钱来。”
孙兰送饭的时候又送来一万块钱,临走时说你身上有一股臭味了,还不回家洗洗澡?’’
秦怀阳笑了笑:“没法讲究那么多了。”
晚上,秦怀阳头脑发涨,一趴到床头就睡着了。
秦木石推推他,催儿子说回家看看去,别给你也熬出病来,别冷了媳妇。我这里自己能照顾自己。”
秦怀阳睁开眼,恍惚过了一个世纪,心里除了爸妈,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他迷迷糊糊的,真的想回家洗洗澡换身衣服。久病床前无孝子,秦怀阳不想成为这句话的注脚。他太想把爸爸的病治好,尽管不可能治好。他这些天光顾着给爸爸换衣服洗衣服,自己居然没回一趟家。他怕进家仇梅就不放过他,等着他的肯定是那些不吃粮食的屁话。但是他回到家,发现仇梅却不在家。他洗了澡,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秦怀阳一惊,自责太大意,于是直奔医院。到病房才发现爸爸不在,邻床病人说一早下楼转去了。秦怀阳“咚咚”跑下楼去找。平时他会带着爸爸在楼下花坛里转悠,他以为爸爸还在那里转悠,但到花坛里找遍了,也没发现爸爸的影子。秦怀阳心慌了。
秦木石会到哪去呢?
秦木石此时正走在去天堂的路上。
马家湾的早晨,又一只刚蜕了壳的蝉,爬上村头老榆树树梢,扯开嗓门高唱起来:
“咝——m——咝—”
秦木石从中巴车上走下来,徘徊在老榆树下。他摘下树干上的蝉壳塞进嘴里嚼起来。他背靠在老榆树根下,面向着太阳。从榆树叶间射下的一缕阳光照在他灰白的脸上,他感到一丝温暖。也许是难以下咽,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仰起脖子,嘴对嘴,咕噜咕噜喝下去。
呀嗨哟,
呀鳴哟,
咿嗨咿嗨呀嗨哟——
秦木石的身子就像定向爆破的烟囱,一节一节塌下去,在老榆树下慢慢蜷成一团。
当马姓人发现秦木石时,秦木石已经死了。
秦木石是喝农药死的。自从得病,秦木石就在身上藏一小瓶农药,预备着。他曾跟老伴说:“我要死就死个干脆。”可谁想到他会喝药死呢?
秦怀阳接到妈妈电话回家,扑向已经躺在堂屋当门心的爸爸大哭。人们把他拉起来,他跪在秦木石身边卖呆发愣时才知道爸爸的死亡过程。
怀恨在心
孙兰从马家湾吊唁秦木石回运河市,仇梅爬上她的车也跟了回来。孙兰一路上没话。仇梅也一路上没话。因为在仇梅爬上车时孙兰带气说了仇梅一句“果果姑姑,你不该撇下秦怀阳回来。你跟我们不同,你是秦家媳妇。死者为大,你应当给公公捧棺下地以后再跟秦怀阳回城。”
仇梅说了句”我没那个工夫!”
孙兰就等于把仇襦给了仇梅。
仇梅当然生气不理孙兰了。
在马家湾,仇梅和普遍吊客一样,既没在秦木石的棺头烧纸礎头,更没陪着秦怀阳守灵,早早钻进丧棚里坐着等开席,吃完饭就躲到院子外面的树阴下乘凉。孙兰为秦怀阳难过。仇梅没给秦怀阳争一点面子,简直还不如一个路人,连起码的做人道理都不懂,哪里还有夫妻的情分?孙兰怎么也没想到仇梅会对秦怀阳如此薄情寡义。联想到秦怀阳曾经征求她意见时的情景,联想到秦怀阳花斑蛇一样的胳膊,特别是联想起仇金玉抢走果果,孙兰对秦怀阳充满愧疚,对仇家充满仇恨。
回到运河市,孙兰把车径直开到公公婆婆家楼下,一是送仇梅回家,二是想把果果接回自己的家。仇梅吃住在娘家,孙兰是知道的。仇梅下车就往楼上走,一句招呼都没打。孙兰泊好车后上了楼,进门拉起正在客厅里玩小狗的果果说,“妈妈,果果我带回去了。”
刘丽从卧室跑出来“不行,带走你爸回来又要发疯了。要带走必须他同意。”
孙兰撂下脸子,“妈,我是果果监护人,带孩子还要谁同意!岂不笑话!”
“哟,说话牙齿紀地了,你在跟谁说话呢?”刘丽立即变脸了。
仇梅说:“妈,你就让她带去吧。”
“我偏不让她带去!”刘丽上来拉扯果果,“你给你爸打电话,就说小孙要抢果果。”
—个拉,一个扯,谁也不让谁,果果快撕成两块,疼得哭了。这时最能看出谁最疼爱果果了。孙兰最先松了手。果果落入刘丽怀抱。但孙兰终于忍不住说“你霸占果果是不是为仇杰今后跟我离婚的?”
“谁说的?”
“仇杰自己说的。爸爸也对马明侠说过这话。妈,你们根本没拿我当你们仇家人!”孙兰说出的话像打着摆子,疙疙瘩瘩颤抖着。
“是,你又能怎么样!”
孙兰二话没说就冲出门下楼,怎么回到自己家里的,一点也记不得了,头脑早气得昏掉了。她决心不再去公公婆婆家看果果,在煎熬中咬牙坚持着。同时,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向秦怀阳和盘托出仇梅堕胎那些丑事。
至于仇金玉挪用公款投资的事,孙兰还没想捅出去。
情至深处
孙兰的机会来了。
就在她从马家湾回来的第三天晚上,秦怀阳敲开了她的家门。
“哎呀,真是鬼气,家门怎么也打不开了,锁好像是让人给换掉了。我只好到你们家来借宿了。”秦怀阳本来单薄,一连这些天折腾,落魄得鸠形垢面,更瘦更黑。
孙兰说这家人都拿人当贼防了,真不是东西!”
秦怀阳长叹一声”莫名其妙。仇杰呢?”
“招商去了。你先洗把澡吧,糟蹋得不成人样了。”孙兰找出一条新毛巾,换了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不是因为专为秦怀阳的,而是因为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各用各的,不想让秦怀阳用自己的用品,更不能让秦怀阳用仇杰的用品。秦怀阳两手空空来的,洗澡不换衣服还不如不洗哩。孙兰就从衣柜里找出一套没拆封的新衣服。这套衣服既不是仇杰的,更不是专门为秦怀阳准备的,而是平时逢年过节或开会发的纪念品,大大小小的还有不少,孙兰找了一套估计合秦怀阳穿的,递给秦怀阳。
秦怀阳去卫生间洗澡。
孙兰开始收拾卧室。这个卧室原来是妈妈住的。妈妈走后,床上的东西都揭掉了。幸好现在天气还热,不需要厚被褥子什么的,否则还要把收藏好的被褥拖出来,麻烦,用一次也要洗一回的。孙兰简单把凉席抹千净,找一条方方正正的薄被放上去,又换了一个枕头套子,就算好了。
孙兰又走进厨房忙碌。
自从妈妈回去,仇杰冒失鬼似的,三天两头见不到人影,孙兰吃饭也就有一顿没一顿的,冰箱里放着菜,但一个人懒得做,想去食堂吃就去食堂吃,不想吃就什么都不吃,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饿不饿,也没人知道。特别是这几夭,她一想到仇家人防贼一样防着她,心U就堵得难受,哪里还吃得下饭?今晚就打算喝一袋牛奶凑合一顿的,不料秦怀阳来了。秦怀阳还是第一次到家里来,而且要在这里借宿。孙兰把冰箱里的菜拿出来,打算做几样给老同学兼果果姑父补一补。这阵子秦怀阳肯定饥一顿饱一顿的。忙了没多会儿,孙兰居然感觉自己的心气顺了,肚子也饿了,嗯,心情宁静了许多。
“你干什么?”不知多会儿,秦怀阳站在厨房门口问了一句。
专心致志切菜的孙兰手一抖,差点切到手指头‘哦,吓我一跳。正好,我还没吃晚饭哩,你肯定也没吃吧?”
秦怀阳说没吃。”
“你去休息一下,我做好了喊你。”
秦怀阳应声转到客厅里,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有好久没看电视了,他一直关注国际国内新闻,记忆中的新闻如今早就过期了。但秦怀阳看着新闻却一点也没进脑子,紧张这么多天,刚洗完澡,一下松滞下来,眼皮子马上重得像两扇石门,钎子都撬不开了。电视还在播着,秦怀阳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孙兰走出厨房看到秦怀阳睡着了,便轻手轻脚走过去,拿过遥控器关了电视,又到卧室里把那床方方正正的薄被拿来给秦怀阳搭在肚子上。秦怀阳居然像没根的草,薄被那点重量轻轻一压,身子就倒下了。孙兰突然想起一根稻草压死胳驼的话,心底一笑,弯腰把秦怀阳的双腿搬上沙发,再把薄被展开盖上他的全身,又顺手关了客厅里的灯,这才回到厨房里做菜。
菜做好了,孙兰却没有叫醒秦怀阳。她把菜盖好,把红酒开好,然后就坐在桌边等着,就那么静静地等着。
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孙兰坐在幽静的黑夜里守着一份孤独和宁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没有丝毫的困意,也没有丝毫的不安。她无论如何都要等到秦怀阳醒來吃上一顿可口的晚餐。
孤男寡女独处一室,肯定会有故事。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孙兰平静地期待和安排着情节。想起秦怀阳走进人事局办公大楼站在正己镜前的情景,想起自秦怀阳到人事局以来局里和仇家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孙兰对人生产生一种困惑感。谁能想到彼此好感的同学会成为一家人呢?阴差阳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但是,他们在仇家都同样没有地位。仇家防贼一样防着他们呢。他们同病相怜。她的痛苦来自于知晓仇家内幕太多却不敢说,秦怀阳的痛苦来自于仇梅的奴役却不知道内情,但他们都有一个在权力淫威下呻吟的灵魂,遗憾的是他们缺乏彼此沟通,更没有抱团对付权贵的勇气。然而,今晚孙兰就要把仇家的内幕和盘托给秦怀阳了。孙兰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嘀嗒,嘀嗒,时间的脚步在静夜里踏过孙兰的心田。
在一片寂静里,孙兰享受着渴望倾诉的兴奋和即将到来沟通的快乐。突然,她听到秦怀阳大喊一声“妈妈,我带你离开这鬼地方!”声音里带着哭腔,吓得她浑身汗毛直竖,顺手开亮了灯,她才看到秦怀阳坐在沙发上卖呆发愣。
“你做梦了吧?”孙兰走过去问。
秦怀阳幽幽地说:“嗯,爸爸死了,我想把妈妈带进城里来过。打电话给仇梅,她死活不同意,还说哪里有我家,我是大麦去皮光人。唉,我家本来在马家湾就孤门小姓受人欺负。我太对不起妈妈了,把她一个人丢在马家湾,我不放心啊!”
孙兰说:“迟早你都要把婶子带过来的,不然,为儿为女的还有什么意思?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秦怀阳来到餐桌边坐下。孙兰给他和自己各斟了一杯红酒喝起来。他们碰杯喝酒,谁也不说话。没有外人,目光可以肆无忌惮,照映出各自的心跳的,但也彼此回避着。喝下几杯红酒以后,终于憋不住了。
“孙兰,你在仇家过得好吗?”
“不好。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去。”
“我总感觉这家人把任何人都当成敌人,当成了贼,他们是怎么了?”
“哼哼,怎么了?有权有钱烧的。”
“你比我强。我是外人,你是家里人。”
“强不到哪去,一样都是外人。哎,你感觉仇梅怎样?”
“一言难尽。想不到为人师表的女人会像一个恶魔。”
“哼,她有什么资格对你横鼻竖眼的丨”
“她出身高贵呗。”
“其实她比谁都贱。”
秦怀阳直直看着孙兰,目光在问孙兰,此话怎讲?但孙兰转过脸去,然后突然伸出酒杯来碰秦怀阳的酒杯:“来,喝酒,不说她了。”
“不行。你肯定有什么瞒着我。孙兰,我们是老同学,你不该有什么瞒着我。”秦怀阳放下酒杯不喝了。
孙兰说”这话该烂在肚子里一辈子的。可仇家欺人太甚,从来拿人不当人,我也就不给他们要面子了。秦怀阳,难道你没感觉到,仇梅跟你结婚时没有什么不一样吗?”
结婚时仇梅的处女红一直像一朵不败的桃花开在秦怀阳心底,尽管婚后生活总是不和谐,但秦怀阳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仇梅是干干净净的。听了孙兰的话,秦怀阳皱起眉头“你是说她作风上有问题?”
于是,孙兰把仇梅几次堕胎的事说出来。
秦怀阳无地自容,趴到桌子上抽泣,不愿抬头。
“我前天还看到她跟你们婚礼上献花那个男的在一起吃饭的。”孙兰继续说。
“砰”,秦怀阳一拳打在桌上,差点震翻了碟子:“别说了,我要跟她离婚!”
孙兰笑笑说”你没那个胆。”
“我怕什么?”
“除非你不想在官场上混。”
“头顶绿帽子,就是在官场上混出个人样来,也让人戳脊梁骨。”孙兰站起来收拾碗筷抹桌子快去睡吧,天不早了。你要是想步步高升,你就当好缩头乌龟。你要想无所作为,你就离婚。你掂量掂量吧。”
躺到床上,秦怀阳据量来推量去还是咽不下一口气,更睡不着觉,脑子里放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回放着进入人事局以来的境遇。难道其间就没有思考过仇金玉为什么会把漂亮的女儿许配给自己?想过。但他从来没往坏处去想。这种事情为什么偏偏受害者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呢?孙兰为什么不早告诉自己,却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呢?
秦怀阳…夜未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