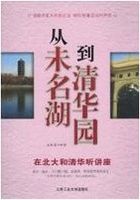原本在前一封信里和母亲说的好好的,今年春节一定要回家过年,吃吃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饺子,看看几年没见的母亲是否又添了许多的白发,听听侄子们高高兴兴的笑声随鞭炮一同炸开的喜悦,让自己沉浸在淳朴的乡情和民风之中,唤醒已有些麻木的灵魂。但单位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毫不留情地拖住了我梦想中早已迈进那个山村的脚步。
于是我只好再写一封家书。往常写信,收信人都是大哥。信写好了,也封好了,当正要写下大哥的名字时,窗外传来了忽远忽近的“常回家看看”的旋律,在夜深人静的月光中,我的泪水悄然无息地夺眶而出,于是我决定在这封家书上第一次写上母亲的名字。
当母亲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心颤动了,啊,母亲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与我记忆中孱弱的身材、蜡黄脸庞的母亲本人,根本无法相比。
于是,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那个从未走出大山深处的小山村的母亲,从千里之外向我蹒跚走来。
母亲的名字很慈祥。
母亲慈祥的名字上,曾经飘满了晨雾。她常常比太阳起的还早,去采摘带露的野菜。母亲闯入浓雾之中,一点点驱散了雾气,但母亲的头上却沾满了露水。
母亲慈祥的名字上,充满了母爱。她常常轻轻地走到我熟睡的炕边,弯下腰,轻轻地唤我,生怕惊吓了她的孩儿,然后帮我穿衣穿鞋,在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悄悄地将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一把黄豆或一块土豆塞进我的口袋,一遍一遍地叮嘱我,放学后早点回家。
母亲慈祥的名字上写满了牵挂。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站在村口那棵百年老榆树底下,耐心的等待,焦急的翘盼,直到她孩儿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时,她便飞也似的迎上前来,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回家,母亲从来都是这样等我回来。
母亲的名字很动人。
母亲动人的名字上,积满了许多的泪水。苦难的日子,母亲是一座最能忍受的大山。母亲忍受过父亲烟锅里的唉声叹气,忍受过父亲在油灯下爆雨般的拳头,忍受过她的孩儿们饥饿的哭喊、无助的眼神。父亲无情地撇下我们,过早地融入了黄土,只有母亲含辛茹苦的同岁月抗争,和我们相依为命,用她生命的付出,实践着她“宁肯挣死牛,不叫翻了车”的承诺。
母亲动人的名字上积蓄了无数纯洁的月光。借着那月光,母亲总是有做不完的活计。不是缝补我们破烂的衣服,就是纳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我们的,父亲的,唯独她自己的很少很少,那悠悠长长的丝线连同皎洁的月光,连同母亲对我们的感情,一起被母亲纳进了鞋底。
母亲动人的名字上也曾经写满了喜悦。那是她的孩儿第一个从小山村凤凰般飞出的时刻,母亲手捧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在众人羡慕的眼光里,泪流满面,号啕大哭。
今夜的月光,格外的温柔亲切。我把湿润的目光和思绪从遥远的山村收回来,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今往后的家书,一律写上母亲的名字,用一声声儿子亲切的呼唤,让母亲的名字更加光彩;用一声声儿子深情的呼唤,唤回母亲曾经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