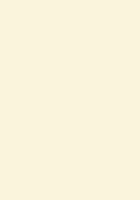又一天,父亲也出门了,我问父亲去哪里,父亲仍说去找小刚,但这回父亲没去抚河边,而是往村后山上去。我跟着父亲,还说爸爸你去山上做什么呢。父亲说小刚在山上呀,我去山上找他。我说哥哥不在山上,哥哥怎么会在山上呢。父亲说谁说小刚不在山上,我记得他以前天天上山砍柴,你说是不是。我点点头,我说以前哥哥天天都上山砍柴。父亲说既然小刚天天都上山砍柴,我怎么找不到他呢。说着,我们走到一处山崖了,在那儿父亲要往下爬,我慌忙拉住父亲,我说爸爸你不能再往前走呀,前面是山崖,很危险。父亲说危险什么,我记得以前村里的杏花滚下了山崖,是小刚爬下去把她救上来的,是不是。我又点头,说是。父亲说既然是,我就要去下面找他。我说爸爸你不能去,我们在上面等他吧。父亲看看我,点点头,在那儿站着,等着哥哥。
但父亲失望了,父亲哪里等得到呢。
有几天父亲没去河边也没去山上,父亲只在村里转,一副找人的样子。有人问父亲找谁,父亲说找小刚。村里人听了,眼睛一红,村里人都知道小刚在抗洪时牺牲了,有人跟父亲说在村里找不到小刚,父亲说怎么找不到,我记得以前村里惊了一头牛,疯跑,就要踩着五毛时,小刚过去抓住牛角,推开牛,是不是。村里人说是。父亲说既然是,我就找得到小刚。村里人听了,不做声了。晚上,父亲还是坐在电视前,父亲依然希望在电视里看到哥哥,为此,父亲每晚每晚都盯着电视一动不动。一天,父亲看见一个抗洪抢险的场面,堤上全是穿迷彩服的军人。父亲看着,突然眼睛一亮,然后叫了一声,父亲说:“你看,那不是小刚吗?”
我侧头去看,但画面变了,我便说哪里呀,那不是哥哥。父亲瞪我一眼,父亲说:“真的,那是小刚,我没看错,小刚跳进水里,在抢险哩!”
我眼里一片潮湿。
父亲第二天出去,精神明显好了,父亲见了村里人,跟人家说:“我看见小刚了,在电视里,他跳进水里,在抢险哩。”
村里人听了,都流泪。
一个女孩儿叫张云
文/刘国芳
他在街头一次次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父亲多么盼望能有人脆脆地回答一句“哎”呀,但女儿张云没有出现,街上只有父亲孤独的呼唤。
一个女孩儿出生了,女孩儿的父亲要为女孩儿取名字,做父亲的拿出字典来,把一些可以做女孩子名字的字找出来写在纸上:青、琴、芹、云、影、韵、兰、荷、梅、莲、菊、风、霜、雨、雪、雾等等。父亲姓张,把那些字列在纸上,他又逐个把姓连起来:张青,张琴,张兰,张梅……念了许久,父亲还是不能确定女孩儿叫什么好,最后,父亲把那些字拿给还在坐月子的女孩儿的母亲看,做母亲的看了许久,开口说:“还是叫一个简单好记的吧,我看叫张云就很好。”
就有一个女孩儿叫张云。
此后,做父亲的便整天“张云张云”地叫:
张云饿了,给她喂奶。
张云乖,不哭。
张云会笑了。
到张云大些,父亲同样整天叫她:
张云,吃饭了吗?
张云,帮爸爸拿双筷子。
张云,帮爸爸买包烟。
张云还大些,父亲照样天天叫着:
张云,下雨了,快去帮妈妈送伞。
张云,中午你自己煮饭吃。
父亲任何时候喊张云,张云都脆脆地“哎——”一声,父亲让她做什么,张云就做什么。为此,在父亲眼里,张云从来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但有一天,张云不听话了。
张云找了个对象,父亲不同意。父亲跟张云说:“张云,找对象的事不要太急,再缓缓,会碰到更好的。”张云说:“我就觉得他很好。”父亲说:“他连工作都没有,好什么好。”张云说:“难道没有工作的人就不要找对象吗?”父亲说:“没有工作,他拿什么养活你。”张云说:“我自己有一双手,我怎么会要他养我。”父亲说:“到时候过苦日子可别后悔。”张云说:“我不后悔。”父亲说:“我这是为你好。”张云说:“你为我好就别干涉我。”父亲说:“这件事我就要干涉你,我不同意你跟他好。”张云说:“你干涉也没有用,我就要跟他好。”
那段日子,父亲每天每天都跟张云说这些,但没有一次说动过张云。有一天父亲就生气了,父亲说:“你要跟他好,就滚出去,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张云就抹了抹眼泪,跑了出去。
父亲在张云跑出去时,“张云张云”地喊起来,但张云没回头,跑走了。
张云离开后再没回来。
父亲每天都盼着张云回来,而且天天“张云张云”地喊着,但没人应他。后来,父亲就去报上登了寻人启事。父亲在启事上说“父亲错了,张云你回来吧”。把启事登出,父亲甚至又把字典找了出来,他想如果张云回来了,就让他们结婚。等他们有了孩子,他还给孩子取名,父亲于是又把一些可以做名字的字写在纸上:青、琴、芹、盈、影、韵、兰、荷、梅、莲、菊、风、霜、雨、雪、雾等等。
父亲觉得上面哪一个字做名字都好听。
但张云还是没回来。
父亲只好天天上街去找。
有一天父亲就在街上听到一个人喊:
“张云,张云——”
父亲睁大了眼睛。
但应声的,只是一个小女孩儿。
一个也叫张云的小女孩儿。
但父亲还是跟着这个小女孩儿走了很远。后来,小女孩儿发现父亲跟着她,就回头问了一句,小女孩儿说:“大伯,你怎么跟着我?”
父亲说:“我也有一个女儿叫张云。”
说着,父亲流泪了。
我请父亲吃饭
文/陈韶华
他们的心还是连在一处的,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无时无刻不在默默地关心着对方。
请父亲吃饭,怎样请父亲吃顿饭,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他整日侍弄花草,以花为伴,孤独生活。他生性耿直,少言寡语,脾气不好,与儿媳们的关系总处不好,也不愿与我们住一块儿。父子难得一聚,只有逢年过节,弟兄们吃酒,人多时,才把他也请来。
说实话,多少回,我总想把父亲单独请到我家,一家老小好好吃顿饭,但鉴于他曾多次得罪过我妻子,话到嘴边,又怕再引起家庭风波而难以启齿。好在北京还有三弟、四弟、六妹,父亲时时北上京城,两头居住。
这一次,三弟在北京的公司门面多,实在太忙,三番两次打电话,催父亲去救急帮忙。父亲年事日高,往返也跑怕了,想已下了决心,对我说:“老大,你喜欢什么花就都搬走吧,余下的花草我全都散给邻居们,这次去北京,我可能就不再回来了……”父亲的声音中,分明有几分掩盖不住的酸楚与无奈。
行前,我说:“爸,我请你吃顿饭吧!”父亲说:“好啊,在哪儿?”我说:“去饭店,就我们父子俩。”父亲似有不悦,估计他还是想到我家里去(这也是他一贯的向往)。沉默良久,说:“也好,咱父子好好聊聊。”
傍晚时分,我同父亲来到富康酒楼,老板是我的朋友,要了个清静的单间,拿来菜单,让父亲点,父亲看也不看,就说:“来个三菜一汤,一个红烧肉,多肥少精的,以免塞牙;还有清蒸鲫鱼,要大些的,再就是牛肉烧萝卜,要化些;至于汤嘛,就来个整鸡煨汤吧,但一定要农村家养的,不要饲料鸡!”
父亲常说:“日图三餐,夜图一宿,这人嘛,能吃才有福!”父亲饭量大,尤其是在困难年代,即使粮食再紧张,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祖母、母亲及我们都让着他吃,他也从来当仁不让。好吃,好喝,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父亲果然好食欲。有吃福,这回更是放开量来,他喝了两瓶啤酒,吃了两条大鲫鱼,一碗红烧肉,大半个煨鸡,还喝了一碗鸡汤。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如此能吃,真令我眼界大开,又惊又喜又惭愧,因我平生从未单独请父亲吃过饭,更不知他竟有如此饭量。我想,以往在人多吃饭的场合下,父亲一定是控制食量,多少回都是在委屈自己。
父亲吃得痛快,我更高兴。饭后,想起父亲年轻时也曾是票友,便提议说:“爸,唱段戏吧!”父亲说:“好哇,有京胡吗?”老板说:“只有二胡,早预备着呢!”父亲说:“那好,就来段黄梅戏吧——《天仙配》,董永的。”我便操起琴来,父亲放声而唱……想不到的是,父亲声音虽然苍老,略显沙哑,但仍不失圆润、饱满,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一曲唱罢,竟引来饭店众多食客,齐声叫好。父亲却不无得意地说:“老了,老了,不比从前了!”
走出饭店,已是晚上九点。将父亲送回家,在门口,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好儿子,谢谢你的这顿饭,还有唱,让我过足了一把瘾!往后怕没这机会了。”父亲说着说着,竟流下了老泪,自觉不好意思,又说:“我这可是高兴啊!”
当晚,我想着父亲的平生事,还有这顿饭,一夜无眠,心头不知是心酸,还是欣慰……。
老父
文/高海涛
父亲抓住儿子的那只手上,当然有着一位老人一生的正直和无私,但更多的应该是对儿子的爱,这种爱让儿子防微杜渐,及早回头。
所有人的感觉和所能使用的一切医学检测手段,都表明:老人已进入弥留之际。一向慈善安详的老人,表现了极度的痛苦。人们屏声静气地关注着他,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深深的痛苦不是来自生理,而是来自心灵。人们甚至感觉到有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在支撑着老人一次次地挣脱死神的巨手,竭力攀住崩溃殆尽的生命堤岸。
人们再不忍心让老人延长这种挣扎。他们努力猜测着老人的愿望,以便满足他,让他放心离去。
老伴捧着他的枯手,根据人们的提示,把嘴贴到他的耳边,一一地问。老汉一一用急躁厌烦的表情否定。
不是老伴身体的事,不是孙子上学的事,不是外孙女求医的事,不是女儿与婆婆不和的事……不是,都不是。
难道是不放心儿子?儿子大顺是乡长,三十八岁,正走红,如日中天,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老伴还是问了:你是不放心顺儿?
老汉停止了急躁厌烦的表示,手指在老伴的手心上用了用力。老伴扭头寻见了儿子,示意他过来。
儿子没动。
老伴喊了声:顺儿,你过来!
大顺走到父亲床前,叫了声爸。老汉双眼睁出一条缝,挤出两道令人生畏的光,定在了儿子的脸上。儿子扭了脸,却看见由被窝里伸出的那只枯手在床单上敲击着,便感到那手是在擂动一面大鼓,撼人心魄。于是,又躲这只手。
有人提醒:乡长,把手递给大爷。
大顺没动。
母亲说:“顺儿,你爹要你的手。”
大顺把手伸过去,立刻被抓住。他感到那只手传导着由心底发出的刻骨的力量。立刻,愧疚、悔恨、慌乱、恐惧、悲痛交织一体,在他的心灵深处倒海翻江。但,没有泪,只有汗。汗从额上、两鬓、两腋、前胸、后背冰凉凉地涌出来。
此刻,他是真的悔不当初了!
朋友倒化肥,求乡长大顺帮忙。他应了做了,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便一次次地干下去。当发现是假化肥时,他已深深地陷了进去,无力摆脱。
一车假化肥被发现,货主和司机逃脱,车被扣押在乡政府大院。第二天,公安、工商就要来人,这罪证必须看好,以便顺藤摸瓜,惩治罪犯。
乡长大顺深夜悄悄打开了大门,带人来开车。来看儿子、住在院里的老汉把一切看了个真真切切。老汉跑出屋,车已经出了院,喊了声:“顺儿,你这个……”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满身冷汗的大顺,嘴贴着父亲的耳朵说:“爹,那些货不是我弄的,我只是帮帮手。”
老人不松手。
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没让他们坑过本乡一个人。
不松手。
又说:爹,我对不起您,从今往后,我再不会干了——您放心吧!
仍不松。
一个穿制服的近了床前,帽子上的国徽被老人的目光捉住。老人的眼睛突然地睁大了,似在辨认。又由帽徽而下去辨那张脸,渐渐,眼睛失神了,失望地闭住。那人是女婿,在税务上工作。
大顺突然声泪俱下,大声向着老父说:“爹,我明白了,您等等——”说完挣开老人的手,奔向门外。
大顺回来时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爹,我投案自首——您、您放心吧!”说毕,把手举到老父跟前,紧跟他进屋的公安派出所所长迅速地给他戴上手铐。
老人又睁大了眼,辨认了帽子上的国徽,辨认了国徽下的脸,辨认了手腕上的铐子,长长地出了口气,如释重负地合上双眼,两滴浑浊的泪由深深的皱纹丛中滚落下来。
哭声骤起……
最后的愿望
文/佚名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根,平常的日子并不觉得,甚至会忽略它的存在,但当生命之树枯萎时,每一片树叶都会落向根的方向。
在明白生命来自造化之后,也明白父亲是我生命的缔造者,是我世俗生命的源头。
父亲晚年赋闲在家,确诊为胃癌时我们都不敢相信,整日和父亲厮守在一起。原先父亲的身体极好,见到的人都不相信他已是花甲之年。却突然就不思饮食,消瘦,在医院我陪他做各种繁复的检查,医生说:是胃癌,已到晚期,呈花瓣形了。医生的话使我不寒而栗。从透视室出来,父亲边穿衣服边问我病情,我按医嘱说是胃溃疡。
死是正常的。我的阅历让我见识了死,见识了生命的寂灭和消亡。我认为死是正常的。然而,当死以如此切近的距离接近我时,我还是感到了它的凶险,感到了它给我内心带来的震惊,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哀和痛是怎样一种感觉。
被病痛侵蚀的父亲日益衰竭,先是不能走路,再是不能下床,辗转病榻。父亲开始怀念家乡,怀念家乡的亲人。父亲少年时代就告别晋北的故乡,饥馑和灾难使他在十五岁就开始他长达半生的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