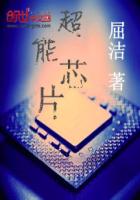在吴巧的辗转反侧中,大周国北部边境宣州永平十一年,寒风中带着雪粒送来了宣州的初雪,天地间白茫茫地一片,分不出边际来。
吴巧涩缩着脖子隔着门帘看了看,打消了出去走走的想法。她没有袄子,给自己以前的衣服裹在里边,外面套着军中发给杂役的衣服,在灶房也算暖和。眼光飘过,却发现角落的凳子上放着一卷书,她想起来是何析留下的。便上前去看看这里的书里都写点什么,上前看了封皮,心中默念着那遒劲有力的书名——旧说。心里就一阵欣喜,ok,这是脱盲了。
忙过中午那阵,她靠着灶台翻起书,随后翻起来一篇来看,对于繁体的文言文,为了好理解,只好一字一句的念,“陈彦过楚,湘王使与司马言论白马非马之说。彦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名其所谓,使人与知焉……说的有道理啊!”吴巧读到后面,看到陈彦说倘若辩论只是为了运用巧言令色而转移论点,取信对方,把人引导离真相越远,无法明了其意,争论不休,混淆是非,非君子所为,也有违论道。一边颔首一边摸了瓷碗喝了口水,不禁出言感叹:“陈彦真是一个明理有大智的人!”
她放回瓷碗,准备从头细细翻看,这里能找个带字的东西太难。
“你这丫头过的好不惬意。”
吴巧不经意间听到一声温润,抬头去看,却是何析。她急忙将书合起来,站起来双手将书卷捧给他。“这样的天气,正适合读书。大人帐中不能逾矩,只能等何大哥您自己来,请不要见怪。”何析嗤笑一声,接过书去:“发配到军营中的女眷多有书香门第,这也不稀奇。大人此刻也同你一样,倒是没想到你这烧火丫头倒能静下心来。”吴巧垂首不言,随即灵光一动问道抬起眼眸望着何析:“何大哥,你可认识江管家?”
“江管家是何人?”何析挑眉问。吴巧想了想说:“应该是个贩卖物资给军中的商人吧。”何析闻言笑笑说:“你找一个商人又如何。你就算是被他卖过来的又怎么样,难道还不死心在这里呆着吗?”
吴巧心中反感,怎么人人提起来这事都好像自己异想天开一样,用这样刻薄的语气说话感觉很嗨吗?碍着他什么事儿了。她本想开口说自己想爹娘了,想到这估计又是一阵冷嘲热讽,索性不开口提这事了,只摇摇头福身:“失礼了,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何析看她低眉顺眼的模样说:“晚上大人有宴,下午要及早准备。”吴巧点头称是,却明白何析不过是无话找话说,这消息恐怕孙叔一早就知道了,一会就来张罗。何析声音放低说:“不该有的心思会害死你。”
吴巧心中冷笑,最差不过如此。继续这样下去,待自己过两年再大些,恐怕到时候就是生不如死吧。何析见她仍是不语,脸上就带了些薄怒,有些发红:“你才这般小,就想去给人当侍妾,未免也小了些。过两年军中来选你的人不会少。”说完还似笑非笑地上下打量她:“在军中未必就比那些商贾人家差,至少你在这里也算独一份的。”
吴巧听完越来越奇,后来就真的笑起来,真想破开他脑瓜检查下他脑回路是怎么安排的:“何大哥你误会了,我只想知道自己的家乡在何处,想知道爹娘是否尚在,心中牵挂而已,并没有你说的那些心思。我前段生了场大病,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既然晚上有酒宴,我去找孙叔寻人再添些柴火,先退下了,您且自便。”说完她福身后不慌不忙地先走出去了。
外面积了四指的白雪,她感觉通身上下都被寒风包围着,心也似乎被冻透了。踩在上面缓缓地往前走,眼中带了雾气。她别无所求,只想求一个平安喜乐,不想如脚下的荒草身不由己地被肆意轻贱而已,仅此而已。可活着,却这样艰难。她蹲在地上,憋回眼泪,用手指在雪里轻轻写:“Iwillbeokay!”吴巧暗暗握了握拳头,一定会好起来的。
何析随着出来,面如寒霜,语气多有不屑,看着地上的脚印自语:“求人打听事情还有这样的,我倒是也长见识了。越早接受这些事实,对她越好。”
经过这件事,吴巧更加认清眼前的形式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积极干活,决定以后要更加小心隐秘地打听此事。
起先以为这场雪很快就退却,没曾想竟然有愈演愈烈之势,断断续续的下了五天,吴巧更少出门,何析上次走后次日送来了本《长亭夜话》,是本修身养性的书,不及上本《旧说》带些故事看起来有趣,虽然有警告的意味在里边,但还是一番好心意。吴巧好一番言辞感谢。这过了好几日都不曾过来,她不由的好奇,怎么这位大人晚上少了夜宵呢。想到这自己又想说自己果然是个劳碌命,不来了自己怎么还盼着呢。
刚靠着炉灶看了一会儿书,孙叔就进来了,喊道:“丫头,快些,大人要用些夜宵。”
吴巧心里咒骂自己是乌鸦嘴,将书放在一旁麻利的起身道:“这几日怎么没见着何大哥呢?”孙叔仔细看了她一眼道:“出事儿了!军中可能有瘟疫了。”这话一出,唬的吴巧一愣,忙问:“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灶房的人没事吧?”
孙叔摇摇头:“咱们伙房的人还未有,但是听说采买的邓虎似是染上了。现在都在楚大夫那里呢,何小哥好像也……”吴巧一帮手上忙活着一边问:“孙叔,既然说是瘟疫,那传染源可找到了。”孙叔将肉汤煨上,摇摇头:“起先是说风疹,不能见风,否则那人肿胀的厉害,可是最近却又开始慢慢塌了下来,那些瘦弱的人看着很吓人,不断喊疼,受罪啊!大夫说又不像是瘟疫,像是中毒。”吴巧一阵犹疑,觉得大冬天气温这么低也会有瘟疫吗?孙叔又是一阵忙活,备好了两菜一汤出门要送去。吴巧问:“孙叔,怎么今天是你送的?大人身边难道没别人了吗?”孙叔摇摇头说:“大人身边伺候的是他贴身带来的,旁人不使,还有个自然是要时刻伺候在旁了。”吴巧闻言点点头:“那孙叔外面路不好,我给你前面引路吧,然后我就回来。”孙叔点点头道:“俺也正是担心呢,刚才忘了叫人一起过来,这会子都做好,耽误了就凉了。你能给俺前面引路是最好,外面雪大,深一脚浅一脚的难走的很。丫头今天帮了孙叔大忙了!”
吴巧拿了根火把引着,听着孙叔的指挥往中营走,她不怎么出帐,自己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裹紧了,大约五分钟这才拐到中军营帐。吴巧在一旁候着,孙叔独自上前去送,守帐的士兵进去禀报一声,孙叔就送了进去,吴巧冻得牙齿打战,感觉度秒如年。孙叔掀了帘子出来,小跑到她跟前道:“丫头,丫头,快进去复命,大人有令。”吴巧一阵迷茫,还没领命,复命是几个意思,孙叔接着说:“我猜着是何小哥举荐了你,你是不是识字?”吴巧点点头:“是认识几个字。”到了营帐跟前孙叔接过火把道:“在大人面前伺候要处处小心。”
说完,他同侍卫说:“队长,大人要见她。”那侍卫冷冷地上下扫了吴巧一眼,看她裹的不伦不类,头发两边就编了俩麻花辫子,夜色漆黑,也看不清模样:“那你跟我来。”
吴巧亦步亦趋的跟上,进了这个军中的核心机构,大约六十平大小,起居室在南用屏风格挡,右手边上博古架摞起各类书,左侧显眼处挂着一幅地图,几案上堆满了类似奏报之类的东西,后面正危襟坐着一人,埋首正在看着东西,地上铺着红色的毯子,屋子各处熏了十多个火盆,点着淡淡的檀香,六个如雀的蜡烛架子上的满满地红烛把帐内照的通明。这哪里是寒冬腊月,放两盆花说这是春天也不为过啊。
吴巧跪在地上,那军士行了个军礼:“大人,人已带到,卑下告退。”这便出了营帐。
几案后一人喝着汤,声音却是意外的年轻:“何析染了病,你先来替他做些杂活吧。听何识的差遣便是,在何析病好之前,你就是一个聋子,一个哑巴,在这里听到的任何一个字,如果在外面出现了,那你也就不必再出现了。”
吴巧深深呼吸了下,叩首称是。
何识伺候李湛之用过夜宵,又准备好了热水梳洗,这才问道:“大人,奏报已经批阅完了,您是要直接歇息还是再看会书。”李湛之站起身来,淡淡道“这几日着急紧张,不可懈怠,我先歇息片刻,一个时辰之后命军医来见。”指了指吴巧道:“你来榻前,给我念书,念这本书第六篇——忤合术。”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吴巧扫了一眼假寐在榻上的李湛之,左军都督佥事,官拜正二品,却是一个看起来才十几岁的少年郎?他冠束长发,缨纬飘垂,身着白色深衣,玉带束腰,外套玄色袍衫,脚踏皂靴,身形匀称修长,秀骨清像,声姿高畅,面如傅粉,眉目疏朗,卧之如珠玉在侧,给吴巧本来就没有的信心来了一个粉碎性碾压,深深深深地感叹这云泥之别,就算是卫阶在世,也不过如此风采了吧。
心思一转,念得就不太顺了,于是赶紧敛神念第三段“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念完之后,她仍跪在地上,低着头盯着书卷中的字。
“在想什么?”李湛之问,音如玉润,眉微蹙。吴巧一心做自己的哑巴,一言不发。何识过来,脚轻碰了她一下:“主上让你回话呢。”“回大人话,婢女已将忤合术读完了。”吴巧想了想,回了一句废话。李湛之闻言轻笑一声:“狡诈。对于忤合术这篇,说说看,你有什么心得。”吴巧心中郁闷:“回大人话,这些字婢女都认得,可连成了章法,婢女就不懂得什么意思了。”
“那你好好琢磨下再回我,再梳洗一番,等下军医来了唤我。”李湛之一翻身,何识上去拿了白色表裘覆在其身上。
吴巧退下后依命退到旁边的小帐梳洗自己,嫌冷就没洗头发,重新打了麻花辫。换上何识刚给她的小丫鬟的服饰,带了层厚袄。她觉得李湛之帐中暖和,就没有穿在里边,趁机赶紧送回了灶房。回来应卯了不久,军医就依命来回,发病的士兵越来越多,情况很严重。吴巧忍不住低头心中暗暗为那些病患之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