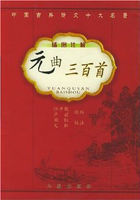屠牛坦一个早晨宰十二头牛,锋利的刀刃并没有变钝,那是因为他拍打剥割的地方都在肌肉和骨头的缝隙之间,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至于对付大腿骨的地方,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仁义恩厚好比陛下的锋利刀刃,权势和法制好比陛下的砍刀和斧子。如今诸侯王都像一些大腿骨,对他们不用砍刀斧子,而想用利刃去切割,我认为不是被碰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不用仁义厚恩的方法去对待淮南王、济北王呢?因为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了。
【原文】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成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成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成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成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译文】
我私下考察以往发生的叛乱,先谋反的大都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淮阴侯韩信在楚称王,势力最强大,是最先反叛的;韩王信依靠匈奴的势力,也起来反叛;贯高依靠赵国的优越条件,又反叛;陈稀倚仗其军队精悍,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国的资助,又反叛;英布依靠淮南的力量,又反叛;势力最弱的卢绾,最后一个反叛。长沙王的封地内人口才二二万五千户,功劳小但保存得最完善,势力弱但对朝廷最忠诚,这不是由于性格独特与其他诸侯王不同,而是形势使他这样的。如果像从前一样,赐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几十个城池,即使现在他们的势力已经削弱了,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只居于彻侯地位,即使现在还存在,也是可以的。既然这样,治理国家的大计就可以明白了。要想使诸侯王都对朝廷忠心归附,那么最好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势力弱小;要想使臣子不至于被剁成肉酱,那么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只封侯不封王;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最好多建立小的诸侯国,减弱他们的势力。势力小了,就容易用法令来规范他们;封国小了,就不会起谋反的野心。如果全国的形势就如同身体指挥胳膊,胳膊指挥手指一样,就没有不服从的。诸侯王不敢抱有二心,就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向车轴那样,齐心协力地效忠于皇帝。即使平民百姓也会觉察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因此天下人自然就会感到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下制度,使齐、赵、楚等几个大诸侯国分成若干小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都按长幼次序继承祖先的一份封地,一直到把地分完为止。对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都用同样的方法分割土地。那些封地多子孙少的诸侯国也划分成若干小国,可以暂时空着王位,等他们有了子孙,全部让他们去做诸侯国君。对于诸侯王的土地被大量削减而收归朝廷的,就迁移他的封地和封他的子孙到其他地方去,按原来的土地数还给他;哪怕一寸土地,一个百姓,皇帝都不想占有他们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安定罢了,因此,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洁了。分割土地的制度一确定,宗室子孙都不用担心做不到王,诸侯王没有反叛之心,皇上也就不用有讨伐的念头,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仁爱了。法制建立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没有人违抗,像贯高、利几之类的阴谋不会发生,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也不会萌发,平民百姓都趋向善良,大臣都表示顺从,因此,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的正义了。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国家也是安定的;即便是立遗腹子为皇帝,只是让臣下朝拜先帝遗留下来的衣物,天下也不会混乱,这样,当代国家能安定太平,后代也会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实行这一项措施,就能树立以上这样五项功业,陛下还为什么顾虑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原文】
天下之势方病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鹄,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踱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倡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痘也,又苦踱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日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译文】
目前,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患有脚肿的病人一样。一条小腿肿得几乎跟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头肿得差不多像大腿一样粗,平时不能屈伸,一两个脚趾抽动,全身都感到疼痛难忍。如果现在治疗不及时,必然成为难治之症,即使以后有扁鹊也无能为力了。况且患的不仅仅是脚肿病,而且还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做楚王的是陛下堂弟的儿子。惠王是陛下兄长的儿子,现在做齐王的是陛下兄长的孙子。现在,陛下近亲当中有的还没有封地来保持天下的安定局面,而疏远的人却有的执掌着大权来威胁皇上。这就是我说的,不但患脚肿病,同时还苦干脚掌扭折的原因。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现在,国家的形势正好上下颠倒。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呢?因为在下面。现在匈奴对汉朝肆意侮辱掠夺,到了不尊敬的极点,成为天下的祸害,没有止境,而汉千朝每年却还向它赠送大量的金钱、丝绵和各种彩色的丝织晶。匈奴对汉朝发号施令,掌的是皇上才有的权力;皇上向匈奴纳贡,行的是臣下的礼节。现在脚反而到上面,头反而在下面,如此颠倒,没有解决的方法,还能说有治国的人才吗?不但上下颠倒,又像得了足病,还患了风病。足病只是局部性的病,风病则是一大片地方疼痛。现在在西部边境,即使爵位很高的人也不能轻易免除兵役,獐以上的人都因为备战而得不到休息,哨兵日夜瞭望烽火不得安睡,将官睡觉时都挂着甲胃。所以我说这是一方得了病。这种病,医生能够治疗,但皇上没有让他治,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啊。
陛下怎能忍受以堂堂皇帝的称号去做匈奴的诸侯,地位既卑下屈辱,又祸患无穷,长此下去,哪有穷尽!出谋献策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这些人简直无能到了极点。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口只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以这么大的天下,而受困于只相当于一县人口的匈奴,我真为执政的大臣们羞愧。陛下为什么不任命我为属国之官去掌管匈奴呢?实行我的计策,必定可以捉住单于,掌握他的生死命运,制服中行说而鞭打他的脊背,使整个匈奴都听从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攻打凶猛的敌人而去打野猪,不去捕捉叛臣而去捕捉兔子,贪图娱乐而不考虑解除国家的大祸患,这就是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啊。皇上的恩德本来可以施行到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仅仅在数百里以内就行不通了,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啊。
【原文】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毂之表,薄纫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日“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日“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译文】
现在民间贩卖奴婢的人,给奴婢穿上镶了花边的绣花衣和丝鞋,圈在木栅栏内,这些奴婢穿的服饰都是古代皇后穿的,而且皇后平时宴会都不穿,也只是在祭祀时穿,而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婢妾穿了。用白色绉纱做面子,细薄熟绢做衬里,又镶上花边。更漂亮的还绣上花纹,这是古代帝王的服饰,现在富商在宴会上招待客人时,却用来挂在墙壁上。古代这些服饰只用来侍奉一帝一后,是节制也是适宜的,现在平民的屋壁挂上了皇帝的服饰,下贱的倡优也穿皇后的服饰,这样天下财力不枯竭,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粗厚的丝织品,而富民的墙壁上披挂着华丽的刺绣;皇后用来镶衣领的花边,一般人的婢妾却用来镶在鞋口上:这就是我所讲的错乱之事。一百个人做衣,还不能满足一人穿,要想使天下没有不受冻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一个人种地收获的粮食,却有十个人聚集起来吃它,要想使天下之人不挨饿,是不可能做到的。饥饿寒冷关系到人的生存,要想使他们不做邪恶的事,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财力已经枯竭了,盗贼何时起只是时间而已,然而献计的人却说“最好是不要变政策”。社会风气已经到了对上极不尊敬的地步,已经到达没有尊卑等级的程度,以至于去冒犯皇上,而献计的人还是说“不要去改变”。我可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