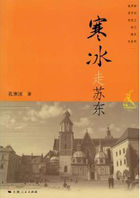但是,作为旷世大儒的阳明,学养深厚,功夫精湛,很快就从“俟死”进入了“俟命”的状态。所以《年谱》中记之为“俟命”,亦反映了阳明悟道之进程,不应视为无意识的改动。从一般的意义来说,“俟命”是一种消极地听任命运的安排。但儒家的“俟命”超出了这一意义。孟子云:“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孟子译注》,第338页。所谓“君子行法”是说,人们行其所当行,做其所当做,至于现实的结果如何,则听天由命了。因此,君子“俟命”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它颇有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味。在儒家学者看来:“天命”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而是内蕴“天德”、“天理”的,当其化为人性和伦理道德时,便成为人们一生中应该努力践履的仁义道德。因此,儒者在活着时,能奋发勉力于修仁行义,而对富贵与否毫不挂念在心,是谓“富贵在天”;儒者又能在面对死亡时,因具备了充实的德性,完成了人间的道德使命而理得心安,是谓“生死有命”。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将“知命”规定为君子的前提,视为道德修养的一个较高境界,可见知“命”是不容易的,连孔子自己也说是“五十而知天命”。儒家的“知命”,实际上是将盲目的客观必然性经过人之知性或体知的方法,转化为应然之必然,也就是人生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必然法则。后来,《中庸》将这种努力概括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天命”与人之心性本就相合,人们顺性而动停行止,其实也即遵循了“天命”。所以,面对生死之交,人们可能会产生两种状态:一种是人们并无道德的觉解,只是意识到人之生生死死是必然,故而被动地等待时光的流逝,“俟”人生结局的到来,无所用心,此为“俟死”。另一种是人们已觉解大化流行之真谛,明确人一生中所应该及必须做之事,故而能够在世间孜孜努力,而不在意于人生的结局何时与何处降临。孟子当然是提倡后一种“俟命”的,阳明“龙场悟道”也是进入此一状态,即由“俟死”进而“俟命”。谪居龙场十三年后,阳明对此有明确的说法。正德十六年,阳明已五十岁,平定朱宸濠之乱后,于八月归越省亲,此后有六年的时间居家讲学,主要内容大部分收录在《传习录下》。在《传习录下》,有这样一段语录:“问夭寿不贰。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语录三》,《王阳明全集》,第108页。所谓“夭寿不贰”之问,语出《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译注》,第301页。这是从人生内涵上来确立生死态度。人们只要能“天命”、“天理”在握,“生”则汲汲于仁义道德的修养与实践,那么,即便“早夭”亦可无怨无悔,是为“不贰”。一般而言,“早夭”是人间的大悲痛,人人极力远避之。但儒者们因为沟通了“天道”与“人道”,又致力于“人道”的推行与践履,所以长寿也好,早夭也好,皆不在意,此谓“立命”。朱熹释道:“‘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寿夭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朱子语类》卷六十,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29页。在“龙场悟道”的过程中,应该说阳明先是从一般人皆持有的“宿命”出发进入到“俟死”的状态,后则逐渐地能将“天”所涵蕴的万物流行发育之条理,转化为人间的人伦道德之准则,就由知“天命”进入到“俟命”的状态了。从根本上而言,即是把外在客体“天”与主体“人”贯通为一,阳明从内外相合的“天之命”中获得了践履人伦道德的坚定性,从而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坦然态度,突破了“生死念头”。于是,从感性的物质欲求到精神的名誉荣辱,再到生死之念等等都可以放下,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悟道阶段,即所谓“胸中洒洒”的状态。此处所谓“洒洒”,就是阳明常谈的“洒落”。他说:“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答舒国用》,《王阳明全集》,第190页。“心体”是“天理”,明此“天理”者,本心之“良知”也。当人们不仅摆脱了一切声色犬马之物质欲求,也超越了一切名誉权势地位等精神欲望,直破生死之念时,“天理”便由“良知”整体映照而出,这是一个即知即行的过程,人们的一举一动自然皆中礼中节,直入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化境。这即是阳明“龙场悟道”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可见阳明所悟之“道”应该是:只要自明本心就可以解决一切人生困厄,完成道德人格的矗立,止于至善;也可以化解“生死之念”,这就叫做“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具体而言,当人们通过自明本心之良知达到“天理”之本体境界后,借助于本体之无限而超越了生死之有限,亦即所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那么,“惧死恋生之念”也就消弭于无形。再者,当人们的良知“和融莹彻,充塞流行”之时,自然会为人们现世的人生构建出社会及伦理责任,这即是曾子所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论语译注》,第80页。的意思。如此,人们“求死解脱之念”也将消失于无有。后来,阳明“自径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阳明认为,自己悟出之“良知”,“实千古圣贤相传一滴骨血也”,并且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年谱二》,《王阳明全集》,第1279页。
至此,阳明可谓彻上彻下、彻里彻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怎不中夜“呼跃”,让“从者皆惊”呢?可见,“龙场悟道”之悟,突破“生死之念”是个中的关键,而“良知”之心性本体的构建又成为阳明离开龙场后接受新的人生挑战的无穷无尽之精神资源。十年后,阳明在南都讲学。有学生问“死生之道”,阳明回答:“知昼夜即知死生。”学生再问:“昼夜之道”是什么?阳明说:“知昼则知夜。”学生还是不解:“昼亦有所不知乎?”阳明之意是:以昼喻“生”、以“夜”喻“死”,如果人们视生死更替尤如昼夜相代,于是便不会有死之恐惧了,而要知“夜”(死)则需要先知“昼”(生)。可是,学生仍问:人人都在“生”,何能不知“生”呢?又为何透悟不了“死”呢?阳明再论:“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什么死生?”《语录一》,《王阳明全集》,第37页。这是说,虽然人人都活着,但如果只知求食求衣,其余一概不知,一概不求,那便是“梦昼”——活着尤如睡着了,不省人事。一个人只有不唯清醒时孜孜于“天理”、睡梦中亦归之“天理”,涵养成自我之“天德”,这样便与“良知”合为一体。如此“更有什么死生?”(超越生死);亦可以“昼夜生死”(生死象昼夜一样自然交替),从而对死亡毫不畏惧。生死之履:“死得其所”“死得其所”是儒家最重要的生死价值论,也是儒者生死践履的观念支撑。真正的儒者担忧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得是否有意义与价值。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论语译注》,第163页。;亦如孟子所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译注》,第265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就是“死得其所”。阳明云:“生死常道,有生之所不能免也。”《答张淑人文》,《王阳明全集》,第1213页。每个人都不免一死,人不可能改变死的结局,但却可以改变对死的态度,在追求某种神圣而崇高的价值过程中,死亡这一人生最大的痛苦会转化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甚至还会成为人们勇于投入其中的人生归宿。阳明在阐释、践履儒家“死得其所”的生死价值观时,还指出人们要珍惜自我之生命,不要去做无益之牺牲,这样才符合天地的“好生之德”。在这里,阳明吸取了老庄、道教珍惜和重视生命的思想。庄子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庄子浅注》,第42页。阳明不仅对庄子的“保身全生”思想非常熟知,而且本人也长期修道,珍视生命的思想在他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应该说,道家“保身全生”的观念是“死得其所”另一面的表现,它要求人们不要做无益的牺牲,不要为获取外物而伤身害体,尤其是不要为获取功名利禄而扭曲、残害人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