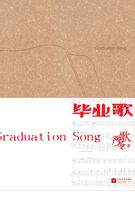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您都冇看到那棵树长得么子样,又不知道它长在哪里,又怎么会知道它古木参天,枝繁叶茂呢。”
“这你有所不知,在南岳大殿,长老告诉我说,在资江边上一支流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叫弯山的地界茶马古道,旁长着一棵千年老腊树,树根底下立有一块箭碑,碑上刻有明朝宝庆府官吏封号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令牌。你瞧,这就是长老给我的路引。”
“您老为何不告知我家大官人等知晓?”
“那长老教予我时就再三告诫,此乃天机,未见舟行不可泄露,不到宝庆府东塔进了香则不灵验。还说这是他四方云游时看好了的一方宝地,要心诚之人、有弥勒心肠之人方可享用。”
张氏一听,心想,弥勒心肠?瞧你一身骨瘦如柴的模样,从外形上看哪里有一点弥勒佛的相?不过,嫁到这一户人家,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她却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老员外那心肠倒是有弥勒佛的胸襟,也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的度量。
没等张氏往下细想,对面船上的乌篷门洞开,环儿从船舱里钻了出来,一见张氏与大老爷在船头立着,先给大老爷行礼问安,接着就喊张氏:“二姨娘,你出来观风景,也不叫我一声,我在篷里捂着不见天日,都快发疯了。”
“你不是睡觉了吗?上船前你不是就嚷着,上船后就好好地睡一觉吗?怎么,冇睡吗?”
“我的好姨娘,你也不动动脑子,这船舱里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这么多男男女女的挤在里面,你一句他一句地闲聊不说,就是那晃来晃去和着那哗哗的流水声,也让人睡不安生呀。”
张氏反驳道:“傻姑娘,你那是不困,要是真困了,立在哪,有个地方靠,都能睡个好觉。”
老员外也答话道:“嗯,看来是不累。常言道,真要是累乏了,用棍子支着眼皮都会睡着的。”
听见船头有人在说笑,两条船舱里的人都先后纷纷爬出来凑热闹。船老大见此情景,连连招呼:“这样可不行,船头地方小,站不开这么多人。再说了,也不保险,容易掉江里去的。”要求众人都退回船舱里去。
老员外只好在张氏的搀扶下回到了舱里。刚一进去,就听到了船老大和大官人在船头商议。
大官人问:“船家,前面可有停泊的码头?已过正午,是该生火煮饭呷的时辰了,众人早已饥肠辘辘。”
船家道:“还要过一会儿才行,驶过这道河湾,前面就有一片沙洲,恰好可以生火煮饭。沙洲上浮柴也多,取水也干净些。运气好的话,掏个水坑兴许还能捉几斤鱼呷。”
大官人没有接着他的话说下去,而是岔开话题继续问道:“船老大,到宝庆码头最快还要几天?”
船老大没有说出准确的日子,只是打着哈哈说道:“您很急吗?赶急去那里有么子重要的事吗?”
大官人搪塞道:“那倒没有,只是想打听打听,心里好有个底。”
“哦,是这样啊。说给你听,跑江湖吃船运饭的人是不计日子的,只能随波逐流。俗话说得好啊,行船跑码三不算,这第一不算的就是日子。因为谁都无法预料,起船后这一段水路上会发生么子事,要是刮大风、起大雾、下大雨、过险滩,有时一耽搁就是十天半个月。你问我要几天,我只能告诉你说,要不了几日就能靠上宝庆码头。”
“哦,是这样啊,都怪我等无知,还望船老大不要见怪才好。”
“这冇么子的,冇么子的,不知者不怪。”
说完,他顺手从篙架上抽出一根长篙,立在船头,插入江水中,试了试水深,吆喝对面的艄公喊出老大来:“水情浅咯,江面窄咯,怕要解了缆,各行各的船咯。”并对艄公说:“记下了,转了江湾靠银沙洲搞东西呷哦。”
艄公对着船舱里喊了一嗓子,立马船舱里就出来两个船工,解了前后的缆绳。船老大用篙点住船帮,用力一推,两条船顺着江水缓缓分开,一前一后地行驶在江面上。
转过河湾,江水平缓如镜。船老大放下篙子,喊了几声:“挂桨咯!挂桨咯!”船工们前后各站两个人,挂起了双桨。随着声声船工号子,桨起桨落,掀起朵朵浪花,船行驶在平静的江面上。
这里水平如镜,有如湖面,两岸苍松竹影在阳光照耀下倒映在水面上,天地一色。船儿划过,波浪起伏,一群群水鸟随波戏水、荡漾。
见此情景,大官人好奇地问:“船老大,这江水中怎么会有这样一潭静水,真是美呀。”
“哦,这个道理很简单,江水在这里形成个回湾,又加之这里的水很深,俗话说水深静流,自然就平静如湖,也就形成了沙洲。”
“哦,是这样,您说的银沙洲就是这里吧。”
“对,没错,过会儿就靠岸煮饭呷,大家也上岸轻松轻松,您还不知道搭船不习惯的人那难受的滋味。人在船舱里窝久了,血脉不通,不上岸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筋骨,时间长了那才叫难受。看官家这一身打扮,就知道是来自山里人。”
大官人一听,笑道:“嗬,好眼神!”
“哪里呀,不过是常年在这江河上跑船,多见着几个人罢了。”
不知不觉中,开始还在头顶的太阳已偏向了西天。一抹晚霞渲染在天际,江岸上几棵高大的垂柳摇曳着枝条,倒映在水中,苇絮似雪花随风飘荡、四处洒落。大官人感觉身上增添了几分寒意。
船老大见大官人一直望着天空,觉察到了点么子,问道:“冻人了吧?肚子早该饿了吧?先进篷里去,里边要暖和些,靠岸还要一会儿呢。”
在桨起桨落的哗哗声中,两条乌篷船先后靠上了银沙洲。印祥与张氏扶着老员外、老夫人爬出船舱,立在船头,等船老大将跳板搭好。
张氏细心地先让印祥走上跳板,说道:“你先上去试试,看牢靠不?你年轻,万一不稳,跳下去也不会有事。到那边边上扶着点儿,接大老爷下船。”
印祥先是在跳板上踩了踩,而后快步地走了下去,站在船下喊道:“冇事,蛮稳嘞。就是窄了些,两个人行,要加小心。你们过来吧,冇事,我在下边护着,踏稳脚,一步一步地行,别着急。”
张氏扶着老员外上了跳板,喊道:“慢着点,我扶着您哪。”
老员外不服气地甩开了张氏的手道:“这么窄,我一个人能行,别把我当小孩,还冇老到连下船都要你们紧张成这般模样的时候。”说着,独自一人颤颤巍巍地走上了跳板。
张氏发现老员外一步一颤,身子晃晃悠悠的,生怕老员外掉到江里去,紧张得颠着小脚跟在后面,喊着:“慢点行,慢点行,一步一步踏稳了再迈下一步。印祥,你站在那看么子,还不快上来扶着大老爷,接下去。哎,这孩子,真没眼力劲儿,死脑筋。”
老员外听到张氏在骂孙子,心里老不高兴地回过头来埋怨道:“你怪孩子做么子,他不是在下面守着吗。要怪只怪老朽人老体弱,冇得用啰。”
印祥站在跳板下面,伸手扶着老员外:“爷爷,您慢着点行,不急。”
老员外一只脚踏上了银沙洲,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人哪,就是怪,躺在漂泊不定的船上心里就是不踏实。下了船,站在这松软的沙洲上,尽管脚踩上去,一踩一个脚印,有时还会打湿鞋袜,但心里却踏实安稳。看来,流浪和漂泊真是永无宁日。”
印祥以为这是说给他听的,刚想搭话,又觉得不对味儿,反问道:“爷爷,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哦,我是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呢。”
“哦,那是自然,我等这一路翻山越岭,您老率一房人拖儿带女的,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一房人不是遭老罪了吗?”
“是啊,是啊,不知老朽这把老骨头还能在这度日如年的乱世上熬多久,要是能熬到领一房人寻到那好谋生的地界就好咯,就是死了,也好闭眼。”
张氏颠着小脚下了船,招呼完一干人与环儿、彭氏、伍氏一道,手里拿着一块油布赶了上来。一见面就对老员外说:“大老爷,这地界沙子还干爽,我把油布就铺在沙地上,您老就坐在上面歇歇。印祥,大冬天的,冻人,你去拾些浮柴,点着篝火,让大老爷烤烤。一大家子人煮饭食呷,也还得要一会儿工夫。”
印祥拉过环儿:“你陪着大老爷,我去拾柴。”
环儿小嘴一噘:“大老爷有我娘和二姨娘照料着,我们俩一同去拾柴好了。”
彭氏知道环儿的心思:“去吧,我和你二姨娘陪着大老爷。”说着,一屁股坐在油布上,也不管大老爷看不看得惯,跷起小脚,脱掉小鞋,提起老高,往外倒灌入鞋壳里的沙子,嘴里还自言自语道:“这脚啊,走沙地,真他娘的受罪。一踩下去,鞋壳里一下子就让沙子灌得满满的。”又对着张氏问:“你鞋里就冇灌沙子吗?”
“还冇灌?我和姐姐都是一样的脚,你的都灌了,我还跑得了吗。”
“那你还不脱了鞋子倒掉,挨么子,时间长了,沙子会把脚磨破的。”
“冇事,过会儿找个冇人的地方倒出来就是了。”
坐在油布上的老员外没好气地看着彭氏的举动,心里想:别人可冇你这么大咧咧地不遵妇道,冇得规矩,当着老公公的面脱鞋弄脚,冇个廉耻。看来姑娘家在娘屋里没得个好教养,嫁到男人屋里也调教不出个好规矩来。相比之下,张氏出身书香门第,教养就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