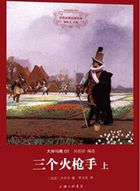傻子胡二突然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的那一天,正好是这一年的七月半。因此我们猫庄人有理由相信傻子胡二是在那天夜半里撞鬼了。确切地说是被鬼魂附身了。胡二是半夜里醒来后独自爬上他家二楼天台上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顾一切地爬上去的,在没有任何辅助物的情况下他又是怎样爬上去的,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总之胡二在天台上站了一阵之后,就冲着挂在天上的那轮又大又圆又白的月亮咿咿呀呀地叫喊起来。那是一种特别兴奋的叫喊声。声音短促、高亢、尖厉,在寂静的夜半里突然响起来就像鬼叫似的让人心悸。当时胡二的母亲就在屋前的天坪上送“亡魂”,她一边烧冥纸一边口里念念有词,突然听到一阵鬼叫声,心里不由得一紧,吓得拔腿就往屋里跑。她一边跑一边还四外张望了一下。由于月亮太大太明亮了,跟大白天一样,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天台上咿咿呀呀张牙舞爪的黑影是她的儿子胡二。母亲冲着胡二说,你个愣货,你要吓死你娘呀?母亲又说,那上面危险,下来,快下来。胡二却不下来,仍旧咿咿呀呀地在天台上转圈圈。母亲想胡二平日里不疯不癫的,今个儿是怎么搞了的?母亲抓起屋檐下的一根长竹篙,说你到底下不下来?你不下来我就戳了。母亲的竹篙还没戳上去,胡二就像一截木头似的“嗵”地从天台上掉了下来。
胡二的父亲也被吵醒了,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胡二从天台上掉下来后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母亲趴在胡二的身体上哭。胡二的父亲略通中医,拿过脉后说,哭你个死,他死不了的,脉相正常,身上也没有伤,你看看脑壳摔坏了没有?脑壳上起了一个大包,你摸摸,母亲还是哭,他本来就是个傻子,再把脑子摔坏了那可咋办呀?不是连傻子都不如了。再傻还不就是一个傻子,父亲说,说不定这一摔把脑子里的哪根筋接上了,通灵了呢。
父母把胡二直筒筒地抬回了他自己的床上。母亲擦干了眼角的泪水后马上就想到了今晚是七月半,是一个不祥的节气,她又跑到堂屋里拿了香纸,专门去为胡二烧,一边烧一边念了驱鬼的咒语。但她的忙碌没有得到丝毫效果。整整一夜,胡二就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既没有醒来,也不像是睡着那样。胡二虽然是一个傻子,也虽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半大小伙子,但他跟大多数正常人一样,睡觉时双眼是微闭的,也打鼾,鼾声细细的,流水一样均匀,鼻孔也要不时地翕动一两下。现在的胡二却是面色苍白,双目紧闭,牙齿咬得死死的,唯一能证明他还活着那就是他的鼻孔还在一张一合的。他还在呼吸空气。
父亲给母亲说:“我看明天找个大夫来看看吧。”
母亲说:“愣货的脑子八成是摔坏了,睡不醒了。”
父亲冲母亲发火,他本来就是个傻子,你听说过有比傻子还傻的人吗?我不是说过,兴许他这么一摔脑子里的哪根筋就接上了,通灵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要不人就没个活头了。
奇迹是在第二天早上大夫来后出现的。大夫是邻村普若的陈三胖,他懂中医,也懂西医,人就像他的绰号一样,大腹便便的,全身的肥肉嫩豆腐一样在坐下来后一阵还在一抖一抖的。他先是用中医的那一套给胡二拿了脉,翻看了眼皮,撬开了嘴巴,又拿出了西医的听诊器听了胡二的心跳。他的动作磨磨蹭蹭的,急得胡二的父母直问咋啦,咋啦?
陈三胖说:“我估计是严重的脑震荡,颅内积血了。”
胡二的父母忙问,要不要紧,会死人不?
陈三胖说:“赶紧拉县里医院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这时,来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发现胡二四肢动了动,忙说他醒了,傻子胡二醒了。等大家都去看胡二时,胡二已经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了。他一下床就做了一个舒展四肢的动作,像似刚刚睡醒那般。
胡二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对陈三胖说的。他点着陈三胖的肥胸说我没事,我看倒是你应该进县里的医院去看看。陈三胖呵呵地笑了,说傻子就是傻子,我膘肥体壮的,能吃能睡会有什么病。
胡二说:“你还是看看去的好,不然你活不过三天了。”
陈三胖怒道:“胡说,我看你才活不过三天呢。”
胡二说:“我可是说真的哟,你别不信。”
陈三胖一下子变了脸,扬起巴掌要打胡二,众人连忙架住了他,劝道,他是一个傻子,别跟傻子一般见识。好了,好了,我不跟这种人计较,陈三胖一边收拾他那些家什一边嚷嚷。嚷完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三胖走了老远,胡二还在对人们说你们让他进城看看去吧,不然他真的会死的。人们从他家离去时还直摇头,说胡二的脑壳真是撞坏了,比以前更傻了,连句好话都说不来了。
母亲也骂:“愣货,你哪天给我说句人话我死了眼睛也能闭上。”
只有父亲什么也没有说,他一直还处在惊奇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父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胡二的变化,从胡二下床时他就发现了胡二的神色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胡二怕人,人一多他就躲,也不敢说话;胡二的眼睛以前是黯淡无光的,现在他的眼睛却是亮亮的,炯炯有神;胡二的歪嘴巴也好像正了,嘴角干干净净的,没有流哈喇子。父亲对母亲说他娘,你不觉得咱胡二变了,好像不傻了。你看他那样子,精神着呢。
母亲说:“咋不傻呀,比以前还傻了,醒过来就没说一句人话。”
没想到的是,三天后,从普若传来了消息,陈三胖死了。带来这个消息的人叫胡达,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来胡二家的,未进屋就对着胡二的父母鬼喊死叫,神了,神了,真被你家胡二说准了,陈三胖死了!
“真死了?”父母惊奇地问。
“死人的事还敢乱说,你当我也是你家胡二。”胡达说。
胡二走出来,脸色平静地说我讲了他会死的,他就是不信,真死了吧。胡达呆呆地看着胡二,足足看了一分多钟,说嗨哟,胡二你好像不傻了呀?胡二耸了耸肩,说你看我像个傻子吗?不像,不像,嘴巴也不歪了,胡达说,他妈的神了,傻子胡二不是傻子了呀。他把胡二拉到屋檐下,问胡二是怎么晓得陈三胖会在今天死?胡二说我看你是我叔,我告诉吧,他得了一种心血管的隐疾,一喝酒血管就会扩张、爆裂。你还一套一套的,胡达说,你说的我不懂,我问你是怎么晓得他有心血管病的,又怎么会在今天死?胡二笑了笑,示意胡达伸过脑壳来,然后神秘兮兮地说了六个字:天机不可泄露。
胡达有些生气了,严肃地说胡二,你既然能知道陈三胖会死,你一定还知道其他的是不是?胡二说当然。胡达说你给我说说你还知道什么。我说了你要骂我的,胡二像是不肯说,也像是在吊胡达的胃口。你说,你说呀,我不骂你。胡达的胃口真被吊起来了。
“真说了呀。”胡二说。
“真说。”胡达说。
“你家今晚会失火。”胡二又是语出惊人。
“你个傻子,你能不能讲句好话。”胡达冲胡二骂道,“陈三胖被你咒死了,我家要是真失火了我要你赔。”
胡二的父母闻声急忙跑过来,一边跑一边问怎么拉,怎么啦?胡达还是怒气冲冲的,说你们的傻子儿咒我家要失火。他不是一个傻子吗?父母给胡达赔不是,你多担待些。他可不是一个傻子,他是一张乌鸦嘴,毒着呢,陈三胖就是被他咒死了,胡达心有余悸地说。胡二的父亲说,你晚上小心火烛就是了,就当是给你提个醒,敲个警钟。
胡达愤愤地回了家,想到胡二说陈三胖要死他就真的死了,心里害怕的,天一黑就嘱咐家人把所有的炉火都熄灭了,整个屋里不留一丝火星。他不敢睡觉,也不敢抽烟,坐在屋里守夜。到了后半夜,胡达实在熬不住了,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打起了盹。迷糊中听到了柴房里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一个激灵就醒了,高叫着:“燃起来了,燃起来了,大家来救火呀。狗日的傻子胡二的嘴巴硬是有药!”
狗日的傻子胡二的嘴巴硬是有药!他说陈三胖要死陈三胖就死了,说我家要燃就燃起来了。胡达一边感激帮他扑火的人一边还忿忿地骂胡二,大家以后少招惹他,狗日的嘴巴有药呢!我看他是着魔了,要不就是被鬼缠身了,胡达的老婆说,他从天台上栽下来的那晚不正是鬼节吗。对,对,被鬼缠身了,大家附和着说,要不他怎么会嘴巴有药呢,说什么灵验什么。
得想办法破了他身上的邪气,胡达说,他是一个傻子的时候多可爱呀,哪个都可以逗他惹他。
我们赶快去请法师吧,一个老者说,我活了七八十年还没听说过咒谁谁死的怪事。了不得呀!
我去杨家寨请杨法师去,胡达说,大家把我家的那条大黄狗杀了吧,淋那狗日的傻子。
胡二在他家天坪上玩泥人儿,他捏了两个泥人儿,正在唆使它们打架。其中一个已被打断了一条胳膊。父亲走过来说胡二你怎么还像个傻子那样玩泥人儿呀?胡二的回答可不像是一个傻子,他说我以前喜欢玩泥人儿吗?父亲就呵呵地笑了,说你以前整天都玩泥人儿。胡二拿迷茫的大眼睛望着父亲,说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父亲的笑声更响了,说不记得了好,你以前是个傻子嘛。胡二说我才不是傻子呢。
“胡达家昨晚真的失火了。”父亲说。
“我说过他家要失火的。”胡二说。
“你是咋晓得的?”父亲问。
“我看得见。”胡二答。
父亲还想追问。陈三胖之死和胡达家失火这两件都被胡二不幸言中的事情整天都在困扰着他,使他从儿子还阳成不呆不傻的最初的欣慰变成了惊愕。他已经感觉到了他家里因为儿子的这种变化也一定会跟随着发生些什么,只是吃不准是福是祸。父亲张开了嘴还没有说出话来,胡二突然说胡达带人要来我们家找麻烦了。
“那可怎么办?”父亲着急地问。
“没事的,”胡二胸有成竹地说,“我有贵人相助。”
半个时辰后,胡达果然带着杨法师和一干人到胡二家来了。一走上天坪,杨法师就唱起了咒语,敲着一面破锣围着胡二转圈圈,胡达他们把手里准备好的狗血、鸡血和猪血一齐往胡二的身上泼,胡二本能地躲闪,但是没有躲过,头上、身上,甚至脚上到处都是那些动物的血。
王镇长一行就是被杨法师的破锣声吸引到胡二家来的。王镇长是到虎村检查工作来的,听到胡二家有锣钹声,就过来了。他一进胡二家的院门就看见了身着法衣、头戴道冠的杨法师在做法事,立即就严厉地制止了他。王镇长说杨大昆你还在搞迷信活动,要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坐几天警闭是不是?此刻杨法师正在一边转圈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咒语,被王镇长一吼,岔了气,一下子就瘫软下地了。也许是被王镇长吓得昏了过去的。谁说得准呢?
胡达连忙跑到王乡长跟前去给他解释。胡达说,傻子胡二被鬼缠身了,说陈三胖要死陈三胖就死了,说我家要着火我家柴房就燃了。要是我昨晚睡了房子就燃成一把灰了。众人也说,就是,就是,胡二嘴巴有药呢,说什么灵验什么。
王镇长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们可别在我面前宣扬迷信,要不我让派出所来人一绳索把你们都捆了去。”
是真的,是真的,众人大声地喊冤,说骗你天打五雷轰。
“是真的吗?”王镇长还是不相信,说,“那我们的傻子可就成了一个大预言家了。”
胡二的父母也畏畏缩缩凑过来,他父亲说我家胡二说今天他叔要来找麻烦,刚说完胡达就带人来了,我家胡二还说有贵人相助,王镇长,这不您就来了。
王镇长说:“嗨哟,那还真神了不是?不过,哪个也不能讲傻子的脑壳里就不会没埋有宝藏。”王镇长毕竟是镇长,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他对大家说,你们讲的我都听明白了,傻子胡二要真是未卜先知我看也不是坏事,大家想想吧,要是陈三胖听了胡二的话去县医院里检查他兴许就不会死了,再说你胡达,胡二要是不告诉你家里会失火,你会不睡觉吗?你家还真会燃成一把灰,依我看吧,你不但不能怪罪胡二,你还得感谢他,是他救了你一家人。大家说是不是呀?
胡二的父母率先响应,说就是,就是嘛。
王镇长蛮感兴趣地问:“胡二呢,那个傻子哪去了?让他给我也说说。”胡二的父母和大家赶紧去找胡二,他们发现浑身是血的胡二蹲在墙角里还在玩那两个泥人儿。那两个泥人儿只剩一条胳膊了,但胡二还是玩得很投入。王镇长摸了摸胡二的头颅,对胡二的父母说还是有点傻呀。胡二的父亲说已经比原来好多了,现在时好时坏的。
胡二转过头来望着王镇长,望了一阵,看得王镇长心里有点发毛了。
胡二说:“你要升官了。”
王镇长说:“我不请客,不送礼,怎么会升官。”
胡二说:“你要当副县长了。”
“什么时候?”王镇长急切地问。
胡二却又专心地玩起他的泥人儿,看也不看王镇长了。王镇长离开胡二家时冲着胡二说,我要是真当上了副县长我敲锣打鼓地来谢你。
半个月后,虎村一溜烟来了五六辆黑卧车。车壳黑得发亮,能照出人影儿。车一停稳,首先下车的就是西装革履、精神焕发的王镇长。现在他已经是副县长了,他带来了一个乐队,吹吹打打地往胡二家去了。
现在的傻子胡二再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傻子了。
傻子胡二成了“活神仙”胡二了,在猫庄他的名声响当当的了。
胡二首先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因为王副县长私底下的宣传,每天都有黑壳子小卧车来村里。车子载来的都是县城里的达官显贵,他们是来找胡二问官运、前程的,也有些人是问生死的。这些人都是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走。当然也有的是垂头丧气或者是面如死灰地走的。无论高兴的不高兴的,总之这些人无不佩服傻子胡二一说一个准,称胡二是“活神仙”。发展到后来,村里人也来找胡二了,他们问胡二的除了生死、财运之外,其他的更是五花八门,譬如天气,收成,甚至丢失的大小物件,走失的猪牛马羊,胡二也能一说一个准,他说明天下雨就下雨,说你家的猪跑到三汊沟去了你就能在那里找着。从来没有出个差错。
受了王副县长的影响,现在除了杨法师一个人坚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说胡二是被鬼缠身了。但是杨法师却不能自圆其说,他的咒语也念了,狗血鸡血也给胡二淋了,但胡二还是说什么准什么。大多数人现在相信胡二父亲的那句话,他摔了那一下把脑壳里的哪根筋接上了,通灵了。胡达说得更有意思,他说肯定又给接错了,接得跟常人不一样才通灵的。这叫傻子有傻福嘛。
胡二不管是给那些达官显贵算官运前程和生死,还是村里人来问天气,或小猪小狗,从来就是张口就答,干脆、直接,绝不拖泥带水。说过之后他就不理你了,任你百般纠缠,他都三缄其口。这也是胡二和其他神汉巫婆最本质的区别。他没有拜神、下晕、烧香纸、请神那一套装模作样的裹脚。胡二还有一个跟那些神汉巫婆本质区别,那就是他对钱不感兴趣。胡二虽然被他父亲认为已经还阳成不呆不傻了,但他至今还是没有弄清钱跟纸有什么区别。但胡二的父母却是对钱极其敏感的人,他们相当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商机。现在,如果找胡二总问任何事,都已经被他父母明码标价了。官运、前程,一次五百;生死、财运一次三百;其他三十至二百不等。亲戚朋友及寨邻减半。虽然很多人都说价格有点偏高,但胡二家还是门庭若市。两年里换了三副院门,那些院门都是因为开关得太频繁把门抽磨损坏了。
几年下来,父母从胡二的身上不知收取了多少钱财,他们尽管是精于理财的好手,但这笔数字显然过于庞大了,他们也一时无法计算清楚。
每天晚上母亲点完钱后都要说一句,真没想到,这个愣货能这么挣钱,快赶得上印钱的机器了。没白养了他。
父亲比母亲要冷静也要现实,说把这房子扒了吧,我们建一座三屋的新楼。
母亲说,我看先给他娶一房媳妇吧,胡二年纪不小了。
胡二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看着一沓沓的钱从母亲的手里转移到父亲的手里,他的耳朵里也听到了房子、媳妇之类的,但是他的脸上却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表情的表情也是一种表情,一种麻木和迟钝。
胡二不但对钱、房子和媳妇之类表现出一种麻木和迟钝。同时,他对时间的流逝也同样是惊人的麻木和迟钝。尽管胡二未卜先知,能看到别人永远看不到的过去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胡二对于时间这个概念几乎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上说,胡二还不如以前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傻子时别人问他有多少岁了他还能准确地报出来。
有一天,母亲给他说:“你都二十了。”
胡二说:“二十是多大?”
母亲又说:“胡二你该娶媳妇了。”
胡二说:“媳妇是什么?她有泥人儿好玩吗?”
母亲被气得不行,说:“愣货,你爹说你不傻了,我看是比以前更傻。”
胡二说:“我不是傻子。”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说你是‘活神仙’没错,说你是一个傻子也没错。”
胡二是在他成为先知的第四个年头的五月结婚的。胡二的媳妇是镇上裁缝店老韩头的二女儿。那女子以前有一个相好的,出门两年了音信杳无,老韩头做主把她嫁给了胡二。他自然是图胡二家那一笔丰厚的彩礼。胡二的父母许诺给他的那笔彩礼数目大得够他老韩头开一家雇用上百个工人的服装厂。
这一切都是瞒着胡二进行的。他既然对媳妇一点也不感兴趣,父母只好全权包办了。胡二是在办喜事的前一天才得知他要娶媳妇了。不是他自己看到的,是母亲说给他的。胡二既没有沮丧,也没有欣喜,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只跟自己说话。
胡二说:“我为什么看不到我明天要结婚?”
胡二答:“你干嘛要看得到自己呢,看不到不是更好吗?”
胡二说:“我连自己的命运都看不到,看到别人的有什么意义?”
胡二答:“胡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对于自己你就是一个傻子,在别人那里你才是先知,是‘活神仙’。”
胡二问:“你是谁,是谁在跟我说话。”
胡二答:“我是胡二呀,是你自己。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墙壁、柜子在跟你说话,要不是魔鬼也行,你认为这重要吗?”
胡二被他自己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半晌,胡二又说:“你要是魔鬼就好了,你把我还原成一个傻子吧。我宁愿做一个快乐的傻子,也不愿做一个看不见自己命运的、受人摆布的先知。”
胡二答:“你本来就是一个傻子。”
胡二再一次无言以对了。他呆呆地在房间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胡二还是当上了新郎。和面色忧郁、心事重重的新娘相比,傻子胡二根本不像是一个傻子,他蛮精神的,面带笑容,举止优雅得体,让男女双方的宾客绝对就看不出也想不到胡二是一个傻子,或者说他曾经是一个傻子。
胡二的茫然无措是在新婚之夜里表现出来的。既然结了婚,胡二就试图接近婚姻的本质,但在这个关键时刻,胡二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女人已经赤条条地躺地被窝里了,胡二掀开被子准备躺上去时看见全身光裸的女人就像被一团耀眼的白光刺伤了一样噔时就“娘呀”一声惊叫起来。
女人听到胡二喊娘后,知道这个夜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女人赤条条地从床上爬起来抓住了想要逃跑的胡二。
女人说:“是不是我长得难看?”
胡二说:“嘻嘻,不难看。”
女人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胡二说:“嘻嘻。”
女人说:“你不是‘活神仙’吗,你真不知道我过去做过什么?”
胡二说:“嘻嘻,不晓得。”
胡二的回答全然不是女人印象中的白天时那种精明,跟任何一个傻子都一样,女人盯着胡二的脸,她从胡二的脸上看不出来什么,心里踏实了一些,说:“那你就是不会做那事。”
胡二说:“嘻嘻。”
女人以过来人的口气说:“来,来,傻子,我来教你。”
女人没有想到的是她刚一抓住胡二的那东西,胡二又大叫了一声:“娘呀!”挣脱女人就往外蹿去。
女人一下时泄气了,骂道:“真是个傻子!傻子你给我听好了,你不会干的事有的是人想干。”
胡二听到了女人的骂声,他却什么反应也没有,甚至连回头看一眼女人都没有。女人一个人嘤嘤地哭了小半夜。
尽管胡二一家人对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极尽隐瞒,但是外人一眼还是能够看出来结婚并没有带给胡二什么。他们几乎从未看见胡二和他的女人说过话,没事时胡二还跟以前一样在院子里玩他的泥人儿。只有在胡二一个人走出了他家的院子,人们才敢问他,胡二,晚上和你女人干了什么?或者问,胡二,抱着那么个屁股大奶子圆的女人是啥滋味哟?胡二说明天要下下雨,赶紧把稻子收回去吧。或者说你老爹八月里要死,赶紧打棺材吧。
“嗨,这个傻子,我没问你这些呀?”人家说。
“我就晓得这些。”胡二说。
胡二还是跟女人住在一间房里,女人睡在床上,胡二却不睡,他要不就是整夜都在玩他的泥人儿,要不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胡二跟自己说话他的女人听不到。
胡二说:“我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住在一间房里?”
胡二答:“因为她是你的女人。”
胡二说:“她为什么要是我的女人?”
胡二答:“你为啥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胡二说:“你说我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
胡二答:“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
胡二说:“你让我做一个傻子吧。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要天天有泥人儿陪我玩就行了。”
胡二答:“你怎么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不是告诉过你了,你本来就是一个傻子。”
胡二明知他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但是这样的问答好像成了他每晚必做的功课了。有一天深夜里,胡二正在和自己说话,他的女人醒了过来。女人拉亮了灯,看到胡二面壁而坐。胡二夜夜如此,她已经熟视无睹了。但是这个晚上女人还是起身下床去看胡二。她看到胡二的嘴巴在快速地一张一合,像似在跟人说话,也像似在跟人吵架一样。女人却听不到胡二说话的声音,不止是听不到胡二的声音,整个房间里也寂静无声。女人有些害怕了,去推胡二,但是她推不动胡二,胡二坐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嘴巴却仍在一张一合的。女人发出了一声尖叫,胡二,你是不是鬼上身了?!
父母听到尖叫声跑来房间时,胡二已经恢复如初了。女人问他,你刚才是怎么了?胡二说我没怎么,我在睡觉。
“我看你是鬼上身了。”女人后怕地说,“你睡着了嘴巴还一动一动的,而且我怎么推都推不动你。”
“哪有什么鬼,”母亲垮着脸说,“哪个像你半夜里鬼叫。”
一连三夜,女人都看见胡二对着墙壁说话,她害怕了。她悄悄地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胡二自己也不知道。
胡二是在他的女人走的那个晚上再次从他家天台上栽下去的。这一晚恰恰也是这一年的七月半,鬼节。
同样是在深夜里,胡二一个人走出了他的房间。胡二在出门前和他自己说了一阵话。这一次对话他们真的像吵架一样。
胡二说:“我为什么看不见我女人要走?”
胡二答:“你有必要看见吗,看不见不是更好吗?”
胡二说:“我看见别人有什么意义吗?”
胡二答:“你不认为了解别人比了解自己更容易吗?”
胡二说:“我要看得见自己。我要主宰我自己的命运。”
胡二答:“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主宰他自己的命运,哪怕是天上的神仙也不能。”
胡二说:“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了。”
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胡二在没有任何辅助物的情况下爬上了他家的天台。这晚也是一个大月夜,胡二站在天台上能看到一轮又大又圆又白的月亮,月亮已经稍微偏西了一些,在离它的很远的地方才有几颗也很明亮的星星。胡二还能看到月光下远处的房屋、树木,以及山头影影绰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这天晚上胡二没有咿咿呀呀地叫喊,也没有在天台上转圈圈,他好像出奇地冷静,在天台上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就一头往楼下栽去。在整个往下掉落的过程中也是悄无声息的,只在他落地时才发出“嗵”的一下声响。
胡二自己从天台上栽下来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那时他的母亲早已送完“亡魂”回房睡着了。他们是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胡二。这一次胡二摔得要比四年前更为严重,他的头上流血了,还有一条腿骨折。父母是从胡二躺着的位置判断他是从天台上摔下来的。
胡二醒过来之后,父亲一下子就发现了胡二的变化,他的心里也一下子凉了。他发现胡二一下子又回到了四年前还没从天台上摔下来时的样子了,胡二的双眼不亮了,滞呆无光,他的嘴也歪了,流起了涎水。唯一没变的是,胡二一下床就去找他的泥人儿,而且他竟能毫不费力地就找着了它们。
几天后,王副县长带着省里的一个大官来找胡二问事,胡二不仅不认得王副县长了,更糟糕的是他一看见生人进了院子,抱起他的泥人儿就住屋里躲。最后是胡二的父母把胡二哄到了来人的跟前,那个大官问了许多事,但胡二一个字也没说。不管问他什么,胡二就只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望着他,气得王副县长只差给胡二喊老子。
就是喊老子也没有用了,王副县长看着胡二那个样子,心里已经知道了傻子胡二已经回到了他几年前那个纯粹的傻子的角色上去了。
胡二再也不是什么“活神仙”了,他又是傻子胡二了。村里人再问他什么,胡二说的没有一件是应验的。联想到胡二又是在七月半那天夜里从天台上摔下来的,人们就又有理由相信胡二曾经是被鬼缠身过的,人们相信那个在傻子胡二身上附了四年之久的鬼魂就在那天夜里从胡二的身上走了,因此他说话就不灵了。
但这对胡二来说并没有什么。那些曾经的事情对于傻子胡二来说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一点也记不得了。除了家里多了一个女人。现在,人们再问他晚上和他女人干了些什么,胡二还是不回答,他只是笑,一个劲地傻笑。笑得涎水都流了出来。
而他女人的肚子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