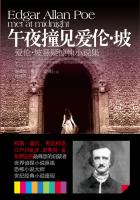小卖部和理发馆都面街并仅隔一墙。香岚出门倒炉灰的工夫,二叔已经把街前的砖铺路面上泼上了清水,晨光便像一群白鸽抖落在二叔眼前。
我所说的并不是某一天早晨,事实上二叔清扫小卖部和理发馆门前的这爿街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早在香岚还没有来到这里开理发馆或者说我还没有出生以前,二叔就开始清扫这块街面了。
只要有空我准往二叔那里去。家里人常戏谑我:吃惯了嘴,跑断了腿。我确实如此,我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迷恋着二叔那里是因为他的小卖部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其实我是有些惧怕二叔的,二叔的脸很瘦削,好多人都说他满脸剔不出二两肉。二叔是不轻易笑的人,不过我发觉他笑的时候比板着脸孔更令人毛骨悚然,他的笑容里总搀杂着那么一股说不清的绝望和哀伤,就像你津津有味地咀嚼一块鲜美的肉骨头,却突兀地发现这肉里竟然正滴淌出黑红的血。
现在小卖部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被一个叫作泡花碱厂的乡办企业占据了。你无法找到夕日小卖部的影子,倒是有一间叫着新潮名称的个体商店又出现在这里,当然二叔再也不用清扫这里的街面了。
而二十年前二叔确确实实每天都要在清晨打扫这里的街面,他在清扫完路面并洒上水后,他才架着双拐一高一低地走进小卖部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在双拐的驾驭下腾空而起的一瞬间,那两条腿似乎和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分离,它们在两根木拐之间自由飘荡,很像是在荡着秋千。
二叔走进水泥柜台的后边,整个人就只剩下脑袋露在上面,这让他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你会觉得让一个残肢人(跛子)去站柜台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情。一会儿工夫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地踱了进来。那时间人们不比现在有事没事总爱好在商场转悠,他们去小卖部就是为了买个手头短缺的东西,比如:油盐酱醋、针线、砖茶、白糖或蜡烛、香烟、火柴之类的日用品。
而实际上二叔的小卖部也只有这几样东西可供人们选购,有时候赶上紧缺连这些最起码的商品也被抢购一空而供不应求。不过逢年过节二叔这里还是会多出三两样好吃的东西,例如水果糖、五香瓜子、到口酥饼等。有了这些诱人的吃头,我的劲头便欢实起来,我整天死乞掰趔地泡在小卖部里,两只脚像是锥子扎进了地里,眼睛瓷登登地看着二叔的那张瘦脸仿佛在等待某种奇迹的出现。
香岚来这里开理发馆是大队书记亲自领来的。
大队书记把二叔从小卖部里吆喝了出来,他指指点点地高声对二叔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这就是李香岚同志,往后就是你的邻家了,生活上你要多照顾她呵!接着他又指着二叔对身后的女的说,别看他腿脚不灵便,想当年他可是远近有名的大英雄呀。
二叔听得别扭,他就架着双拐朝大队书记身后的女人冷冷地斜了一眼,那女的像只害羞的母兔子一直怯生生地躲在书记的身后,他便转身吭哧吭哧地进了小卖部。他听见书记仍然用作报告式的语调给那个女人讲这讲那,那女的始终不多说话,只是很服帖地连声应诺。
随后大队书记就独自闪进了小卖部,他的眼睛像是在看二叔,他同时又飞快地在二叔身后的木头货架里随便瞄了一眼。他笑嘻嘻地说,把白沙糖给我来上二斤,前门烟还有吧,也拿上一盒子。
二叔没吭气,他转身给书记取东西,他却听到从隔壁传来的丁丁冬冬的声音。那声响极像是一曲铿锵有力的兵营进行曲。他想那女的开始收拾屋子了吧。于是他的内心便突地震动了一下,他一想到那声音来自刚才书记身后那个兔子一样的女人的手,他就明显地失落起来,像是谁抢占了自己的这份安宁与平常。
大队书记心满意足地揣着那些东西,他嘴里哼着什么歌子,他掀开门帘往出走,又回头大声补上一句,别忘了给我记上账呵!
二叔照旧不吭声,他思谋着一个问题,觉得书记刚才哼的那首歌子很熟悉,可他怎么也记不清在哪里听过,后来有个人进门的时候,他终于想起来是部老电影里的插曲。
二叔的情绪就古怪起来,他已经很久不看什么电影了。
李香岚就从这天起住在了二叔的隔壁并开了间理发馆,这里早先是有个老剃头匠的,后来他下世了附近再也没人来干这个行当,直到李香岚搬到这里。
我要说的是二叔的生活并没有因为隔壁来了个理发的李香岚而发生丝毫变更,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二叔照旧和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一瘸一颠地清扫小卖部门前的街面,然后又一声不响地伏在黑漆漆的水泥柜台后面塑像样地等待着顾客们的到来,多年以来二叔已经习惯了这种等人问津的生活方式。
然而,小卖部的生意似乎一下子变得红火起来(当然货架上的东西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品种和花样)。男人们吃过晚饭便一堆一堆地往这里扎,一时间小卖部竟成了他们的集中营,他们买上两毛钱的瓜子或一包廉价的工字牌纸烟,有滋有味地咀嚼或咂摸着。他们不停地讲述和重复某个猥亵的故事情节,他们从黄昏持续到深夜,声音高亢震天,直到二叔无奈地接连发出厌恶的叹息,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实际这些家伙都是冲着隔壁的李香岚来的,偶尔她要是出门倒水或解个手啥的,聚集在小卖部里的男人就一窝蜂地趴在窗户上眼馋地向外观望,像是八辈子没有见过女人。
通常这个时候二叔是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的。
这天李香岚走进小卖部。
二叔觉得眼前一片鲜亮,他不由地紧张和局促不安了,这种强烈的紧张使他猛然陷入一种近乎恐惧的思索状态,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只断腿的母狼正凄厉地嗥叫,并不停地追赶一只受惊的兔子。
香岚的双手轻轻伏在水泥台面上,样子很像一个端坐在课堂上的好学生静静聆听着老师的讲授。她的手指或许经常给人洗头嬗变得苍白而纤细,但看上去依旧是很美妙的,此刻她的十根手指正像一堆蚕虫安静地匍匐在水泥柜台上。
香岚说,给我拿块香皂吧!说话的工夫,她的目光匆忙地在从货架上面一一掠过,最后她的眼光停留在二叔那张瘦削的脸上。她微笑地接过二叔递过来的那块散发着淡淡香味的“喜”字牌香皂,她将攥在手心的一团毛票顺势塞给对方。她并没有立即离开,她轻声对二叔说,是上海产的吧!我就喜欢这种味气。她轻嗅着手中的香皂,闲了过来把脸也刮一刮,看胡子长成啥模样啦!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格外亲切随和,她甚至连“你”呀“我”的都省略掉了,就像是在同自己屋里的男人说话一般。
二叔似乎没有完全弄明白李香岚的意思,他颇显迟钝地摊开那团略微潮湿的毛票一张一张地点数着,有一股说不出的热香从那些毛票里弥散出来,比那香皂的味道还诱人呢!而他的眼前也仿佛有一只雪白的兔子在一蹦一跳地隐现。
二叔迟疑地摩挲着自己的瘦脸,滋滋啦啦的摩擦声伴随着他手掌的动作粗糙地传入他的耳膜,他有些异样的感觉和冲动。
其时我尚小,只知道二叔那里有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吃在那样异常短缺的条件下显得尤为迫切,我并不能理解一个大龄、残疾的独身男人的情感世界。
我曾隐约听家人谈及类似的事情,从他们间或发出的叹息声我朦胧地觉察到二叔将要面临的生活境况。
某一天去找二叔时我被理发馆的李香岚喊了进去,她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和温顺得多。她有一头很软的黑发,但她并没有过多地加以修饰,只是齐肩散披着。她的眼睛真的有些像兔子既聪慧又温和,她说起话来跟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一样清晰悦耳。
她起先问了几个不相干的问题我都摇了摇头,后来她就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鱼皮花生豆很亲近地塞给我。我顿时被一股香喷喷花生味包围了,我甚至觉得呼吸都局促不堪,要知道那个年月里鱼皮花生豆意味着什么,几年能吃上一回!
我知道我就要被好吃的花生豆收买了,不过我相信这种妥协对我或者二叔并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其实香岚向我打听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就是有关二叔当年身体致残的经过。我边往嘴里送着滑溜的鱼皮豆,边神情激昂地侃侃而谈,仿佛在回忆有关自己的某一惊心动魄的漫长经历。
二叔曾经担任过大队民兵排的排长,他当年体格健壮、枪法娴熟,和现在判若两人。头些年大队闹狼患,群众的家禽牲畜屡遭厄运,二叔便奉命带队去深山围剿狼群。有一次队伍里的人擅自抱走了狼窝中的几只狼崽,而使得那只潜逃在外的母狼穷凶恶极地伺机报复,终于有一天晚上一群嗥叫的狼们扑向民兵的帐蓬。当晚正赶上大队部放映《霓虹灯下的哨兵》,那阵子放场电影不容易呢,其他的人都跑回去看电影了,只留下二叔在山沟里守夜。
讲到这里我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紧张与恐惧,我接连往肚里咽下了几口唾沫,似乎我即将面对这群突如其来的饿狼。而香岚却深深地喘了口气,她的暖甜的气息正随同她丰盈的胸脯的起伏向我扑来,这种女人特有的气息使我的情绪有所缓和,我竟然有些陶醉于其中,我愿意被她的喘息紧紧地拥抱着。
后来我没有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一腆一腆地跨了进来,他很老练地一屁股坐在地当间的那把椅子上,他的动作幅度很大,以至于那把靠背椅严重地朝后倾斜了。
香岚,好好地给我刮刮脸。
干部模样的男人眯缝着眼对香岚说着。
缘于我吃了人家的鱼皮花生豆又没有把故事讲完整,我只好呆在屋子里的一处旮旯,等着她忙完手里的活。我当时还在想如果我把二叔的事情全都告诉她,或许她还会给我其它什么好吃头呢。
我终于有些明白,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了,食物的魅力竟然就在这里。这让我兀自想起了那些说书的人,你给他们掌声和钱,他们就乐此不疲地重复那些老套的故事。我便觉得或多或少有点儿对不起二叔,我在此搬弄他的伤心事竟是为了换回一把鱼皮花生豆?
那人眼睛都懒得睁一下。他从一进屋就那么仰面躺在椅子上。我这才看清干部模样的人就是大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