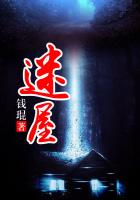这就对了。各有各的活法。说到底,是西瓜的心机好?还是南瓜的本色好?是西瓜的尊荣好,还是南瓜的平凡好?是西瓜的华丽好?还是南瓜的纯朴好?是西瓜的巧舌如簧好?还是南瓜的闷声大发财好?是西瓜整天被人吹吹拍拍好?还是南瓜的悄悄过自己的小光景好?狗有狗踪,猫有猫道,各有各好。这个世界多元化,虽然西瓜永远也做不成南瓜,南瓜这辈子也变不成西瓜,可是,只要人生乐趣所在,想做西瓜的,就做西瓜好。想做南瓜的,就做南瓜好。
那就这样定了:诸位都去做西瓜,我来做个悄悄生长的大南瓜。不是有句名言是这样讲的?走自己的路,让西瓜去说吧。
你看你看标点的脸
在一个小说里看到一句话:“我就像个句号,没法儿表达疑问感叹或省略。”心里一动,像开了天眼,刷地一下,一排标点当前,我看见它们各自长着不同的脸。
叹号就像年青人,蹦迪、泡吧、玩轮滑、说脏话,要不就是热血煮开了,喊口号喊得声音都劈了叉,可惜下暴雨一样,激情一散,各回各家。热情的火焰燃个冲天,烧得越猛,熄得越快。
句号就是个扑克脸,央视的新闻主持人也是扑克脸,说不定就是私底下打球那表情都不会变,可是那不表明脸底下没藏着七情六欲。文字表达好了,情感铺垫到位了,一个句号能顶一百个叹号使。当然文章里全都是句号那也不成。“草帽。草帽。麦秆儿编。藤编。白色的草帽。黄色的草帽。新的草帽。半新半旧的草帽。破了檐儿落了顶儿的草帽。写了农业学大寨的字和没写农业学大寨的字的草帽。”这是我们本地一个已故的老作家当年调侃几十年前流行的意识流小说时仿写的一段话,吐啊。
顿号的间隔太短,用多了像打机关枪,于是有时顿号逗号皆可的地方我就用逗号了,当然实在避不过的时候,顿号还是要一顿一顿地上阵的:“杀猪,煮肉,灌肠,炸丸子球、豆腐块,围着围裙,扎撒着油手,当当地剁馅,猪肉馅,牛肉馅,羊肉馅,扫地,擦窗,逛超市买烟、酒、瓜子、糖,大包小包往家搬……”短短一段话里逗号和顿号一起飙戏,为的是让人看着欢喜,像一地炮屑散梅红,小哥俩手搀手撒了欢地蹦。
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欢顿号的,跟弹簧兔似的;逗号就一豆芽菜,软软的,没什么脾气,你一逗它它就眯着俩眼儿笑;句号是个酷酷的终结者,怎么愤怒、激动、快乐,一个句号一封,得,就跟盖了张铁皮似的;叹号太夸张,用不好就显出外强中干的相;省略号太抒情,有点像琼瑶笔下沫沫唧唧的女主角,你要是不理她,她就给你哭个没完,嘤嘤嘤……嘤嘤嘤……;破折号是个老学究,长着山羊胡,老想给人指点什么,用句现时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好为人师神马的,最讨厌了,所以一般情况下都躲着。
其实我也就一句号的脾气,写文章也是面瘫式,用什么标点符号都循规蹈矩,不喜欢“?!”或者“!!”或者“!!!”或者“???”或者“…………”地用一堆,所以看见年轻孩子们写的网络小说里用这一堆我头疼。情多必滥,钱多也滥,人多更滥,撒谎骗人多了叫下三滥,符号多了也一样,一个字:滥。
有的时候四下里看看,人也真的就跟标点符号一般。有的人像问号,时刻都想化身好奇宝宝,爱迪生、爱因斯坦神马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像叹号,就是京剧里的张飞张翼德,喝老白干,吃肥肉片;有的人像省略号,总让人看着别有深意似的,深意在哪儿,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就知道一人,钱钟书的《围城》里的,叫韩学愈,跟方鸿渐一样买了一个假文凭回国混事的,就敢夸口娶了个美国老婆,其实不过是在中国娶的白俄;夸口说“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其实不过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中国少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和“史学杂志”的通信栏:“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某处接洽”。就因为他说话少,慢,着力(好掩饰他的口吃),听上去就上带着隐形的省略号,让人自动补齐他省略掉的内容为满腹经纶,是以做得了系主任--所以天下的事蛮难讲;有未竟之志的人也是一省略号,省略了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文友去世前说的话:“我刚琢磨出来写文章的路子了,结果就得走了……”大部分人还是清清淡淡的句号;小孩子是一个个的顿号,尤其排着队出现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个的,看着好玩死了。
要这么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基本上也就可以用标点符号概括了:在娘肚子里是逗号,出生了是顿号,再大些化身成问号,再大些青春期了变叹号,再大些,看得秋风独自凉,省略号,再大些,俩眼一闭,驾鹤西去--句号。
你看你看,标点的脸,逗号长着山羊胡,问号拄着拐棍儿,叹号戴着耳坠儿,省略号是一串匀实的小呼噜,句号是个小子弹,凡事一般都由它给出个结局,一枪命中靶心,希望这个靶心只有两个字曰幸福。
普鲁斯特和马二先生
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繁星如沸”四个字,运笔近妖,把我惊到。
后来才发现他的师尊是苏轼,写过“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夜行观星》)不过坡仙被纪晓岚在“小星闹若沸”下重重打一道墨杠,批“疑为流星”。
这位纪先生,他还真当小星如蛙,在夏天的夜里扯着嗓子叫“呱呱呱,呱呱呱”,然后一个个像曳光弹,拖着长长的光尾巴,嗖一下一个踪影不见,再嗖一下又一个踪影不见啊。
文字的世界多陷阱,上宽如洞,下似尖针,一副牛角模样,想不到真有人前赴后继,猛往里钻。
宋祁《玉楼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就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
既是红杏不能“闹”,那么梅也不能“闹”,灯也不能“闹”,毛滂《浣溪沙》的“水北寒烟雪似梅,水南梅闹雪千堆”、黄庭坚《才韵公秉》的“车驰马骤灯方闹,地静人闲月自妍”都该毙掉。盛夏去白洋淀,真是如范成大《立秋后二日泛舟越来溪》所讲:“行入闹荷无水面,红莲沉醉白莲酣”,荷叶大如伞、小似钱,摩踵挨肩,闹市一般。换“盛荷”、“绿荷”均失其神,这样又该怎么办?
文字这种东西本来好比千面观音,一时它喜欢素白颜面,青丝松绾;一时它又喜欢盛装严饰,满头钗钏;一时它又变成尤三姐,戴着耳坠子,敞着白脯子,翘着小金莲……千变万化一张脸,如鱼,如花,如响,如云,难道非得要把它化成铁汁,倒进模子,再磕出一把把壶,一只只犬,一枚枚不差模样的钱?
《儒林外史》里有一个游西湖的马二先生,大长的身子,高高的方巾,乌黑的脸,捵着个肚子,一双厚底破靴子,横着身子在女客们的人窝里子乱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他的眼里只有热茶、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不解风情到如此。
这样的人若是不幸而做了批评家,是一定要把文字“规”成慈禧出巡时大轿前的顶马:一律昂着头,跨大步,却是蹄子似挨地不挨地的时候,慢慢地一蜷,又缩回来约一尺五,实际上走的却只有五寸,这样来和轿夫的步伐相等。就这样,马蹄子落地“哒哒哒”、轿夫走路“嚓嚓嚓”,方能尽显天家威严和光华。
所以他们读了唐代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定要指摘其不符合生物学事实:一粒粟顶多收一二百颗籽,怎么能收一万颗呢?唐代浮夸风实在太重了啊啊!读了陈丹青的“我站在屋后树林子里谛听山雨落在一万片树叶上的响声”,更会张着嘴笑:你真的数过了,不是9999片树叶吗?
想想就觉得冷。
普鲁斯特一生病卧在床,却是屋小而心大,乘着文字走天下,所以他的《追忆似水流年》才能字字句句皆如宝花。他居然想像着“巴马”这个城市因其名字而“紧密,光滑、颜色淡紫而甘美”;“佛罗伦萨”则仿佛是一座散发出神奇的香味,类似一个花冠的城市;“贝叶”的巅顶闪耀着它最后一个音节的古老的金光;“维特莱”末了那个闭音符又给古老的玻璃窗镶上了菱形的窗棂;悦目的“朗巴尔”,它那一片白中却既有蛋壳黄,又包含着珍珠灰;……美丽的“阿方桥”啊,那是映照在运河碧绿的水中颤动着的一顶轻盈的女帽之翼的白中带粉的腾飞;“甘贝莱”则是自从中世纪以来就紧紧地依着于那几条小溪,在溪中汩汩作响,在跟化为银灰色的钝点的阳光透过玻璃窗上的蛛网映照出来的灰色图形相似的背景上,把条条小溪似的珍珠连缀在一起……
所以马二先生和布鲁斯特即使同在一个时空也不能相见,否则布鲁斯特先生的文字会让马二先生晕菜,马二先生的批评会让布鲁斯特发疯。
春风春日,绿水小亭,就便有学究先生眉竖目瞪,也拦不住风流才子弹琴唱歌给美人听,文字的风情本来便是墙里桃花墙外红,看你有什么本事朵朵都禁。
不可太用力
年轻时爱过一个人,爱到什么都不肯要,什么都肯给,把自己踏进泥里,把那个人奉为上帝,整日整日地傻笑,整夜整夜地哭泣。梨花一枝春带雨?弱了,是汪洋恣睢的一江水。
等到散了,又恨他,恨到眼底流血,恨不得那个人立时三刻化烟化灰。恨到拿刀割自己,恨不得剜掉自己的眼珠子,再把心活生生地挖出来。
后来开始选择遗忘,直到再怎么用力也回想不起曾经有过的哪怕一丝过往。那个人回来了,说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有吗?瞬间茫然,我真的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爱得太用力,恨得太用力,遗忘得太用力,把自己都丢了。
如今人到中年,依旧火性不减。油烟机有油,水槽里有水,桌上乱翻书,心头怒激,一巴掌把书报全都横扫在地。天色已晚,鸟雀归巢,一家人说说笑笑,父亲、母亲、丈夫、女儿、狗、猫,听在耳里不是红杏枝头春意闹,是群猴大闹水帘洞的闹。
心中郁闷,出来散步,天上朗月高照,没心情冲它笑。
一切都不好。人生如打仗,想着打赢的,结果打来打去,总归还是输了。爱情没有尽善尽美,输了,家庭没有尽善尽美,输了,工作没有尽善尽美,输了,孩子没有尽善尽美,输了,一切都输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踉跄就倒了。等到清醒过来,想的是,我太累了,再这样下去就离死不远了。其实有什么呢,家里乱一些没关系的,吵一些也没关系,生活不完美没关系,生命不完美也没关系。松驰下来,软和下来,世界是朵花,有香气,停下来,闻一闻吧。
而且香气里有规则在。
古人聪明,早就窥破天机,谆谆告诫: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可是为情所困的照旧为情所困,想建功业的照样想建功业。都说慕仙慕道,却是世人种种,总是有老子不肯学老子,有庄生不肯学庄生。
犹记得《还珠格格》里,紫薇和尔康这样讲:
紫薇:尔康,不要难过。
尔康:我没有难过,只要你不难过,我就不难过,紫薇,答应我不要难过。
紫薇:尔康,我没有难过,我哪有难过,你不要难过,你看我都不难过了,你也别难过,不要难过,尔康!
尔康:好好好,我不难过,可是紫薇,你一定别难过,难过的已经都过去了!
紫薇:恩,我们都不要难过吧!
当时我就笑喷了。
演戏如恋爱,不可太用力,太用力遭人笑。你看《潜伏》里的小眼孙红雷,一张脸永远那么面无表情的,却是内里有大江大海,这叫演得好,演得到位;做官如演戏,亦不可太用力,否则就会太想把官做上去,结果把官做下来;做富翁又如同做高官,亦不可太用力,否则不是成了守财奴葛朗台,人死了,钱没花了,就是成了雅典的卡门,人活着呢,钱没了;做文人又如同做富翁,亦不可太用力,否则不是得个什么鸟奖就欣喜欲狂,就是为没得个鸟奖满腹闺怨;再不然就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你又不是屈原,怕不是世人皆醒你独醉,世人皆清你独浊?做美女又如做文人,更不可太用力,东施学西施太用力,结果成了效颦了;要不然就成了白雪公主的后妈,整天跟镜子过不去:“镜子啊镜子,这个世界上谁最美丽?”省省吧,任你轻扭蛮腰,款抬玉臂,轻掠云鬓,慢下楼梯,只因存了一个计较的心,最美丽的怎么也不是你。
炒股太用力易破产,破产易自杀。做穷人太用力易卑贱,做朋友太用力易散,昙花开得太用力,美则美矣,一夕即谢。养家太用力了,百病丛生,身心疲惫。作家太用力容易过劳死。书癖手不释卷,洁癖手不释抹布,爱官癖近官则荣,疏官则萎,美女癖俗名花痴……皆不是天地涵养万物生机的道理。
总之一句话,做人不可太用力,好比美人妙目莹莹泪,远胜于嚎啕乃至声嘶力竭。一切都要适可而止,就像周作人说的,于日用必需衣食之外,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人生如水墨,襟怀冲淡一些,坠下悬崖也能看见花,这叫境界。
种瓜不为得瓜,为的是看花
去书店,那么多的书看得我眼晕,就像皇帝在三万佳丽里挑选待幸的美人,一边辛苦挑书一边纳闷:这么多的书,有多少人看呢?偏偏我又刚刚签了一本来写--既然没有人看,我还写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