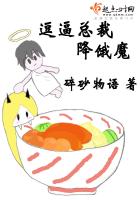谁也无法优雅地黑
网上呼叫朋友:“在吗?”她回了我一句:“干嘛!!!”三个感叹号砸得我差点背过气去。把界面关掉不理她,过了一会儿她自己醒过味来,忙不迭解释:“对不起啊,刚和人骂战,频道一时还没有调过来呢。”
我很好奇,说骂什么?为什么骂?骂出什么结果了?老实交代一番,我就原谅你。
她苦笑说,我骂赢了,不过觉得很可耻。
我更好奇了,赢了是好事,怎么会觉得可耻呢?
她发过一个聊天记录,说你自己看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知道是她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她有事,给一个人发信息:“您好,请问您是清凉雨先生吗?”
那人毫不客气地发过来一句话:“你他妈谁啊?”
我朋友气得手抖着往上打字:“你一定不是清凉雨先生,清凉雨先生不会像你这么没教养。”
对方开始脏字连篇地骂起来,朋友说我活了四十多岁啦,平时工作忙顾不得照顾爹娘,现在居然连累两个老人家被人家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于是对骂展开。
硝烟弥漫。
看得我浑身出汗。
看不出来温温柔柔、和风细雨一个人,骂起话来又快又狠,刚开始两个人能够拼个平手,后来就她骂三五句,对方才能骂出来一两句,再后来,她骂了十句八句不重样,对方居然颠来倒去还是那两句。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储备不丰富的小孩子,左不过十六七岁,想是偷了别人的号来玩--确实不是清凉雨,因为她找到清凉雨的另一个号码发去同样的信息,那边的回话彬彬有礼--这人想在网络上发挥一下平时发挥不到的流氓气质,结果踢到了铁板。靠在椅背,一声长叹,平时咋就没发现她有这么泼悍的一面?
“还有更可笑的哪,”她说,“那家伙看骂不过我,干脆叫了好几个人来加我好友,想群殴,被我拒之门外。开玩笑,我还真指着骂他们过日子啊。这就已经够恶心了。都搞得我恶劣因子大爆发,没办法优雅了。”
我大笑。
陈凯歌的前妻洪晃出身名门,外祖父章士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母亲章含之也是位出色的女外交官,这样一位名媛却自言在闹离婚的时候,把所有的恶劣因子激发出来,让自己整个人都变得狰狞万分(原话忘了,大意如此)。为了不让自己泥途堕落,干脆痛下决心,离婚了事。
真是,世界上没有谁想不优雅,却总有一些人和事会逼得你放下身段。
前阵子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人,刚开始我对他保持着相当的敬意,说话做事十分有分寸,不温不火,不即不离,算得上比较理想的同事关系。后来有一次,也是在网上交流的时候,他无意间把发给别人的话错发给我,要命的是,那居然是对我的毫不客气的议论和嘲讽。
这下子我如梦初醒,愤怒得无可名状。以前不知道从哪里看过一句话,记忆犹新,说的是一种“老娘们一样的小男人”,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撞上一个活标本。一个大男人,说小话告黑状献媚求宠东长西短,又要占便宜又要装清高,就是大多数的“老娘们”也比他格调高!从此他敢说一句我就敢堵十句,他做一件事我就使十个绊子,哪怕他满口都是“您”啊“您”的尊称,我也毫不手软,毫无怜悯,毫不同情。
不过,当时对着干觉得痛快,过后反思,却深觉自己的恶劣。是以下定决心,宁可放弃合作机会,也要离他越远越好,免得自己越变越坏。
平时教女儿慎交友,因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西谚又有一句话叫“羽毛相同的鸟一起飞”,现在发现用在自己身上也合适。若是不择人而处,择邻而居,就真可能成了麻生蓬中,扶而不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而乌鸦和鸽子一起飞,最大的可能不是乌鸦把羽毛漂白,而是鸽子把翅膀染黑。
几年前去荷花淀,里面有女子脱光了衣服在泥里摔跤的表演,那样婀娜的身姿,用着那样野蛮的姿势,染着那样腥臭的污泥,就像是莲花被摁着花瓣在泥里打滚,让人心痛。说到底,无论你再怎样想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士,只要白沙在涅,就谁也无法优雅地黑。
小心难驶万年船
“小心驶得万年船。”
明明是好话,听上去却既胆怯又阴险,好比小脚老太着绣花鞋,一步走一步看。可是小心小心再小心,活得不累吗?头发不白吗?皱纹不深吗?
陈胜起义,朱元璋兴明,是小心思虑的结果吗?若再三思虑,小心再小心,恐怕到死一个为奴隶,一个要饭吃。
比尔·盖茨的帝国是小心思虑才结构出来的吗?若是他当年思虑再思虑,小心再小心,结果很可能是乖乖地大学毕业,弄得好了搞个大学教授当当--可是现在大学教授满地跑,全球首富可只有他一个。
还有那个张季鹰,做事实在够冲动,像个无牵无挂的老光棍。有人劝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回答:“使我身后有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结果想起家乡的莼菜跟鲈鱼,官位也不要了,挂冠归里去也。他原是齐王的官,不久以后齐王被杀,他却幸免,人说他有先见之明。哪里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反而是他沾了凡事不那么“小心”的光,想到哪里便做到哪里,即时一杯酒有了,身后名也齐活,两赚。
司马懿被诸葛亮耍,诸葛亮就吃准了他那“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个性,所以才会在危急关头大摆龙门阵,一座空城哄得老家伙进不敢进,只好摆手退兵。
深入地想一想,所谓的行驶万年船的“小心”,不过是打着智慧旗号的恐惧,恐惧的背后却是一颗脆弱的玻璃心。害怕冒险,害怕前进,害怕失败,害怕失了声名,害怕降临不幸。因为害怕而退缩,如行冰面,步步担惊,好比满树的花开出去,没一朵是敢开错了的。
狼在草原上驰逐,既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害怕别人入侵--只要你敢;只有羊才会固守羊圈,屁股死抵着围栏,向往着外面的绿水青山,打死也不敢向前,还美其名曰“小心驶得万年船”,却忘了小心的结果未必是行船万年,很可能大铁船搁浅在小水湾;冒险的结果最坏也不过是失败,失败不过是证明此路不通,敬请绕行,总有一条路抵达成功,总好过一步也不敢迈,人生褪色成一张挂在墙上的老相片,江山寂静,岁月无声。
恐惧的负担甜蜜似糖,看穿了也不过是土做的薄墙,胆放大,推倒它,小心难驶万年船啊。
山有木兮木有枝
我认识一个人。偌大的江河,我只不过是一条在文字的世界里游弋的小蝌蚪,他却当我是占了他地盘的大蛤蟆;偌大个天空,我只不过是一只掠飞而过的燕雀,他当我是抢他的风头的鸿鹄。
他恨不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一次两招无数次地出了明招出暗招。招数有的用老了,有的没用老,到最后七七八八都被我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君仇我兮我又怎么能不知。
不是不愤怒的。相识数年,我敬你,你恨我;我推你助你,你厌我陷我;我当你是友,你以我为仇。
走在路上,郁郁不乐。人性之恶,让我哆嗦。
有一弃狗,卧在墙边,被车撞了,奄奄一息。看着它,转回去又走了两站地,到超市给它买了一根火腿肠吃,它却只是痛苦地痉挛,张不开嘴。一边走一边往回看,心里想流泪。晚上散步,特意弯过去,它还在,又去买了一根火腿肠来,和一瓶水。把盖子拧开,瓶身微斜,给那狗一滴一滴地倒下去,狗就张开嘴巴伸舌头去接,渴啊!一瓶水喂完,把火腿肠掐成指甲盖大的小块,用竹签插起来送过去,它还是不能吃。
第二天一早,又起一个大早,拿一袋纯牛奶去喂,只有这样吃流食了,希望能养得好起来。我不是基督徒,却在心里求上帝:如果能救的话,就让它活过来吧;如果不能救的话,就让它少受点罪吧。
一日三餐皆如是。第三天晚上,仍旧弯到了那里,它却不在了,地上牛奶的湿痕犹在,可能是已经死去,被清洁工收走了吧。心里一阵阵地难过,走回家去,门口一只流浪猫正候着,瞧见我影子就喵喵地跟汽笛一样叫。把牛奶倒给它,上了楼,又想起那个人的事。这种被阴的感觉真是……难过。
把这事跟朋友说,朋友说:如果你们换个位置,你敢保证你不会这么做?
我不敢。
我也有阴暗的一面。很多时候,名利当前,我也想把人踹飞,自己上阵。可是总归是心里想想,脚却伸不出去。我不忍心毁了别人的前程,更害怕自己的心掉进灰堆。
我也知道照顾流浪的猫狗麻烦,也巴不得想清净一下,可是仍旧一日三餐送去给它们吃。我也知道把钱捐出去心痛肉痛--都是我熬夜爬格子挣的咧!可是那患病、失学、遭灾的人更可怜。我不忍寒风凛冽,我吃暖炉人挨冻,我更害怕漠视别人的苦难会让自己的心枯死僵毙。
说到底,我爱的恐怕不是世界,而是自己。世情如炉,人心似铁,叮叮当当,火花飞溅,我不敢把我的心炼成杀人的刀,坑人的剑。哪怕世风贫瘠,落红成泥,我的心里总得留一个地方,种一个小小的花园给自己。
这个“朋友”几次组织大家给人捐款,别人纷纷上前,他负手而立,隔岸观火,无动于衷。他把自己定位在衣履光鲜的组织者,却忘了救人于水火,他还有另一份慷慨解囊的责任。他的心已经腐朽成柴。
可是再怎样的冷漠、仇视、自私,恨的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厌的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染污的更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打压的永远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这是真的,二十年如一日,靠踩人搏出位,结果人也没有踩下去,位也没有升上去--不是别人不让他升上去,是他让自己没有办法升上去--哪个上位者用的不是人,谁敢用鬼?好比一只蚂蚁困死在地牢里,一颗心永远、永远地暗无天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浩浩大军里面,他只不过一粒小卒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种花得花,种刺得刺。世间规律就是如此,不信你就试试。
上当时代
1988年,来自意大利的贝尔托鲁齐的电影《末代皇帝》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九项大奖。当他被人问及中国印象,他说,“最叫我震撼的是人们的脸,这些脸反映出一种前消费时代的朴素。”
所谓前消费时代,依我的理解,大约就是被消费大潮彻底淹没之前的时代,亦或说消费时代之前的非消费时代。总之,就是一件衣裳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传小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就是一碗米蒸一锅饭,剩下半碗不舍得扔,搀上青菜煮成汤淘饭的时代。
当我们处在朴素的前消费时代的时候,西方正在五光十色的消费时代里大踏步行进。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初到美国,最让他震撼的不是人们的脸,而是堆积如山的物资:八成新的家具,用了两三年的彩电,簇新却已过时的精装杂志,这些东西被毫不留情弃置街头,变成华丽的垃圾。
最初的震惊与不解很快过去,我们的消费时代也紧随而来。从最初的飞鸽、凤凰自行车,到单卡、双卡录音机,到音响,到VCD、DVD,家庭影院,再到现在的名车,豪宅,人们的消费水平一日千里,呈现一种真正的“发烧”态势--发财之后拿钱来烧的态势。
这种状态诞生了数不清的“发烧友”,凭着深厚的财力跟高科技较劲。比如音响发烧友,讲究的不光是音响的价位和摆放位置,而且要给音响特辟一室,专门聘请专业技师安置,一切昂贵费用均由自己承担,然后在无人之际,静静聆响音响带给自己的听觉震撼。画家陈丹青由此说过一段话:“……音乐、音响,究竟哪一样才是他们的福祉?总之,那是一种人类才有,又被人类赋以艺术的名义而能永不疲倦的物质热情。”
这段话其实可以无限止地套下去:“绘画,绘画的工具,究竟哪一样才是绘画发烧友的福祉?”“手机,手机的款式,究竟哪一样才是手机发烧友的福祉?”“服装,名贵的手工服饰,究竟哪一样才是服装发烧友的福祉?”“健身,健身房以及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究竟哪一样才是健身一族的福祉?”这个反问所代表的整个消费时代的发烧格式就是:“精神、物质,后者才是消费时代高消费一族的福祉。”
不知道是我们心中压抑已久的物质热情点燃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消费时代,还是这个轰轰烈烈的消费时代掀翻了我们心中的欲望之海,反正现实就是,我们正无比奋勇地畅游在这个淹得死人的消费时代,用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去质换电光石火的一时之快。
是真的一时之快。从平面直角到等离子,从蹲机到壁挂,无非一台电视,却以一个个的新名词掩盖住它那听声放影的本质,使它约等于富有、气派,然后凭着此种名义掏光我们的银子;从一居室到二居屋,再到小别墅大豪宅,说到底只不过一座房子,却用大而无当的面积和美仑美奂的装饰掩盖住它遮风避雨的本质,让它和身分、地位挂起钩来,然后让数不清的房奴负债累累,喘不上气。明知道大而无当,多也无益,但我们仍旧以无比真诚的姿态消费着我们的消费时代,因为我们坚信,这是最正确和神圣的生活方式。
日前看豫剧《朝阳沟》,很诧异:无非一个满纸口号和极端模式化的戏剧情节,布景也粗糙,人物也简单,服装也不鲜艳,戏剧冲突只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新农村的基础上,居然一跃成为经典,直到现在,还在有无数人,包括我,被其中的真诚和热情感染--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大神话的背景下派生出的一个真实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