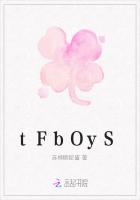甜糯米粥,我们这一带,无论城乡,都叫“米膏儿糜”。
小时候,我嗜食米膏儿糜。
其实,这只是将糯米煮成粥,加上红糖而已。
但我小时候却难得一尝。糯米红糖,这都是逢年过节用的,平日里,尤其是穷人家,是舍不得吃的。
我们这里的年节,大都要蒸糕呀粿的,还有八月十五中秋吃的麻糍、冬至吃的冬至圆儿,都要用到糯米红糖。乡村人,平日里省吃俭用,而年节里,则无论如何也要张罗些节日食品,祭祀鬼神祖宗,节省不得的。
年节各有其节日食品,但就是没米膏儿糜。在年节食品中,米膏儿糜是登不了这大雅之堂的。
用在年节的糯米、红糖,竟全没用来煮我嗜食的米膏儿糜!好在妈妈有时被我缠不过,看我怪可怜的,取出点年节要用的糯米红糖,煮碗让我打打牙祭。
我好吃米膏儿糜,几乎无人不知。因此,常被利用、哄骗,上过当。但过后,人家故伎重演,竟仍然有效。
我有位姑母,并非我爸的亲姐妹,而是我爸义父的侄女。因招婿,所以同住一社。这姑母家,不愁吃穿,在社里,也在中产之上。
我小时候,妈妈常带我去这姑母家。她们拉起家常来,没完没了。我总是吵着要走。于是姑母说:“我们煮米膏儿糜哩。”我一听,就安静下来。但过一阵子,不见米膏儿糜,我又吵着回家。姑母不高兴地说:“就熟了,急什么?”要说,早就该熟了,但总熟不了。最后,是在人们的一片哄笑声中,妈妈带我回去。
这姑母的米膏儿糜,在我的记忆里,从没熟过。
我读小学二册(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家中断粮。我和妹妹饿得实在不行。妈妈苦于没什么可给这家中两个最小的孩子吃,就去拔些“猪母奶儿”(马齿苋)。她怕让人看见,被人耻笑,是偷偷拔来煮给我与妹妹吃的。
一天,妈妈洗完衣服,想好久没浆过,于是,端只陶钵,去向我那姑母讨点米汤。我们这里,都是将米汤加些水,然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放入揉搓,让都沾上这汤,晾晒上。干后,这衣服就会很挺括。
终于讨来小半钵米汤。妈当时口渴,于是喝了一口,就只一口,她不喝了,“快!快!快来喝!”她把米汤给我和妹妹喝。我与妹妹咕嘟了几口。我眼睛刹时一亮,就像软蔫蔫的枯黄小草,得了甘露的滋润,顿时有了活气,人一下子精神起来。妹妹也一样,好久未有水米沾牙,这虽然是米汤,但多少有“五谷气”,得了这“气”,人即有了人样了。
妈说:“留些给你们哥哥喝。”是呀,我们都小,做不了什么事,但哥哥却天天要上山砍柴割草去卖,以买些番薯来充饥。
哥一担柴草刚挑到门前放下,我就急忙说:“哥,有米汤喝!我们都喝了,你快去喝。”似乎在向他报告什么天大的好事。
哥坐在门槛上喝米汤,妹妹站在一旁,痴痴看着。哥拉过妹妹,把剩下的两三口喂了她。
我至今不知道什么“琼浆玉液”,我就只知道我儿时喝过那几口米汤,这是我一生永志不忘的米汤呵!
姑母病逝前,我妈天天去看望。终于姑母对我妈说:“过去,我们糜饭,上顿塞下顿的,也从没让你们吃上一碗。唉--”她老人家为此而负疚,愧悔不已。
我当时已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没能去看望这老姑母。后来,听我妈告诉我老姑母临终前说的话,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是的,我从没在这姑母家吃过一口饭,更别说什么米膏儿糜了。但那几口米汤,胜过我有生以来嗜食的所有米膏儿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