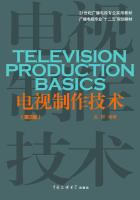一
船名叫做“醒狮”,这小小一组的旅客一共是五位,开船的那一天不迟不早是阳历元旦。
预先打听过,这条“醒狮”要走这么十天才能到埠。但没有办法,十天就十天罢。“沙基惨案”以后,“香港”交通还没恢复常态,而且五位之中那个常常自吹他有“阔本家”的“准小开”不知从哪里听来了无稽之谈,象一匹鼓起了肚子不怕吹垮的癞蛤蟆,一口咬定要是在香港过身,准会惹起麻烦。就这样,买票等等手续都由“准小开”一手包办。
轮船公司也是抓住机会打算在这一条航线上插一脚,急急忙忙把货船改了装,据说一共才只走了三班,这就可想而知,这条“醒狮”的设备不会高明到哪里去的。然而“准小开”单凭“掮客”一面之词,只知道这是一条“新船”,且又一定的是“官舱”,一幅美丽而舒适的近海旅行的图画在定妥舱位的时候便装进他脑子里了;因此,三十一日上午,为了周到起见,他亲自上船一看,好容易揪住一个茶房带路,从船长室抄过一排虽不怎样富丽堂皇但也还精致干净的房间,而后到了船尾,当那带路的茶房指着一个长方形的黑洞,说“官舱就在下边”的时候,“准小开”简直是弄昏了。他看看黑洞右首是雏鸭栅,左首是厕所,突然伸手捏住了鼻子,转身便走,不发一言。
那天午后,“准小开”的同行者接到电话:交涉办妥了,船上人让出了一间房,有六个铺位,你们赶快上船,迟了也许又有变卦,到船上找西崽头目就得了。
四点钟左右,Y君和两个同伴挤在那船上人让出来的房间里,三个人站成一排,侧着头我看你,你看我;三层的铺架挡在他们面前,稍稍一个不小心,就会碰鼻子,而他们的背脊却已贴着了板壁,三位之中衣服穿的最厚的刘,几乎连转个身也怪费力。
“不对,不对,一定弄错了!”刘大声嚷着,他那凹面孔上亮晶晶地冒出一层油汗,平时的三分傻气七分少爷派,此时掉过头来足有七分的傻气了。
“怎么会弄错,”靠在门框上那西崽说:“头目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你去叫头目来!”刘很神气地喊,面对着那三层铺架。
“头目上岸去了,你有话同我说!”
“那——那——”刘用臂推着Y君,表示要他让出路来,“那我就找你船上的买办。”
按照这间房的极端经济的布置,Y君亦只能用臂推着那身在门外而又靠在门框上的西崽要他先让开,但是Y君并不这么办;他攀住了最上一层铺架的木板,身子一缩,居然很顺利地塞在中间一层的一个铺位里了,好象他早就有过训练。
“错是不会错的,”身子折成两半似的“坐”定了以后,Y君慢吞吞地说。他把头伸在上层的铺板之外,悠悠然笑了笑,又说道:“我们的准小开到底有点手腕,找到了这样特别的房间!”
那西崽也笑了。“当真,这条船上就数这一间房是呱呱叫的,”他斜起半只眼看着刘说,“你瞧,亮爽,空气好,那边是船长室,这对面,就是大餐间。”
刘不作声,扁着他那臃肿的身子慢慢地挨到门边,自言自语道“也罢,等小开来了再说。”他抬头朝前看,这才发见那三层的铺架是紧靠着一排玻璃窗把窗做死了的,窗外就是水和天,要不是上下层的铺位距离太小,莫说挺腰而坐绝对不成,就连上去下来都得横着身体平塞进去,那他是没有理由还觉得不能满意的。他轻轻叹口气,也想学Y君的样,怎生设法在最下层一个铺位上坐下来,可是耸着屁股作势蹲了两下以后,终于知难而罢,只转过身,把背梁靠住了铺架。
“定规了罢?”西崽看见刘也驯顺得多了,便想把使命完成,“头目交代过,请你们把房间钱付清;收过定洋二十五块,还差一百……”
“怎么!”刘大声叫了起来,“我们是打了票的呢!”
“那不相干,船票是船票,归公司,这是我们的小伙,我们自家住的房间让给你们的。”
刘当然不肯让步,并且忘记了自己本来就不打算要这间房,抖擞精神,据“理”和那西崽争论,刘是学法律准备做大律师的,眼前既然有这演习的机会,当然要拿出他的看家本领。然而不幸,刘的“普通话”土音太重,本来就难懂,他的上海话呢,一开口就叫人头痛,现在他又兴奋过甚,更加口齿不清,何况还夹着那么多的法律术语!那西崽弄得莫名其妙,只好光着眼看刘一个人在那里演说。
可是还没开过口的S却打断了刘的好兴致。S不耐烦地叫道:“等小开来办就得了,何必跟他多说废话!”
刚才他们三人进这房来,S是第一位,现在如果要出去,他得等待到最后;他一进来就有这样的感觉:这间房好比一个狭长的口袋,而他是被装在袋底了。他根本看不见那西崽的面孔,可是光听他头目长,头目短的,就觉得这是个奴才嘴脸十足的人,从心底里厌恶起来,而他之所以插这么一句,倒不是想戳破刘的气泡,而是要撵走那西崽。
果然,反应马上就来,第二次又听到“小开”二字,那西崽似乎恍然大悟,立即把客人口里的“小开”和他自己脑子里的“头目”并排一比,当下就得出结论来:
“好,好,你们等你们的小开,我等我的头目,让他们自家当面谈罢。”
这可把刘气坏了。他哼了一声,转眼朝S看,S不理会,凝眸正望着这“狭长口袋”的一角。那西崽也已走了。刘叹一口气,忽然有了寂寞之感。
房间的右上角,靠近门口,有一具硕大无朋的电铃,S惘然望着的,正是这个,他想象十天航程之中,这具电铃不知要响多少次呢!他又猜想这电铃是通到船长室的呢还是什么大餐间?他又想到,要是在深更半夜,这伟大的电铃忽然叫个不停,那他和他的同伴们该怎么办:相应置之不理呢,还是到处去找那班鬼知道躲在哪一角的西崽?
这当儿,房外老是有几个人来回地踱着,而且在门口站住了朝房里看,闷在这“袋底”的S当然不会看见,可是他听得Y君的慢吞吞的口音十分正经地在说:“要进来看看么?今天换了人了。今天是我们在这里了。没有什么好看的,也没有咖啡、牛奶、芥哩鸡、蛋炒饭。”
这样说的时候,Y君的缓慢而冷静的音调以及他那事务式的表情,往往会给人异常强烈的幽默感。门外的窥视者笑着走了。刘也笑了,笑声中带点儿愤懑。Y君自己却毫无笑容,他从那夹板似的铺位里脱身出来,解开了他那有名的灰布大衫,露出里面的棉袄,棉袄的两只口袋都装得满满的,这里有日记本,信札,当天的报,新出版的刊物。他脱下大衫,郑重其事的摺好,放在一边,就拣出一份刊物,靠在铺位上读起来。
曾经有人说过一句笑话: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标。“五四”时代在武昌听过Y君第一次讲演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Y君时,首先感到亲切的,便是这件灰布大衫。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是可能,Y君这件灰布大衫是应当用尽方法找了来的。
现在且说他正在看书,而且摸出钢笔,按住书角打算记下一点感想,旁边的刘蓦地喊了一声,接着又连声招呼道:“小开,小开,我们都在这里!”
一张女型的面孔随即在门口出现,皱着眉头,眼光扫了一下,便抱怨道:“这样一间房么,怎么住得!”
“这不是你找的?”刘立即反诘。
“准小开”并不回答,靠在门框上,却诉苦道:“打了半天电话,嘴唇也说破了,结果是这么一间!”
Y君一面在写,一面却轻轻提了一句:“恐怕还有别的问题呢!”
“那倒不会,”这是“准小开”的非常有把握的回答,但又马上转了口气道:“刘,我们一同去办交涉去,这一间是不能住的!”
以后的发展并不怎样复杂,当Y君索性爬在那中间一层的铺位上,从看书做札记而发展为写一篇短文的时候,他的同行者来搬行李了;“准小开”终于另外物色到一间,这回是水手们“情让”的,这回既无电话可打,当然是亲眼察看过了,房间未必干净,滑机油和其他什么油类的气味相当浓重,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挺直腰板坐了,而尤有特点,房内还有一只两尺见方的简陋的小桌子,“准小开”得意地说,“碰和不够大,打打圈的温是刚好的。”然而还有个小问题:已经打好的官舱票怎么办呢?“准小开”—口咬定“能退”,他还觉得刘不够大方,只肯先付五元定洋,而且再三说明,要是退不了票,成议作废。他们本来是定得有官舱的房间的,可不是?
然而到此为止,最热心于挑选房间的两位,却始终不肯到预定的官舱去看一看。那个长方形的黑洞以及雄峙两旁的鸡鸭棚和厕所,竟也把那还有三分傻气的刘吓得退避三舍,待到S发见了这梦魇似的所谓官舱并不和它的进口处同样地肮脏而黑暗,那已是他们在水手房里过了一夜而且“准小开”办退票不甚得手的时候。于是在“准小开”垂头无话,刘却自夸他幸而考虑周到,只付了五元定洋,而且和水手们言明在先的喜悦中,他们终于进了那命定的官舱。
船起锚前十分钟,他们同行者的最后一人也赶到了。这一位“马路英雄”根本不知道刘和“准小开”曾经怎样奋斗,——为了大概十天工夫的住所。他只听得Y君慢吞吞在说:“做西崽不成,做水手也不成,到头儿还是做官来了。”
臂上搭着他那件灰布大衫,Y君接着又说:还是他去住六号罢。六号里的另一铺位上,是个素不相识的旅客。
① Y君即恽代英同志。
二
将来的传记家或许要把这十天的航程作为Y君一生事业中的一个里程碑。革命的风暴从南而北,一年以后,在当时还是大熔炉的武汉,S又遇见了Y君,态度议论,一切都照旧,只是他那件灰布大衫已经脱下了,换上了军服——也是灰布的,那时候,Y君是那有名的军事学校的主持校务的三委员之一。
他住在学校里,他从不说起他还有一个家,当人们知道了他有家而且年老双亲都还健在的时候,便是那些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也吃惊不小。Y君向来不讲自己个人的事,他给同志们的印象就好象是《西游记》上说的“天生石猴”。人们后来又知道Y君每逢例假下午一定回家省视父母。父亲是小职员,也是不到例假便不会有闲的。好事之徒曾经统计,Y君每周的省亲之举,所费约一小时,不会多,但亦不至于少。
然而使人惊异的Y君的私生活还不止这一点。
大概是四月里的某一天罢,军校里忽然有了Y君请假一天的新纪录;显然不是因为生病,当天早上站在大门口警卫的学生明明看见他安步而出,灰布绑腿打的很整齐,清癯的脸上依然那样若有所思,冷静谦逊,而又精神饱满;当然并无紧急公事。校务委员会的秘书敢以人格担保。可是这一天从早晨他出了校门以后,人们就不曾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有几个客人来拜会,秘书代见,问起了何时可以面会的时候,秘书只好把Y君留下来的话转述一遍:明天,上午八时以后,直到晚上十点。
这一天,Y君算是很彻底地留给他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光景,办公室里果然又有了Y君,这是他规定的办公开始的时间。这天除了出去开会,Y君总在办公,见客,没有片刻的休息,但照旧是那样从容不迫;晚上,他又和同志们讨论问题,直到深夜。和他处得极熟的同志偶尔也问这么一句,“昨天你到哪里去了?”他只淡淡地回答道:“还不是在武昌呀,不过家里有点事。”
可是过不了两天,人们终于知道他这所谓“不过家里有点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说来奇怪,这消息还是那时在干教育厅的L君传出来的,而L君又得之于他的属员——本城某小学的校长,校长则是他手下的一个女教员告诉他的。原来Y君那天请假为的是结婚。新夫人也在那小学当教员,为了结婚,也曾请假一天。那位校长十分惋惜这消息他得的太迟,据说他向“各有关方面”报告甚至对Y君的新夫人当面道歉的时候;都曾冒冒失失地用了这样一句话:“真该死,我实在毫不知情!”
消息传布以后,Y君的同志好友们就议论纷纷。
对于Y君的此种简直一个人也不“惊动”的作风,同志好友们倒也可以存而不论,问题是:他们这样多的精明强干的人儿怎么这许多年来竟会对于Y君的“恋爱生活”——借用那校长的话,“毫不知情”?没有人能够记得,Y君主张过独身,但也没有人能够提出证据,Y君有过比较亲密的女友,——更不用说爱人。“然则也是五分钟恋爱的结果么!”五分钟恋爱是当时的流行性感冒,理论根据则为细磨细琢的“谈”恋爱在紧张革命空气中实在不可能。你说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观点罢,也行。而Y君当然也是抱有现实观点的人。
困惑之余,同志好友们所得到的一致,就是要求见见这位新嫂夫人。
Y君并不拒绝,可是很滑稽地拉长了脸说:“她,只在星期日还有点闲工夫。”
“那么,就是后天罢,后天是星期。”同志之一立刻接口说,那态度的严肃和口气的郑重几乎等于约期商量军国大事。
“哦,后天又是星期了么?”Y君象要瞌睡似的闷着声音回答,但又淡淡一笑道,“随你们各位的便罢!可是我不能奉陪。后天有一个会。”
看见朋友们的脸上都有惊愕之色,Y君又闷着声音慢慢地加说道:“反正她又不是囚犯,也还不曾生着什么需要隔离的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