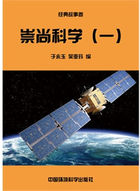不知不觉,在桂林已经住了三个月。什么也没有学得,什么也没有做得,就只看到听到些;然亦正因尚有见闻,有时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来有半月多,不拉警报了,这是上次击落敌机八架的结果,但也有近十天的阴雨,虽不怎么热,却很潮湿,大似江南梅雨季节。斗室中霉气蒸郁,实在不美,但我仍觉得这个上海人所谓“灶披间”很有意思;别的且不说,有“两部鼓吹”①,胜况空前(就我个人的经验言)。而“立部”之中,有淮扬之乐,有湘沅之乐,亦有八桂之乐,伴奏以锅桶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国气派。内容自极猥琐,然有一基调焉,曰:“钱”。
晚上呢,大体上是宁静的。但是我自己太不行了,强光植物油灯,吸油如鲸,发热如锅炉,引蚊成阵,然而土纸印新五号字,贱目视之,尚如读天书。于是索性开倒车,废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强光植物油灯,而复古于油盏。九时就寝,昧爽即兴,实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梦回,木屐清脆之声,一记记都入耳刺脑,于是又要闹失眠;这时候,帐外饕蚊严阵以待,如何敢冒昧?只好贴然僵卧,静待倦极,再寻旧梦了。不过人定总可以胜“天”,油灯之下,可读木板大字线装书,此公②为我借得《广西通志》,功德当真不小。
而且我又借此领悟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说来贻笑大方,盖即明白了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啸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
三星期前,忽奋雄图,拟游阳朔;同游十余侣,也“组织”好了,但诸君子皆非如我之闲散,故归途必须乘车,以省时间。先是曾由宾公设法借木炭车,迨行期既迫,宾公忽病,脉搏每分钟百八十至,于是壮游遂无期延缓。但阳朔佳处何在呢?据云:“阳朔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析成天柱者数十里,如楼通天,如阙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马啮,如阵将合,如战将溃,漓江荔水,捆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态”(《广西通志》),这里描写的是山形,这样的山,当然无可登临,即登临亦无多留恋,所以好处还是在洞;至于阳朔诸峰之洞,则就不是几句话所可说完的了。记一洞的一篇文章,往往千数百言,而有些我尚觉其说得不大具体呢!
还有些零碎的有趣的记载:太真故里据说在容县新塘里羊皮村,有杨妃井,“井水冷冽,饮之美姿容”。而博白县西绿萝村又有绿珠井,“其乡饮是水,多生美女,异时乡父老有识者,聚而谋窒是井,后生女乃不甚美,或美矣必形不具”。然而尤其有意思的,乃是历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在《广西通志》内有一段未定的消息,全文如下:“横州寿佛寺,即应天禅寺,宋绍兴中建,元明继修之。相传,建文遇革除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余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受浮屠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
建文下落,为历史疑案之一,类如上述之“传说”颇多,大抵皆反映了当时“臣民”对于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猜疑好杀,忆杂书曾载一事,谓建文进言,以为诛戮过甚,有伤和气。异日,太祖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难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复令建文拾之,既乃诏之曰:“我所诛戮,皆犹杖上之刺也,将以贻汝一易恃之杖耳?”这一故事,也描写到建文之仁厚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却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诸王子中。
明末最后一个小朝廷乃在广西,故广西死难之忠臣亦不少,这些前朝的孤忠,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皆蒙“恩”与死于“流贼”诸臣,同受“赐谥”之褒奖。清朝的怀柔政策,可谓到家极了。
说到这里,似乎又触及文化什么的了,那就顺笔写一点这里的文化市场。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这许多出版社和书店传播文化之功,自然不当抹煞。有一位书业中人曾因作家们之要赶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费之议③,遂慨然曰:“现在什么生意都比书业赚钱又多又稳又快,若非为了文化,我们谁也不来干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们现在之斤斤于稿费,毋乃太不“为了文化”。这位书业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里真相如何,这里不想讨论,无论主观企图如何,但对文化“有功”,则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个文化市场支撑起来了,而且弄得颇为热闹。
然而,正如我们不但抗战,还要建国,而且要抗建同时进行一样,我们对于文化市场,亦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书出,我们还须看所出的书质量怎样,还须看看所出之书是否仅仅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抑或同时亦适合于文化发展上之需要。举个浅近的例,目前大后方对于神仙剑侠色情的文学还有大量的需要,但这是读者的需要,可不是我们文化发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这两个需要比较起来,我们就不能太乐观,不能太自我陶醉于目前的热闹,我们还得痛切地下一番自我批判。
大凡有书出版,而书也颇多读者,不一定就可以说,我们有了文化运动。必须这些出版的东西,有计划,有分量,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文化市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对文化运动无大贡献,我们只建立了一个文化市场。这样一桩事业,照理,负大部责任者,应是所谓“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颇多的中国,出版家在这上头,时时能起作用,过去实例颇多,兹可不赘。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话,决非单独对出版家——宁可说主要是对我们文化人自己,但也决不想把出版家开卸在外,因为一个文化市场之形成,不能光有作家而无出版家,进一步,又不能说与读者无关。
我想用八个字来形容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这八个字不大好看,但我决不想骂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无非想把此间文化市场的几个特点加以形象化而已,这八个字便是:“鸡零狗碎,酒囊饭桶!”
这应当有一点说明。
前些时候,此间书业公会开会,据闻曾有提案,拟对抄袭他家出版品而成书的行为,筹一对策,结果如何,我不知道。说到剪刀浆糊政策在书业中之抬头,似乎由来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场上,据说已经相当令人头痛,目前有几本销路不坏的书,都是剪刀浆糊之结果。剪刀浆糊不生眼睛,于是乎内容之庞杂芜秽,自属难免。尤其异想天开的,竟有抄取鲁迅著作中若干段,裒为一册,而别题名为《鲁迅自述》以出版者。这些剪来的东西,相应不付稿费版税,所以获利尤厚,据说除已出版者外,尚有大批存货,将次第问世。当作家要求增加版税发议之时,就有一位书业中人慨然认为此举将助长了剪刀政策。这自然又是作品涨价毋乃“太不为了文化”同样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却已暗示了剪刀之将更盛。呜呼,在剪刀之下,一部书将被依分类语录体而拆散,而分属于数本名目不同之书中,文章遭受了凌迟极刑,又复零碎拆卖,这表示了文化市场的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这样的办法,既非犯法,自难称之曰鸡鸣狗盗,倒是这样的书倘出多了,若干年以后也许会有另一批人按照从《永乐大典》中辑书之例,又从而辑还之,造成一“新兴事业”,岂不思之令人啼笑皆非么?但书本遭受凌迟极刑之现象既已发生,而且有预言将更发展,则此一特点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拟题曰“鸡零狗碎”云尔。
其次,目前此间文化市场除了作家抱怨出版家只顾自己腰缠不顾作家肚饿,而出版家反唇相讥谓作家“太不为了文化”而外,似乎都相安无事,皆大欢喜。文化市场被支撑着,热热闹闹,正如各酒馆之门多书业中人一样热闹。热闹之中,当然亦出了若干有意义的好书,此亦不容抹煞,应当大书特书。不过,这种热闹空气,的确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这大概也可算是一个特点。无以每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来者,七十个出版家名月还出相当多的书,当然也解决了直接间接不少人的生活问题,无怪在作家要求维持版税旧率时,有一先生曾经以“科学”方法证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书到明天便只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价天天在涨,法币购买力天天在缩小。由此所得结论,作家倘不减低要求,让出版家多得利润,则出版家经济力日削之后,作家的书也将不能再出,那时作家也许比现在还要饿肚子些罢?这笔帐,我是不会算的,因为我还没干过出版,特揭于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值得专家们讨论。不过可喜者,现在还不怎样严重,新书店尚续有开张,新书尚屡有出版,这大概不能不说是出版家们维持之功罢?文化市场既然还撑住,直接间接赖以生活者自属不少;而作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近来还没有听见说作家中发现了若干饿殍,而要“文协”之类来布施棺材,光这一点,似乎已经值得大书特书了罢?用一不雅的名儿,便是“饭桶”,这一个文化市场,无论其如何,“大饭桶”的作用究竟是起了的。于是而成一联:
饭桶酒囊亦功德,
鸡鸣狗盗是雄才。
1942年6月30日桂林。
① “两部鼓吹”:当时,我住的小房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② 此公:陈此生同志也。
③ 那时候,排字工人排一千字的工资高于作家一千字所得的稿酬,故作家有“赶上排工”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