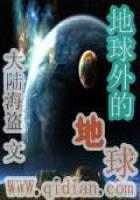从前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十三世纪那时候,有些青年人——大都是那时候几个新兴商业都市新设的大学校的学生,是很会寻快乐的。流传到现在,有一本《放浪者的歌》,算得是“黑暗时代”这班狂欢者的写真。
《放浪者的歌》里收有一篇题为《于是我们快乐了》的长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且生活着罢,快活地生活着,
当我们还是年青的时候;
一旦青春成了过去,而且
潦倒的暮年也走到尽头,
那我们就要长眠在黄土荒丘!
朋友,也许你要问:这班生在“黑暗时代”的年青人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他们寻快乐的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个,哦,说来也好象很不高明,他们那时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不过他们觉得犯不着不快乐,于是他们就快乐了,他们的快乐的对象就是美的肉体(现世的象征),——比之“红玫瑰是太红而白玫瑰又太白”的面孔,“闪闪地笑着……亮着”象黑夜的明星似的眼睛,“迷人的酥胸”,“胜过珊瑚梗的朱唇”。
一句话,他们什么也不顾,狂热地要求享有现实世界的美丽。然而他们不是颓废。他们跟他们以前的罗马人的纵乐,所谓罗马人的颓废,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跟他们以后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要求强烈刺激,所谓世纪末的颓废,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要求享乐现世,是当时束缚麻醉人心的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反动,他们唾弃了什么未来的天堂,——渺茫无稽的身后的“幸福”,他们只要求生活得舒服些,象一个人应该有的舒服生活下去。他们很知道,当他们的眼光只望着“未来的天堂”的时候,那几千个封建诸侯把这世界弄得简直不象人住的。如果有什么“地狱”的话,这“现世”就是!他们不希罕死后的“天堂”,他们却渴求消灭这“现世”的活地狱;他们的寻求快乐是站在这样一个积极的出发点上的。
他们的“放浪的歌”是“心的觉醒”。而这“心的觉醒”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他们是趁了十字军过后商业活动的涨潮起来的“暴发户”,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已经是一些商业都市里的主人公,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主人公。他们这种“自信”,这种“有前途”的自觉,就使得他们的要求快乐跟罗马帝国衰落时代的有钱人的纵乐完全不同,那时罗马的有钱人感得大难将到而又无可挽救,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了,他们也和十九世纪的“世纪末的颓废”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末的“颓废”跟“罗马人的颓废”倒有几分相似。
所谓“狂欢”也者,于是也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向上的健康的有自信的朝气蓬勃的作乐,以及没落的没有前途的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纵乐。前者是“暴发户”的意识,后者是“破落户”的心情。
这后一意味的“狂欢”我们也在“世界危机”前夜的今年新年里看到了。据路透社的电讯,今年欧美各国“庆祝新年”的热烈比往年“进步”得多。华盛顿、纽约、罗马、巴黎这些大都市,半夜里各教堂的钟一齐响,各工厂的汽笛一齐叫,报告一九三五年“开幕”了,几千万的人在这些大都市的街上来往,香槟酒突然增加了消耗的数量,……真所谓满世界“太平景象”。然而同时路透社的电讯却又报告了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也通过了扩充军备的预算,二次世界大战的“闹场锣鼓”是愈打愈急了。在两边电讯的对照下,我们明明看见了“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种心情支配着“今日”还能买“酒”的人们在新年狂欢一下。
我记起阳历除夕“百乐门”的情形来了。约莫是十二时半罢,忽然音乐停止,跳舞的人们都一下站住,全场的电灯一下都熄灭,全场是一片黑,一片肃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一抹红光,巨大的“1935”四个电光字!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雷一样的震动,于是电灯又统统亮了,音乐增加了疯狂,人们的跳舞欢笑也增加了疯狂。我也被这“狂欢”的空气噎住了,然而我听去那喇叭的声音,那混杂的笑声,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经失了主宰的号啕!
我又记起废历年的前后来了。这一个“年关”比往年困难得多,半个月里倒闭的商店有几十,除夕上一天,又倒闭了两家大钱庄,可是“狂欢”的气势也比往年“浓厚”得多。下午二点钟,几乎所有的旅馆全告了客满。并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来是上海人开了房间作乐,除夕下午市场上突然流行的谣言——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保安队缴械的消息,似乎也不能阻止一般市民疯狂地寻求快乐;不,也许因此他们更需要发狂地乐一下。影戏院有半夜十二时的加映一场,有新年五日内每日上午的加映一场,然而还嫌座位太少。似乎全市的人只要袋里还有几个钱娱乐的,哪怕是他背上有千斤的债,都出动来寻强烈刺激的快乐。在他们脸上的笑纹中(这纹,在没有强笑的时候就分明是愁纹,是哭纹),我分明读出了这样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乐能享的时候,且享一下罢,因为明天你也许死了!”
而这种“有一天,乐一天”的心理并不限于大都市的上海呵!废历新年初六以后的报纸一边登着各地的年关难过的恐慌,一边也就报告了“新年热闹”的胜过了往年。“越穷是越不知道省俭呵!”这样慨叹着。不错,从不穷而到穷,明明看见没有前途的“破落户”,是不会“省俭”的,他们是“得过且过”,现在还没“穷”,然而恐怖着“明天”的“不可知”的人们,也是不肯“省俭”的,他们是“有一天,乐一天”!例外的只有生来就穷的人,饿肚子的人,他们跟发疯的“狂欢”生不出关系。
我又记起废历元旦瞥见的一幕了。那是在“一二八”火烧了的废墟上,一队短衣的人们拿着钢叉、关刀、红缨枪,带一个彩绘的布狮子。他们不是卖艺的,他们是什么国术团的团员,有一面旗子。我看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舞他们的布狮子,一边兴高采烈地笑着叫着。我觉得他们的笑是“除夕”晚上以及“元旦”这一日我所听到的无数笑声中唯一的例外。他们的,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音调,然而他们的笑,不知怎地,我听了总觉得多少是原始的、蒙昧的,正象他们肩上闪闪发光的钢叉和关刀!
“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狂欢”,时时处处在演着,不过时逢“佳节”更加表现得尖锐罢了。我好象听见这不辨悲喜的疯狂的笑,从伦敦,从纽约,从巴黎、柏林、罗马,也从东京,从大阪,……我好象看见他们看着自己的坟墓在笑。然而我也听得还有另一种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朝气的笑,也从世界的各处在震荡;我又知道这不是为了“现世”的享乐而笑,这是为了比《放浪者的歌》更高的理想,因为现在到底不是“中世纪”了。
1935年2月20日。
交易所速写
门前的马路并不宽阔。两部汽车勉强能够并排过去。门面也不见得怎么雄伟。说是不见得怎么雄伟,为的想起了爱多亚路那纱布交易所大门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级。自然,在这“香粉弄”一带,它已经是唯一体面的大建筑了。我这里说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进去,一条颇长的甬道,两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视线。再进一步就是“市场”了。跟大戏院的池子仿佛。后方上面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象是一个蜂房。请你不要想象这所谓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戏院的池子似的。这里是一个小凳子也不会有的,人全站着,外圈是来看市面准备买或卖的——你不妨说他们大半是小本钱的“散户”,自然也有不少“抢帽子”的。他们不是那吵闹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主使。他们有些是仰起了头,朝台上看,——请你不要误会,那卷起袖子直到肩胛边的拍板人并没有什么好看,而且也不会看出什么道理来的,他们是看着台后象“背景”似的显出“X X X X库券”,“X月期”……之类的“戏目”(姑且拿“戏目”作个比方罢),特别是这“戏目”上面那时时变动的电光记数牌。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后墙上的横长方形,时时刻刻跳动着红字的阿剌伯数目字,一并排四个,两个是单位“元”以下,象我们在普通帐单上常常看见的式子,这两个小数下边有一条横线,红色,字体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里各处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使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不——应当说是少数人创造那红色电光的纪录,使它刻刻在变,使它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谁是那较多数呢?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池子外圈的人们自然是的,——而他们同时也是这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的助成者,虽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们以外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被外圈的人们包在中央的,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发动器。很大的圆形水泥矮栏,象一张极大的圆桌面似的,将他们范围成一个人圈。他们是许多经纪人手下做交易的,他们的手和嘴牵动着台上墙头那红色电光数目字的变化。然而他们跟那红色电光一样本身不过是一种器械,使用他们的人——经纪人,或者正交叉着两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个伙计匆匆跑来,于是那经纪人就赶紧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间去听电话了,他挂上了听筒再跑到池子里,说不定那红色电光就会有一次新的跳动,所有池子里外圈的人们会有—次新的紧张——撑不住要笑的,咬紧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吞的,谁知道呢,便是那位经纪人在接电话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种器械罢了。
池子外边的两旁,——上面是象戏院里“包厢”似的月楼,摆着一些长椅子,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纪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纪录着,象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挂在男子臂上,太年青而时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进来看看。那边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顶时式的裁制,和一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仰起了脸。电光的红字跳一,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红字再跳一,她慌慌张张把男子拉在一边叽叽喳喳低声说了好一大片。
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绸短衫裤,在人堆里晃来晃去踱方步,一边踱,一边频频用手掌拍着额角。
这当儿,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楼的铁栏干边往下面一看,你会忽然想到了旧小说里的神仙:“只听得下面杀声直冲,拨开云头一看。”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样把手掌伸出缩回,而外圈的人们怎样钻来钻去,象大风雨前的蚂蚁。你还会看见时时有一团小东西,那是纸团,跟钮子一般模样的,从各方面飞到那中央的人圈。你会想到神仙们的祭起法宝来罢?
有这么一个纸团从月楼飞下去了。你于是留心到这宛然在云端的月楼那半圆形罢。这半圆圈上这里那里坐着几个人,在记录着什么,肃静地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背后墙上挂着些经纪人代表的字号牌子。谁能预先知道他们掷下去的纸团是使空头们哭的呢还是笑的?
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他们更敏感的了。然而这对于谣言的敏感要是没有了,公债市场也就不成其为市场了。人心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193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