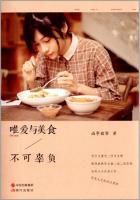夏夜,雨后。
下过了阵透雨,原野里一地清爽。
月儿钩一样伏在青云的夜穹里,大颗颗的星星眨巴着小眼儿,带露的草片叶上尽是光莹,风吹过了,竟带来了一股股熟透的稻香。
刘二爷坐在田埂上,半眯着眼抽着叶子烟,庄稼正熟呢!像饿坏的娃儿喝着甘甜的乳汁正咂吧着呢!好雨水!好雨水!刘二爷连说了两声就站了起来;习惯地拍拍屁股,就拍出两手湿乎乎的泥浆来。刘二爷捧着手在鼻前嗅了嗅后,这才吐了心里一口闷声。
夏夜,雨来之前。
儿子是天傍黑时进门的。儿子一脸倦色,沓拉着步子进来,沓拉着身子朝着刘二爷乘凉的那张竹椅里躺,半晌没个言语句。
刘二爷那时正编着箩筐,地要收了,季节不等人。刘二爷一双手一对眼只顾干着自家的活。咝咝吧吧地弄得满屋脆响。
儿子在城里做了官,刘二爷是去过一回的。从那后,就再也没踏儿子的门槛半步了。别人问起,他说在自个家里吃喝拉撒踏实些。就这话。
屋里仍是一片清脆。
儿子忍不住了,他这时坐直了身子,说,爹,咱给你说件事儿呢!
刘二爷一双眼不偏、一对手不歇,答,什么事呢?
儿子欠了欠身子,说,——爹,咱要走了——
刚回,又要走,你大忙人忙来忙去,要走的事跟爹有什么说呢?到地头跟你娘招呼去。
儿子讨了个没趣,脸倏地红了一阵白一阵。此时,屋里一片清脆、篾丝在他的眼里就像蛇一样“咝咝”地嘲笑着钻来钻去。他讪着脸说,爹,咱这回要远走了——
刘二爷这才停住手,说,又要升了么?什么职务?袋里掏出烟包来,边卷边看儿子笑。
儿子竟被他爹那笑弄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低下头半声也不吭。
刘二爷这才细细地看了儿子一眼,才十天,倒让他瘦了一大圈!刘二爷把烟点着了,猛地抽了一大口。又说,什么职务也不告爹一声,敢情是怕爹有什么事求你不成?
儿子的头却垂得更低了,斜里伸出双手来,给口烟行不?
你给我的烟我都全锁在柜里了,我倒忘了,刘二爷浅笑着站了起来,边开柜边说,听人讲,这烟就一支得比一斤粮食贵,嗨,这是啥烟呢?弄得爹都不敢抽。
橱柜里全是自己带回来的烟酒!看着刘二爷打开了柜子,儿子便楞呆住了:满满的一大柜,爹竟一样没动。儿子的额上就沁上一层晶晶的毛汗来。
刘二爷这时却已把一条烟直直地递了过来,儿子看见爹那双曾经让他引以自豪的大手竟也抖索着。他不敢接,飞快地踅过身子,背对着他爹说,爹,咱对不起你,咱得走了。
刘二爷叹了口气说,这么好的东西不用,会糟蹋了。说完,刘二爷手中的那条烟却生生地落在地上。
出了门,儿子却又磨蹭着不走。他像换了个人样,呆呆地游在夏日的风里。风很静,六月的稻香就很显出露水地荡漾了过来,满口满心的香甜,儿子使劲着抽了抽后,才幽幽说,爹,我不想走——
刘二爷又细细地看了儿子一眼,半晌才说,去吧!我会等你回来——
儿子去了。看着那辆车呼啸着开远了,刘二爷这才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他其实心里很闷,但他相信,自己不会把儿子害了的,至少自己的那封检举信在今后还可以给自己留下这个唯一的儿子;刘二爷知道,跟随儿子去的,可能是在他今后的身上再也看不见的某些东西。
下雨了么?是的,雨劈劈啪啪来了。
夏夜,雨后。
月色又渐淡去,山村的夜愈发朦胧而又厚重了起来。一只硕壮的田鼠不知什么时候钻了出来,“吱吱”地口里吐着贼音。欢叫着,就没提防让刘二爷的那口闷气给惊镇住了,丑儿八怪样定在那里,刘二爷一口唾沫直射,正中着,硕鼠吓得没命要逃,忙乱间头却撞在根电线杆上,昏得在泥地里滚了几滚,再爬起就倏地没了影儿。刘二爷这才乐了,骂道,这小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