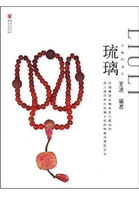书法作者临池挥毫时,总在有意无意地让纸上墨迹带有自己的性情、才识、心绪等心性之物。他总在使自己写成的字“人化”,成为自我的化身,又总在使自我“物化”,将自我投影到白纸黑字中。
唤起人的生命意识是诸多艺术品类都有的共同功能,但是书法由于具有“一字见心”的直接性和显示人的本质力量的深厚性,又具有其节律与人的感情节律的相应性,因此这种唤起的力量就最为强烈。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音乐能与它一比高低。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一本书中谈及音乐的本质时说了这样的话:音乐的最大意义不就是在于它纯粹地表现出人的灵魂,表现出那些长久地在心中积累和激荡的内心生活的秘密吗?音乐首先是个人的感受、内心的体验,它们的产生,除了灵魂和歌声之外,再不需要什么。
被人称作无声音乐的中国书法也能反映人的灵魂最深处的秘密。而人的心性又各不一样,加上个人所处的时代、书法师承及知识背景等等的影响,这就使得治书法者能写出各具个人特色、无有雷同的书法样式。这正是书法风情万种、常变常新的根本原因。
治书法者注入笔墨线条中的情性成分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性格,二是他的才识,三是特定情绪。本章先谈其一。以后两章谈其他两个方面。
书法有刚、柔之分。这是观书者最易察知、评书者最常提及、最能反映人的性格的书法类型。
具有刚性美的书法的体势为刚健、多力、奇拔、放纵、雄浑、痛快、磅礴。有的书论家还用这样的比喻来作形容:有龙虎威风,如快马入阵,如剑拔弩张,像力士挥拳,像崩山绝崖。
具有柔性美的书法的体势为婉秀、清劲、华丽、温厚、典雅、飘逸。
有的书论家用这样的比喻来作形容:如美女插花,如舞者低腰,像和煦春风,像美丽花木。
各体书法均有刚柔之分。其中表现得最明显、强烈的是法度较严而用笔变化最多的隶书和楷书。现举两个隶书石碑来作说明。
刻成于公元186年东汉末年的《张迁碑》骨力道劲,沉着雄浑,方整多变,极富阳刚之气。全文672字。它的作者总在有意地让线条向导致“崇高”风格的方向引进:每一个字力求向外伸展,以显出其体积巨大。
线条粗细不均,常用粗重的捺笔和尾端上翘的横画来显示其凹凸不平和奔放不羁。折处多方,以显出其坚硬多力。严肃之中显示出坚实,虽然笨重,却给人以痛快之感。它的作者没有署名,但我们根据这幅书法可以设想其人是一位勇猛敢斗、正色凛人、说话粗声粗气的男士。石碑现在移放于山东泰安的一座庙中。
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刻成时间早于《张迁碑》一年的《曹全碑》。全文900字。一字一行都写得轻巧、秀丽、匀净、自如。线条在运行中不是无力,也不是不受干扰,但是作者极善于因势利导,终于使它悠然自得地行进。人们观看这样作品会感到如沐春风,如同与老友会面、握手交谈,没有半点生分。它的无名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温文尔雅、宽厚大方的书生。该碑现放在西安碑林。
下面再举两则有名有姓的书法大家的故事,以进一步证明个人性情特质与笔墨样式的密切关系。
五代的杨凝式,是宰相的儿子。他自己也做过高官,但却佯狂装傻,不办公事,游山玩水,以寄情思于乱世之中,保持了一个有正义感士子的节操。他把满腔愤郁流注到书法线条之中,这就是一手天真烂漫、驰骋恣肆、淋漓快目、狂态百出、与他的性格特征相应的妙字。他的行书《韭花帖》,以走走停停、零零落落的松散形式,给人以自然而风流的印象。而他的行草《夏热帖》则是另一种态势:
不是前者那样的闲庭信步了,而是急走匆匆,越走越歪,纷纷乱乱,散散漫漫。这样的书作只有一个心灵超脱、物我皆忘、别有人生与艺术悟性的人才能写出。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少有壮志,不与俗同,在政治思想上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任宰相(参知政事)后,积极推行新法。他的文章以政论为多,大都是针砭时弊,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他的诗歌也都寄托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这位“拗相公”写的是一手老到却又不俗、有法而实无法的字,于飘飘不凡的笔墨中流露了他的睿智、正直,有时是刚愎、躁率的个性。
写到这里,需要指出,书法作品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作者的性格特征等概括性、抽象性的感情,而且这种表现在笔画中也是笼统的、抽象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性格与书法的形质特征很难明确地互相对应。这并非是书法艺术的短处,因为书法的创作者及欣赏者根本就不需要书法作品表现出什么具体的感情与性情,他们所看重的只是书法形式中所表现的一种“意味”、情调,所暗示的一种“情感倾向”,这正是书法艺术的长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