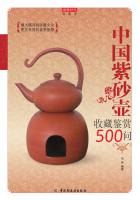近人陈望道曾对“平民艺术”做过界定:“平民艺术,只有不止’知道‘苦闷却是’感着‘苦闷之真的时候才会成就。平民艺术,只有不止有了’平民底认识‘却有了’平民底经验‘的时候才能成就。平民艺术,只有对于平民生活真的要求,觉得不是客观描写只是主观表现,却去客观描写的刹那,才得成就。”渔隐山林乡野的元代文人艺术家们正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将乡野田园的平民趣味引入自我娱适的艺术活动中,展露出元代艺术功能“游戏”观念的乡野情趣。
元代渔隐山林的艺术家们,不仅喜爱梅兰竹菊等象征君子形象的植物,将其写入画中以寄托自己高洁的情志,同时也经常选择田园乡野的日常事物和平民景观作为吟咏描画的对象,或者寄寓自己的情志,或者玩赏平民生活的乐趣,将诗画艺术的审美视线拉向了平民世界。
梅花道人吴镇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浓厚的平民情趣的文人诗画艺术家。吴镇一生“渔钓咏歌书画以为乐”,经常绘画“墨菜”,并在题画诗中寄寓了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其自题《写菜》云:“菜叶阑干长,花开黄金细。直须咬到根,方识淡中味”,他自题《墨菜》云:“崧根脱地翠毛湿,雪花翻匙玉肪泣。芜蒌金谷暗尘土,美人壮士何颜色。山人久刮龟毛毡,囊空不贮揶揄钱。屠门大嚼知流涎,淡中滋味我所便。元修元修今几年,一笑不值东坡前。”玩味着草亭泉石的村居生活,吴镇选取了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事物作为他文士气节和逸士襟怀的象征。
与吴镇志趣相投的元代其他画家也都对吴镇娱戏于“墨菜”的审美趣味颇感兴趣,倪瓒在《题梅花道人墨菜诗卷》中云:“肉食固多鄙,菜烹元自癯。晓畦含露气,夜鼎者去腴。春醪时一进,林笋与之俱。游戏入三昧,披图聊我娱”,同样表达了于平民农舍的日常生活中怡悦性情的志趣;黄公望对于吴镇的“墨菜”也曾题语相赠:“其甲可食,既老而查;其子可膏,未实而葩。色木翠而忽幽,根则槁乎弗芽。是知达人游戏于万物之表,岂形似之徒夸,或者寓兴于此,其有所谓而然耶!”在盛赞吴镇“游戏于万物之表”的豁达与质朴同时,也将自己内心超脱的审美灵境融汇在农家生活的质朴与超脱之中。
“吴兴八俊”之一的钱选,宋亡以后隐居在江苏太湖南滨的吴兴,吟诗作画,读书抚琴,放游山水之间,“诸公皆相附取官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他的《秋瓜图》虽然具有浓厚的装饰之美,却也是一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的艺术作品。厚实的瓜叶与轻飘的秋草交错在画面下方,一只圆滚的西瓜躺在瓜叶与秋草之间,瓜瓣清晰,飘逸的瓜藤上点缀着几颗细嫩的初叶和三株嫩白的花朵,与细韧的草穗一起向上延伸。整个画幅都是水墨染出的或浓或淡的绿色,显得古雅而安静。一首小诗题于画面上方:“金流石烁汗如雨,削入冰盘气似秋。写向小窗醉醒目,东陵闲说故秦侯。”台湾学者高木森曾对此诗进行解读:“此诗首句形容天气炎热,第二句形容瓜的冰凉可口。第三句是说他在半醉半醒的时候从小窗外望,看见了瓜,于是随手画了下来。最后一句道出他的情怀。原来秦朝邵平隐居东陵以种瓜为业,邵平的后人总是念念不忘这段避秦的故事。”可以看出,这幅画就是钱选日常生活的真是记录,其中张扬着钱选乡野闲居之间自娱自适的生活气息。
王蒙成熟时期的画作《谷口春耕图轴》也是一幅描绘山居农耕生活的隐逸闲适类作品。画面层峦叠嶂,山谷深邃。山脚下数顷良田交错在图画的近二分之一处,纵横开阔。田间有人扶犁耕作,与画题相对,一人策杖立于田边,悠然自得。田边清溪绕流,渔翁垂钓。山脚下绿树掩映,环抱着茅屋数间,厅敞堂露。一个男子提壶立于门前。整个画面井然有序,风格清秀,洋溢着简淡宁静的平民生活气息。画幅上有王蒙的楷书题诗:“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有的学者认为这幅画即是王蒙隐居的处所“黄鹤草堂”:“《谷口春耕图》所画的,毋宁说是一种带有史料价值的场面,因为我们可以据此了解到:王蒙在隐居黄鹤山时不但有萧洒的’卧青山、望白云‘,也有’谷口亲耕种秫田‘的躬耕垄亩,读书与耕作交替,使王蒙的隐居生活变得十分充实而富于生机。”一幅山居乡隐图透露出山林隐逸的宁静与恬美,洋溢着乡野生活的闲适情趣。
纵观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平常瓜果蔬菜的描摹、农耕渔樵生活的描写是从元代开始才广泛进入艺术家自我娱适的审美视界的。
远古时期人群围舞、鱼虫花草的彩陶纹样和刻于石壁的骑射围猎图样虽然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的呈现,却有着高于生活的神秘色彩,“与这个时代的图腾信仰,即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商周时期刻于青铜器上的纹样虽然也有动物纹、自然气象纹和车马、宴乐、渔猎、乐舞等图饰而表现着古人的日常生活,却也都是为了祭祀或者记录战功而制作的“礼器”;秦汉时期的画像砖、画像石上虽然也有着对“弋鹅收获”、“夫妻宴饮”等日常生活题材的刻画,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也有“牛耕”、“牧马”、“狩猎”、“宴乐”等生活题材,但它们却都是服务于死者的明器。
魏晋南北朝素有“艺术觉醒”的美誉,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地参与绘画创作,魏晋时期对于花鸟画的创作也颇为繁盛,例如顾恺之《凫雁水鸟图》、史道硕《鹅图》、陆探微《斗鸭图》以及刘杀鬼《斗雀》等等,都是对平民生活的熟见之物的描摹。这些画作大多笔墨精谨,力求通过对事物的细致观察而实现传神写真的艺术追求,但绘画之中所张扬的是门阀贵族讲求脱俗的精神指向。正如李泽厚所言,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并没有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李泽厚进而指出,对自然景象的描摹真正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潮而与生活、情感融为一体,要到宋元以后。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极为发达朝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城市广泛兴起,城市的繁荣造就了一个以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行业的职业为谋生手段的市民阶层,而市民阶层对精神产品的需要又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台湾学者唐文标就曾指出:“中国社会到了北宋时代进入另一个新纪元,出现了一个’平民社会‘。……这样也产生了极有价值的’中国农业文明‘下发展出来的’平民社会‘与’平民文化‘。”但是,宋代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以瓦肆勾栏为场地、以商业性和娱乐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文化的审美主体多为城市平民,文人阶层并未普遍参与其中,其文化活动也较少涉及乡村生活。只有到了元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促成了中国艺术史对平民趣味的普遍张扬。
元代文人之所以能够普遍将平民色彩的日常生活融入自娱自适的艺术活动之中,正是元代文人特殊的历史境遇所造成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夷夏大妨的矛盾纠葛使得他们大多选择渔隐山林以保全志节,沉抑下僚的现实境况击碎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与高贵。因此,他们的渔隐生活大多平实朴素,反映于艺术活动之中,便洋溢出浓厚的平民气息和乡野趣味。
这种平民气息和乡野趣味也进入了元代文人的词曲的创作之中,元代的隐逸文人常作曲词来描绘乡野平民的渔耕生活,抒发自己在渔樵耕作生活的乐趣。正所谓“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渔隐乡野的元代文人除了在自己的诗画作品中呈示着平民生活的情趣之外,随着散曲逐渐成为文人阶层自我娱适的艺术样式,渔隐山林的元代文人也经常将自己对平民生活的情趣付诸散曲创作。
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闲居》唱出了田舍劳作的欢快:“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薛昂夫【正宫·端正好】《高隐》道出了乡间娱乐生活的热闹:“听张暼古唱会词,看村哥打会讹。挺王留讪牙闲磕,李大公信口开河。赵牛表躧会橇,史牛斤嘲会歌,强沙三舞一会曲破。俺这里虽无那玉液金波,瓦盆中浊酒连糟饮,桌儿上生瓜带梗割,直吃得乐乐酡酡”;乔吉【正宫·醉太平】《渔樵闲话》也是一幅渔樵生活的真实写照:“柳穿鱼旋煮,柴换酒新沽。斗牛儿乘兴老渔樵,论闲言怅语。燥头颅束云担雪耽辛苦,坐蒲团攀风咏月穷活路,按葫芦谈天说地醉模糊。入江山画图。”
近人任半塘曾对散曲的审美特性作以概括:“要之,衡其作品大多数量,虽为风云月露,游戏讥嘲,而意境所到,材料所收,因古今上下、文质雅俗,恢恢乎从不知有所限,从不辨孰者为可能,而孰者为不可能。孰者为能容,孰者为不能容也。其涵盖之广,因诗文之所不及。”对于平民生活的描写,对于乡野闲趣的张扬,正体现着散曲广阔的包容性和“文质雅俗”的审美倾向。
(三)聊以自娱:元代艺术娱乐观念的悲情色彩融文化与政治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活动,或者是为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或者是为了标举风雅而赋志咏怀,吟弄风月,无论是可以拓展修齐治平的政治平台,还是能够高标风雅、言志抒情而自娱自适,身为国家命运与社会责任的文化承担者,传统文人从事艺术创作都是一种张扬着人格自尊与文化自信的积极活动。元代文人的艺术活动却并非如此。
特殊的历史情境虽然将元代文人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使其得以潜心艺事、纵情娱适,但这却并非元代文人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沉抑下僚、志不得伸的无奈之举,因此,元代文人或者渔隐山林,在艺术活动中寄托情志、抒泄性灵、自慰自适,或者浪迹市井,在艺术活动中讽刺世事、谑浪调笑、自遣自娱,他们虽然都在客观上赋予了艺术活动任情娱戏、适慰平生的审美功能,其中却蕴藏着“士失其业”的深沉无奈,而表现出无尽的悲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