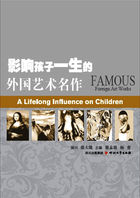即使面对同样的选官机会,汉族文人也明显受到压制。《元史》载:“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创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举凡中央要职以及地方上的各级长官都由蒙古等少数民族担任,汉族人则只能担任副职,南人甚至不能担任省台以上的职位。“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军政事务更是由蒙古人独断,色目人已经参与不多,汉人和南人则绝不参与。《黑鞑事略》徐疏有言:“若行军用师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其亲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也。”有元一代的地方军政长官达鲁花赤除蒙古人外,色目人共有二十人担任,汉人则仅有一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儒士一直是一个颇受优待的阶层,从三代时期重视德行道艺的“学而优则仕”,到汉代的推崇儒术为一尊,再到魏晋时期对于文采辞章的重视,文人与儒士合为一体,向着官僚阶层逐步迈进;从隋唐时期科举取士的正式确立,到宋代文官制度的高度发达,完成了文人、儒士与官僚的三位一体。由读书而仕进,进而显贵的人生路程积淀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自尊与人格自信。蒙古贵族的入主中原却击溃了传统文人的骄傲与尊荣。对于广大汉族文士而言,夷族的统治、科举的废止、任官的歧视不仅仅使他们的生存陷入困境,更令以往的骄傲与尊严受到沉重的打击。“一度为之振奋并满怀希望的广大汉族文人,在逐渐明白事实真相之后立即陷入了迷惘、幻灭和消沉之中”。在元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元代文人不仅身份分裂,还有与之共存的社会地位的下沉与价值尊严的辱没,它们共同构成了元代文人的精神困境。
黑格尔认为,每一时代的艺术都表达着这一时代的精神,都是这一时代的历史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正是元代文人的心灵困顿促成元代艺术的时代特质。面对朝代更迭、异族入主和自身沉沦的三重困境,元代文人不仅需要找到维系生存的动力,更加需求安慰生命的尊严,正因此,艺术活动在元代具有更加浓郁的“适慰平生”的功能。正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既然不能“行义以达其道”,只好“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元代文人或者隐居山林,或者投身市井,坚守儒家“行藏大节”与“夷夏大妨”的传统观念而慷慨悲歌,控诉世道的乱离与社会的不公,于艺术活动之中寄寓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坚贞的君子情结与高迈的文人雅志,从而确认自我,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适慰,而其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也使得元人的艺术活动呈现出一定的悲情色彩。
小结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被处于社会发展较低阶段的草原游牧民族所征服,蒙古贵族的草原文化和中原汉族的儒家文化不仅有着社会形态上的差别,也有着民族与地域的差别,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伴随着蒙古贵族的铁骑席卷南下,冲击着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正统儒家文化,也给中原腹地输入了新的因子。
恩格斯论及欧洲的民族迁移时指出:“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入主中原之前的蒙古帝国还是一个以草原游牧生活为主的奴隶社会,其草原游牧文化要远远落后于封建社会已发展至顶峰的中原农耕文化。游牧民族相对落后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中原汉族的“礼崩乐坏”,也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相对于中原等级森严的封建壁垒而言,草原游牧民族所具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特别是他们对于尊卑等级和伦理纲常的观念,尚处于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之中,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冲击了儒家正统文化的“三纲五常”,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的观念更新。正如元初戴表元所言,“古之通儒硕人,凡以著述表见于世者,莫不皆有统绪。若曾孟周卲程张之于道,屈贾司马班扬韩柳欧阳苏之于文。当其一时,及门承接之士,固已亲而得之;而遗风余韵,传之后来,犹可以隐隐不灭。近世以来,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复续。”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在元代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被压制的异端思想得以破土而出,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普遍人性”与“主体精神”的觉醒进程。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蒙古部落兴起于蛮荒的漠北草原,尚且处在奴隶社会,所以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和社会规范,更容易对异质文化袒露胸怀,表示出包容的态度,其崇尚武功的统治生活、“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追求功利的商业观念、多教并存的宗教思想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了元代文化多元发展的开放格局。诚如刘祯所言,“蒙古民族的勇武之力,不仅在中原及广大之地摧毁了宋王朝的物质存在,而且也摧垮了汉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而改变了汉民族旧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在阵痛中急转弯,使得元朝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审美风尚都从传统的因循守旧中焕然有变,迥异于前朝,迥异于传统。”
蒙古贵族对中原汉地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其并不先进的意识形态强烈地震撼着积淀深厚的中原正统文化,传统的思维、习俗和礼乐规范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为元代社会的“思想解放”创造了客观条件。“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豪不相似”。随着蒙汉文化的不断交流,新的社会风尚、审美倾向与艺术观念在草原文化的冲击中获得了新变。
蒙元贵族统治中原,也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心境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元初文人不同于以往的易代文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朝代更迭的藏行之难,更要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夷夏之辨。生逢宋元易代之际,蒙古贵族统一了大江南北,少数民族第一次正式掌握了中国政权,“夷夏大妨”的传统观念增加了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与不安。
而且,有元一代的整个汉族文人群体还要面对异族统治之下的民族歧视。元朝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原王朝,而是“大蒙古国”的一部分,蒙元之平宋也并非单纯的中原王朝的统一战争,而是兼具蒙古征服战争的性质。蒙古贵族掌握政权,在其实施统治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民族势力的平衡,不可避免地要对汉人进行压制,元朝统治者的尚武精神更使汉族文人蒙受着前所未有的屈辱。
生存境遇的突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心境状态的变化,使得元代文人对于艺术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艺术活动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成为自由洒脱地抒写情志、疏泄积郁,进而自由娱适、聊以获得人生慰藉的审美活动,凝定了元代抒写性情的艺术本质观念、翰墨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和聊以自娱的艺术功能观念。同时,在元代文人沉抑下僚而托身民间的过程中,他们也将自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观念拓展到民间,促进了元代雅俗文艺的融合。可以说,正是元代特殊的历史现实与文人心态共同推动了中国艺术与艺术观念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