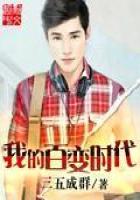陈宗海把自己“宅”起来了。
他忘不了在东北、在内蒙,坐在环保科长或总务科长家的炕头上,用吃饭的黑磁碗把科长们喝得酩酊大醉,也把科长的老婆喝得笑个没完没了,而后一份几万或几十万的环保治理合同便签成了。他也忘不了在广东、在四川,一连等了五天五夜,等来了财务科长,会计又不见了,找到了会计,财务科长又跑了,后来他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与他签合同的甲方代表,将他拉到二楼,可是在二楼等待他的是两个保安人员,他与人家大打出手。最后他们终于惹不起这个玩儿了命的北方佬,只好把欠款给了他。
当然,他也很可怜,西服口袋里装了花生米,一个口袋装半斤,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边走一面成把地往觜里塞。因为沒时间吃中午饭,他要尽量多跑几个地方。到了地方或者在沿途上,他便撅起屁股觜对着人家的自来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一气。花生米吃的时候干,吃完了,渴。
更让她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是,登上那高高的楼顶或攀上了高高的烟囱,站在各式各样的风机托架上测试噪声或粉尘的发源点,得出数据并绘制草图,大到源体的形状、尺寸,小到每一个法兰盘的孔眼,他都标得仔仔细细。当合同与草图一并拿回厂里的时候,科室的人围着他,车间的人向他投来赞佩的目光。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不再回来。
他当然也有过甜蜜的时光,那便是与陆文婷的相识、相恋、到结婚……
他也有过欣慰、窃喜又充满希望的时光,那便是与老同学郝琳的重逢、相恋、到结婚……
这也成为了过去,不再回来。
在奔波的旅途上,他不但要在业务上过关斩将,也同样要接受来自其它方面的考验与诱惑。有人问他:“老板,一个人,不孤独吗?”“老板,要不要褥子?”“先生,想不想其它服务?”他都摇头了,否掉了。然而,在南方那个钢厂附近的一个宾舘里,他险些折戬沉沙,为后来的一场麻烦制造了序幕。
陈宗海知道,自己是个矛盾体。比一般人都矛盾。
都过去了,过去了,一切都成为了浮光掠影,留给他的只是回忆。
今后争取不再矛盾,起码少些矛盾。
从八月与郝琳离婚,一直到冬天,陈宗海曾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在一个物业公司做保安组组长,月薪二千五,但他只去了半个月便不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怎么想怎么觉得不是滋味儿,究竞怎样有条有理、明明白白的不是滋味儿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另一份工作是iT业,做销售代表,但老板安排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去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陈宗海没有去,因父母年势已高,万一有个好歹,作为儿子,迢迢万里,如果连看也来不及看一眼,那将成为终生遗憾!为此,多少孝男孝女曾流下悔恨、愧疚的眼泪。
就这么“宅”着,到吃饭的时候,去父母家,或者自己随便买一点,一个人懒得做饭。
一天,刘铁军忽然来了电话,问:“你有多少钱?”
陈宗海说:“干嘛?你要用?”
刘铁军说:“我不用,是你自己用。”
陈宗海不明白。刘铁军解释说:“北三环路边上有个农贸市场知道吧?”
陈宗海说“知道。”
“人家是股份制。如果你入股二十万的就能当董事长,入股十五万就可以当执行经理。可是我跟你说,现在的那个女经理能力不行,遇事总好纠结,大家对她也不大满意。”
陈宗海笑问:“你跟我说这干嘛?”
刘铁军说:“这不是替你找工作嘛,怎那么笨?你拿出十五万,入股,就可以接替那个女的,做农贸市场的经理了!”
陈宗海问:“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这情况?”
刘铁军说:“废话,我媳妇也在那儿入了股,听她说的。”
陈宗海说:“那怎不呌你媳妇去当经理?入十五万。”
刘铁军说:“废话,我媳妇上班,辞职呵。”
陈宗海正经了:“可是我沒钱呵!”
“你钱呢?”
陈宗海给刘铁军算:“前几年买房,花了个光。结婚以后一共三口人,每月还要交婷婷的抚养费。再说,我多长时间没工作了?”
刘铁军听了,深觉惋惜。啧觜说:“那就不行了。”
过了几天,陈宗海没什么事,可能在家“宅”得也腻了,便出来遛达遛达。
去哪儿呢?忽然想起那个农贸市场,便坐了几站车,来到了北三环附近。
这个农贸市场规模不小,交通也方便,有三趟公共汽车从此路过。
陈宗海遛达进去,背着手,俨然一个有闲阶级,俨然一个文人雅士。
他看着那些卖菜的,卖肉的,看着那些卖水果卖零食的,也看着那些来来往往骑着三轮、推着自行车或开着蹦子车趸货的……旁边的杂货店整年整月整日在放着同一个录音:“本店因经营不善,急需回笼资金,所有商品一元一件!一元一件!一元一件!”
陈宗海想顺便买点菜,带回去;总在父母那里吃,菜总要买一些的。
“茄子怎卖?”陈宗海问。
“四毛五!”摊主回答,一面给别人秤着菜。
“黄瓜呢?”
“八毛!”
陈宗海又问旁边的一个摊主:“茄子怎卖?”
“四毛五。”
“黄瓜呢?”
“八毛。”
一样的价。陈宗海想到别处再转转。
“陈大哥!”
忽然有人呌了他一声,回头看,见是他问的那个第二个摊主。
“您是陈大哥吧?是不是陈大哥?”摊主是个女的,手里攥着刚收的钱。
陈宗海仔细打量那人。她穿着羽绒服,系了一个很大的围裙,头上包着头巾,个子矮而粗……似乎认出来了,但陈宗海呌不上她的名字。
“我是司炳兰,您不认识我了?”那女的说。
司炳兰?似乎想起来了。
陈宗海走过去,司炳兰也放下手里的活儿。
“哦,司炳兰。”陈宗海叫道。同时他也感到奇怪,便问道,“你怎么到这儿卖菜来了?”
司炳兰说:“陈大哥,我秋天就来了。在这儿卖了三个月的菜了。”
“那么你原来那份工作呢?保姆?不干了?”陈宗海又问。
有人买莱,司炳兰一面忙自己的生意一面说:“老太太去世了,这是我另找的工作。”
“去世了?那老太太?”
司炳兰说:“头年拆迁,老太太不愿意走,可是不走又不行。这么一折腾,老太太沒扛过去,就走了。”
“这么说西门三里到底拆迁了?”陈宗海说,“拆得好,早就该拆。”同时焕起了许多回忆,那些破旧而低矮的房屋,那些人,还有那个呌飞宇的大酒店。
司炳兰为两个买主称了菜,也收了钱。然后站定了和陈宗海说:“刚才,险些不敢认您。”
陈宗海看她手下很娴熟,问:“怎么样?一天能卖多少钱?”
司炳兰说:“好的时候能卖三、四百,不好的时候也能卖二、三百。”
“纯赚多少呢?”
“平均每天也就七、八十块钱吧。”
“也行了。”陈宗海说,“不过你还要刨去房租,刨去摊位费是不是?”
司炳兰说:“可不是?实际剩手里的也就五、六十块,和伺候老太太时候也差不多。您想,再刨去我每天吃呢?”
“行,好好干。”陈宗海鼓励说。要走。
“陈大哥,您是不是买菜?不用买,就从我这儿拿吧!”
陈宗海想,从你这儿拿你肯定不要钱,打架似的,何必呢?于是他摆摆手说:“我不买,只是瞎转转。”
“陈大哥,郝大姐和您……”司炳兰说到这儿不好往下说了,“您知道,老太太狠骂了郝大姐一顿呢。”
陈宗海笑了笑。还是想走。
“您还在原来那地方住吗?”司炳兰却紧接着问。
“对对,还是原来那地方。”
“您和郝大姐结婚的时候我和老太太都去了。您记不记得?出租车费还是您给的呢!”
哪壶不开提哪壶,陈宗海“哦哦”两声,走了。
不过,这个司炳兰,变得比以前开通,也会说了。一晃三年,大约经了许多世面的缘故。
陈宗海在别处买了菜,提回到父母家。在父母家吃了中午饭,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整个一个下午,陈宗海游游默默、无所事事,一会儿动动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一会儿拿出自己那把破吉它胡乱地拨拉。
太阳斜射在西面楼顶的时候,他忽然听楼下有人呌:“陈大哥!陈大哥!”仔细听,是司炳兰的声音。
他很奇怪,这个应该近三十岁的农村老姑娘喊他做什么?有什么事?是不是有事又求他?抑或她找别人,迷了路?
他隔楼窗往下看,果然是司炳兰,正仰头四处踅摸。
陈宗海迟疑了一下,向下面呌道:“上来吧。”
“几门,几号,我忘了!”司炳兰仍然仰着头,看见了他。
陈宗海只好到楼下去接。
司炳兰挎着一个包。手里还提了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的是菜,有黄瓜、柿子椒和西红柿,都是当下较贵重的菜。
进了屋,司炳兰直接将菜放进厨房。她是做保姆的,对家庭过日子这一套自然很熟悉。
陈宗海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干嘛还带菜来?”
司炳兰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想看看您。”
陈宗海说:“上午不是看到了?还说了话。”
司炳兰说:“那不算看,只算碰到了。”她的确练得很会说话。
陈宗海有些明白,她大约是想感谢他。没有他的帮忙,她也许找不到那份保姆的工作,也说不定在这个城市还落不下脚。
陈宗海笑着说:“司炳兰,你比从前会说话了,也懂事多了,是不是有点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思?”
司炳兰说:“就是这意思。我早就想来,可不知您搬家了没有,上午问了您,才敢来了。”
陈宗海问:“吃饭了没有?”
司炳兰说:“没有。怕找不着,收完摊就来了。”她倒是实话实说。
陈宗海咧了下觜:“我这儿也没饭,平时都回我父母家吃。”陈宗海也实话实说。
“您吃了没有呢?”
“我也没呢。你要不来,我正要回去吃。”
“那我走了,您去吃吧。”真真的实诚人。
陈宗海又颇觉过意不去,说:“那好,你坐这儿休息看电视,我去做,马上就好。”
实诚人,倒也不讲客气。司炳兰说:“您坐那儿休息,我来做。”说着,进厨房去了。
陈宗海已很长时间不做饭,锅、铲,都生了锈,碗、盆也有了一股尘土味儿,司炳兰都仔细擦了、刷了。陈宗海愈加不忍,要从中帮忙,但司炳兰不用他,在郝琳曾经围过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推着陈宗海,一直将他推进卧室。陈宗海起身,只把油盐酱醋之类预备到司炳兰身边。
陈宗海想,倒也不错……听见洗菜的声音,切菜的声音,然后炝锅儿,从厨房飘出一股久违了的葱花味儿。
他忽然想起米饭,跑进厨房,但司炳兰已在另一个灶眼把米饭蒸上了。
不愧当过保姆。
不破费,只两个菜,一个汤。米饭有些烂,菜也有些烂。陈宗海说:“烂就烂吃,还好消化。”
司炳兰说:“对不起,陈大哥,我给老太太做饭做惯了!她只吃烂的。”
陈宗海问:“你自己也吃这么烂?”
司炳兰说:“我吃生的,放了油盐拌着吃。”
“省。”陈宗海说。
吃着饭,司炳兰忽然问:“陈大哥,您找到工作了吗?”
陈宗海一楞:“你怎么知道我找工作?”
“当初郝大姐说过的。”
陈宗海叹口气:“你们外地人难找工作,我们本地人也同样难找工作。”这话,陈宗海是有潜台词的,以预防司炳兰在工作上又有求于他。
但司炳兰说:“不一样。我们不管工作高低贵贱,只要能挣到钱就行。”
陈宗海说:“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司炳兰想了一下:“陈大哥,我看您不如也去卖菜。看我,早晨四点蹬三轮车去上货,回来六点多,一边卖一边就把饭吃了。到了中午,卖不完也剩不下多少,下午再一找补,就完事了。”看来她对自己卖菜的行业还挺喜欢,也很乐观。陈宗海松了口气。
司炳兰又说:“陈大哥您也可以包几个摊位,当头儿,挣钱比较多。”
陈宗海说:“那得需要一笔资金。可是我没钱。”
司炳兰撂下筷子:“您需要多少?我这儿有。”
陈宗海笑:“你有多少钱?”
司炳兰说:“三万多呢!都是我这几年攒的。”
陈宗海好心地说:“你留着吧。想想,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可不是?给她介绍做保姆的时候是二十五。
说到这儿,司炳兰脸红了,不再说话。
吃完了饭,陈宗海一直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司炳兰说她坐三站地,倒一次车,然后再坐两站,就到“家”了。陈宗海逗她说:“你的家什么样儿?几居室?”司炳兰也笑着:“六平米一个小屋。”
陈宗海一个人回来,到厨房看看,都已收拾得干净利落。他回到自己卧室,依旧冷冷清清……
顺手抄起吉它: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是游击队之鹰。”
这是他十几岁时唱过的,歌词早已记不清,中间便以“当当当”代之。
唱过了,他又禁不住地笑……那样一个人,还很懂得感恩。其实想想,有什么恩可感?他当初也不过碰到了一个“保姆”的机会,才突然想起来;而那时距别人托他,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
陈宗海原以为就此完结,也希望就此完结,不要再感什么恩了,未料到,隔了几天,司炳兰又来了。
这次来,陈宗海没在家,出外办事,当他很晚才回来的时候,却看见司炳兰坐在他的房间门口。同样挎着包,身边同样有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不过这次装的是土豆。
陈宗海只好又请她进去。
“你今天又拿了土豆,但是我一定要给你钱。”陈宗海说,“司炳兰,你忙,以后还是专心一意地做你的生意。”
陈宗海是真心实意的。他不希望这样,也真不希望司炳兰耽误了她的生意。
但司炳兰把土豆呼噜噜倒在地上,边倒边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陈宗海说:“多大的好消息你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了嘛。”
司炳兰说:“我沒电话。”
陈宗海说:“我指的是手机。”
司炳兰说:“我没有手机。”
陈宗海奇怪:“你怎会连手机也没有?”
司炳兰说:“我要它没用,往家里打电话就用公用电话打,一年也打不了几次,不是白花那钱?”
“省。”陈宗海又说。然后问,“吃饭了没有?”
司炳兰说:“这回知道了准地,吃了饭才来。可是在你门口等了一个多钟头。”
陈宗海想笑,算今天才来了两次,司炳兰便不再称“您”,而换成了“你”。
司炳兰喝水的时候,陈宗海掏出钱来:“也不管够不够,给你十块钱。”
司炳兰台眼看着他,声音很大地说:“陈大哥,这是六斤,两块五一斤哩!”
陈宗海很诧异:“这么贵!一个土豆,两块五一斤?”说着又掏出十块钱。
司炳兰急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明白什么?”
“我们老家土豆多得是,家家有,又大又光,顶多才两、三毛钱一斤!”
陈宗海还是不明白。
司炳兰坐下来,又喝了一杯水,详细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土豆特别缺货。今天早晨来了一车,两块五一斤,少一分不卖。结果呢,还是一会儿就抢光了,我好不容易才抢了这六斤……陈大哥,你不是没有工作吗?我的意思是可以去我们老家趸土豆,到这儿来卖,你算一算,一斤就差两块多,如果拉一车回来,能赚多少钱?”
陈宗海明白了,她是想让他去搞长途贩运。
陈宗海说:“你的好意我领了。第一,你陈大哥不是那块料,第二,既然能挣那么多钱,你们老家的人为什么不把土豆拉来卖呢?”
司炳兰耐心解释:“我们老家的人谁有汽车?马车倒是有,可五百里地,马车怎么走呢?中间得歇,还要住店。如果是冬天,土豆就冻了,要是夏天,土豆就烂了。”
陈宗海一想,也有道理。司炳兰说得清清楚楚。
司炳兰又说:“陈大哥,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一趟成了,再去一趟,然后再去一趟、再去一趟,不就能挣上钱了?雇车也方便,我们市场门口就有,什么车都有。”
陈宗海有点动心。
他问:“路怎么样?好不好走?”
司炳兰承认说:“路是不大好走。可是你有汽车,当天去,第二天就能回来。”又问陈宗海,“一车能装多少斤?”
陈宗海说:“那要看什么车,一般的,也得四、五千斤吧。”
司炳兰在给陈宗海鼓劲:“陈大哥你放心,我肯定跟你一同去。你钱不够,我给你添,赔了算我的,赚了钱算你的,成不成?”
陈宗海着实感动。但他笑着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司炳兰继续鼓劲:“不是说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吗?陈大哥,要再耽搁,土豆价就下来了。”
陈宗海说:“事是好事,不过你还要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司炳兰露出失望的神色。她站起来,要走。也不要桌子上的钱。
“钱!”陈宗海拿起那二十块钱追过去。
司炳兰又折回来:“陈大哥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明天我去买手机。”
陈宗海回屋写了一个条子,连同那钱一起塞到司炳兰的口袋里。但司炳兰又从口袋把钱揑出来,那钱飘然而下。
司炳兰走了。陈宗海还真的考虑了一个晚上。
要不然怎么办,坐吃山空?就这么呆下去,什么时候算到头呢?
陈宗海呵,该放下架子就得放,不要总想着你的那个大业务员的名声和你曾经当过厂长。告诉你,比你高级的人多了去了,海了去了,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不是照样去给人家打零工?搬砖、挖土方,甚至掏化粪池,什么全干,只要挣钱就行。实际上,你与司炳兰没多少区别。
是非成败,就拼它这一回。拼好了,索性就长期搞贩运,又有何不可?
第二天下午,司炳兰打来了电话,果然是用手机打的。
“陈大哥,土豆又涨价了,涨到两块六毛五一斤!”
“其它菜涨沒涨?”
“其它菜也涨了,听说山东下了大雪,菜运不过来!”
“你们老家还有什么菜?”
“我们老家光有土豆,其它菜不长!”
“为什么不长?”
“太冷,也没有水!”
话没说完,座机又响起来。
陈宗海拿起电话:“喂,您哪位?”
“陈宗海,你能不能想办法搞点钱?我告诉你,那个女经理快坚持不住了,过几天她要提出辞职。”
陈宗海说:“铁军,我现在要冒一次险。”
“冒什么险?”
“搞长途贩运。”
“运什么?”
“土豆。”
刘铁军呸他,然后说了一句这个城市流行的话:“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