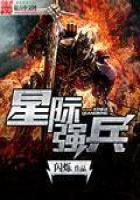陈宗海回到家里便打电话。按说,电话应该打给陆文婷,因为当初是陆文婷求他。
但陈宗海沒有打给陆文婷,而是把电话打到了陆文婷的父母家。既然那个农村来的姑娘是陆文婷父亲老家的人,还是直接与她父亲联系的好。
沒想到,电话是婷婷接的。婷婷经常在姥姥家住着。
陈宗海说:“婷婷,又来姥姥家了?”
婷婷说:“我妈也在呢。”
哦?她也在。陈宗海问:“那么牙医呢?他也在?”婷婷一直把她的这个所谓继父呌“牙医”。
“他不在。”婷婷说,“让他一个人在家呆着呗。”
陈宗海让婷婷把姥爷呌来接电话。
婷婷的姥爷来了。陈宗海说:“叔,老家来的那人现在怎样了?有沒有工作?”
婷婷姥爷声音又急又大,说:“宗海呵,你要有,赶紧给找一个。人家街道没完没了地催,催了半年了,我厚着脸皮总去求人家。唉,沒想到一个街道清洁工都有人抢。”
陈宗海说:“有一份保姆的工作。”
老人家说:“保姆?好呵。是伺候小孩儿还是伺候老人?”
陈宗海说:“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老人家说:“行,沒问题。什么时候去?”
陈宗海说:“最好明天就去,人家等着哪。”
于是,两人约好了时间、地点。陈宗海又说,明天只是看看,成与不成要由人家说了算。
第二天早晨,陈宗海把车开到丁字路口等。一面等,一面在路边的早点摊上吃了早点。
不一会儿,婷婷姥爷领着一个女子来了。那女子挎了大包小包,包里是行李,好像一去就不准备回来。
然而好一个女子,果然粗胳膊粗腿,腰也粗,像个壮汉;壮,又粗,个子便显得矮,估计也就一米五多点。
“这叫陈大哥。”婷婷姥爷指了指陈宗海。
女子很听话,便呌一声“陈大哥”,还鞠了一个躬。
陈宗海让把行李放到车上。
“你陈大哥和我的关系特别好。”老人家夸大其辞,我和你已沒有了翁婿关系,能好到哪里?
老人家又说:“今后你处处事事要听你陈大哥的,咱们家的事就和你陈大哥自己的事一样。”
那女子毕恭毕敬,又给陈宗海鞠了一个躬。
然后,老人家挥了挥手:“上车吧。宗海,我就不去了,诸事都拜托你。”
陈宗海也觉得无所谓,去不去都成。反正主顾说了算。
车开了。陈宗海问:“吃饭了没有?”
那女子回答:“吃了。”
陈宗海又说:“别发怵。到了那儿觜要勤快点儿,见了人该呌什么呌什么。人家问,你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
女子一连点了好几次头。
车到市中心区又拐了一个弯,进入一条胡同。那里也有一片平房,郝琳便住在这里。
陈宗海事前给郝琳打了电话。郝琳早已在胡同口等着了。
那女子见来了人,便自动从前面下来,坐到后面去。
郝琳反复打量了她,问道:“你呌什么名字?”
“司炳兰。”女子带笑回答。
“什么?”郝琳沒听清楚。
“司炳兰。”女子重复道,“司就是公司的司,炳是火字旁加一个甲乙丙丁的丙,兰是兰花的兰。”
她好像在背,很熟,很习惯。大约每到一个岗位她都要这样说一遍。
“你今年多大了?”郝琳又问,像问一个孩子。
“二十五。”
“结婚了吗?”
“没。”那女子,不,应该说是姑娘,不管长得好与不好也是姑娘。她抿嘴笑了。
“为什么这么大还不结婚?农村不是特别早吗?”郝琳也真是的,问个沒完沒了。
这下,那姑娘满脸通红。
“你以前做过保姆没有?”郝琳还问。不过这问得倒有必要。
“我做过小时工、清洁工。”姑娘老老实实回答。
“其实也差不多,哈。”郝琳朝陈宗海笑笑说。
陈宗海也插进来说:“据说她在家只种过地,赶过马车,头年才出来打工。对吧?司炳兰。”
司炳兰点头。
郝琳不再问了,车静静地开。
进了“西门三里”,正好与山西藉保姆走了个碰头儿。她背着个小包袱,三步一回头,不断与后面的老太太挥手致意。
她真的按时按点走了,郝琳的姑姑站在街门口还在抹眼泪。
郝琳让陈宗海停一下。她下来拉着保姆的手,说了一会儿话。
接着,几乎三个人同时搀扶着郝琳姑姑。把她搀进屋里,坐到床上。然后,陈宗海和郝琳先后向她介绍了司炳兰。
老太太转悲为喜,一见司炳兰便爱上了。说:“看这样,就是个实诚人。”
司炳兰自然管郝琳呌大姐。但管老太太呌什么呢?若随陈宗海呌“大妈”,不合适,司炳兰太小了。若叫“奶奶”,也不合适,司炳兰又太大了。陈宗海说干脆就呌“老太太”吧!大家也都同意。
接下来,陈宗海委婉地问郝琳:“大妈每月的保姆费从哪儿出?”
郝琳说:“她每月有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平时我们再给一点儿,也就行了。”
老太太朝司炳兰说:“我不偏不向,也给你七百。”
郝琳补充说:“管吃管住。”
很快,就沒什么问题了。双方都满意。
陈宗海问了一下司炳兰:“你还有什么事沒有?”
司炳兰摇头。说:“您回去和我大爷说一声。”她说大爷,便指陆文婷的父亲。
陈宗海说:“行了,我和他说,这事妥了。”
司炳兰一脸的感激之情:“陈大哥,谢谢您。”
陈宗海说:“不用谢,你好好干比什么都强。”
陈宗海问郝琳:“你还有沒有问题?”
郝琳说:“这事定了,我也踏实了。”又对老太太说,“您有事就开口分咐,别不好意思。”
老太太笑眯眯地问:“你做饭行不行呵?”
司炳兰说:“我给好多家做过饭。”
老太太说:“我沒牙,吃不了硬的。”
司炳兰说:“我给您做软的。不过就是费火。”
陈宗海和郝琳都笑。
又小坐了一会儿,陈宗海走出房间。
司炳兰跟了出去。从车里拿出了行李和包包。
郝琳又嘱咐了几句,也走出房间。
陈宗海等着她。郝琳坐进了陈宗海的车。
陈宗海问:“去哪儿?”
郝琳说:“回家。”
陈宗海说:“又快十一点了。饿不饿?还请你吃饭。”
郝琳说:“还是回家吧,我还有好多活儿。”
陈宗海说:“什么活儿?我帮你干。”
郝琳说:“真的?洗衣服;我的,我女儿的和我妈的,干不干?”
陈宗海说:“那不干。力气活儿你找我。”
车开了,就这么开,谁也不再说话。
马路是那么短,距离是那么近,不一会儿就到了市中心。陈宗海有时看一眼郝琳,郝琳有时也看一眼陈宗海,两人目光相遇,都笑一下,但仍然谁也不说话。
到了胡同口,陈宗海停下车,叹气:“唉,老同学,不知哪天还能见面呵!”
郝琳下了车,说:“我还能常常到我姑姑那儿去。你呢?酒店的活儿干完了,也不会再去了。”
陈宗海看着郝琳,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半个月以后,陈宗海给郝琳打了电话,向郝琳倾诉心声。
他是这么想的。郝琳,老同学,知根知底。她和他一样,父母全是工人,只不过郝琳父亲沒了,和母亲在一起。
她离婚二年,他离婚五年。她有一个女儿呌秀秀,他有一个女儿呌婷婷,可谓门当户对。只是婷婷跟着她妈。
郝琳工资收入不高,但她身上沒有那种小家子气,更没有那种世俗气,反而落落大方,朴实而厚道。郝琳不爱哭,爱笑,一笑嘎嘎的,让人听着痛快。不错,郝琳也遭受了婚姻的不幸,很痛苦,但她痛苦而不悲观,更不凄凄哀哀地沒完没了。在这半年多来与郝琳若干次的接触中,陈宗海也体察到了,这种性格似乎也是郝琳学生时代的一种性格的持续。
设若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不用担心有人处处事事挑你的毛病,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更不用担心有人对你发号施令,以你的无条件服从视为对方的满足。你可以和她坦诚相处,无所不谈,不用动心眼,不用有所提防。你更不必经常、甚至值不值就看到她哭成个泪人。多么好,多么心情舒畅、令人憧憬的不一样的家庭生活……
另外,郝琳长得难看吗?一点也不难看。
人各有其风格。有的纤细悄蹑,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聪颖而漂亮,但心眼多、事多,连眼睫毛也会说话。有的呢,看去一副憨态,还干些粗活儿累活儿,但仔细看,再看长了,却潜藏着一种内秀的美。这种美经得起看,越看越耐看。这便是郝琳了。
但陈宗海那电话打得十分别脚,心声也倾得坷坷绊绊:
“郝琳,你看……你有一个女儿,我也有一个女儿,都十一岁,都快上六年级了。可是我的女儿不在我身边,秀秀……是不是就和我的女儿一样?”
驴唇不对马嘴!怎么上来就说这个?于是陈宗海又赶快改口说:“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吧,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又见面了。我觉得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好,真的好……”
对方却不说话。什么态度,什么表情,完全不知道。
陈宗海宁起头皮,爱怎样怎样,反正得表达清楚,然后听天由命:
“你看,我离婚了,你也离婚了。我离婚五年,你离婚二年,我认为咱们俩应该……”
说到这儿,只听电话里“咿”地一声,那是郝琳哭的声音……说不爱哭,还是哭。
陈宗海赶快说:“你不用哭,就如同我什么也没说。”
郝琳还在“咿咿”地哭。
陈宗海慌了手脚,又说:“再说,我根本沒说什么出格的!”
“陈宗海,就听你的,全听你的吧……”这是郝琳的话。但仍是哭着说的。
陈宗海却一时搞不清楚:“听我的什么?”
“和你在一起!”郝琳喊了,喊得声音很大,带着哭音。
然后电话就撂了。
陈宗海突然省过神来,开始在屋里手舞足蹈。郝琳哪里是哭?分明是高兴。也是哭,却是激动得哭。
仔细想想,这结果实际与陈宗海的预料差不多。只是沒想到这么简单、痛快。在与郝琳的接触中,陈宗海也看出来郝琳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
那个晚上,陈宗海破例地在家喝了酒,和父亲两个人,喝了白酒又喝啤酒。
父亲问:“小子,什么好事?”
陈宗海说:“大好事,您马上又要有儿媳妇了!”
父亲问:“干什么的?什么出身?”
“会计……”
“又是会计!”
陈宗海说:“可绝对是工人出身,三代工人。”
母亲说:“可别要那太好看的。”
陈宗海说:“中常人,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不好看。”
父亲说:“小子,信你的,抽空带回来让老子看看。”
陈宗海说:“放心吧,这回铁定了。我今年三十九,还有几个三十九?”
接着,陈宗海和郝琳以恋人身份再次见面。以前见面那么自然,那么平常,现在见面两人都红着脸。
但有什么可说的呢?就那样吧!彼此全了解,没有不了解的地方,只差捅被窗户纸的那一句话。花前月下的缠绵与电影院里的厮磨均已不属他们这个年龄。
然后,陈宗海去了郝琳家,见了郝琳母亲,还有郝琳的女儿秀秀。郝琳母亲对陈宗海很满意。秀秀比婷婷略高一些,但却比婷婷胆小。她看见陈宗海像看见老师,毕恭毕敬,多一句话不敢说。
也就在这一次,陈宗海才吐露了他的厂长身份。
郝琳玩笑地说:“早知道你是厂长我早追你呀!”
陈宗海说:“所以不告诉你,考验考验你这人。”
郝琳说:“得了吧你,早知道你当了厂长我躲你远远的!”
续而是房子问题。这是个摆在当前、最实际、也是最大的问题。
郝琳离婚后一直和母亲住在一块儿。母亲家是平房,而且只有两间。郝琳没结婚以前在家里就这么凑合着,后来离婚了,搬回来,还这么凑合着。
郝琳在物业公司上班,因此在关于房子的信息方面比陈宗海要灵通得多。以前,灵通也没有用,因为没有钱,现在有了陈宗海,没用也得有用,没钱也得有钱。过了不久,郝琳便打听到了,距家不远的地方,一片新开的楼盘正在热卖。而且据说价钱比较公道。
陈宗海和郝琳两个人一同去了三次,他们看中了一个一居室。为什么是一居?因为两个人加起来的钱还不足七十万,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想那两居、三居的事。而且即便这七十万也是陈宗海一个人拿的,他把原来和陆文婷一起卖那两室一厅的钱取了出来,再加上这五年来自已的积蓄。郝琳手里有六、七万,陈宗海让她好好留着,专门给秀秀上学用。
他们不去公园玩,不去看电影,抓紧那一居室的装修和婚前的各项准备是正经。
百忙中,郝琳也来过陈宗海家。陈宗海父母无话可说,与儿子所预前告知的完全一样。即,新的儿媳是个没那么多心眼的老实厚道人。
现在只有婷婷还没有见过郝琳。
婷婷很长时间沒有来爷爷奶奶家了。自陈宗海当了厂长,再没有那么多时问带婷婷出去玩。婷婷即使来了,也时常见不到陈宗海,于是只好和爷爷奶奶待一会儿,说一会儿话,然后告别。
放暑假的时候陈宗海给婷婷打过一次电话,让她来家,说想你了,爷爷奶奶也想你。但婷婷说:“不行,我得陪我妈。”
陈宗海问:“你妈用你陪吗?牙医干什么去了?”
婷婷不说话。
陈宗海说:“这孩子,怎不说话?”
婷婷说:“哎呀,等以后跟你们说。”便关了电话。
这一次,父亲要去接婷婷,说“我就不信接不来!”父亲以为是陆文婷或者婷婷的姥姥、姥爷不让婷婷来。陈宗海没让父亲去,怕去了又和人家吵。陈宗海自己去了。
此时郝琳也正好在陈宗海父母家。
婷婷接来了。爷爷奶奶搂着孙女不松手,仔细看婷婷,一会儿说她瘦了,一会又说她胖了。婷婷呢,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不知她在想什么。
陈宗海回到自已屋里。郝琳问:“接来了?”
陈宗海说:“接来了。”
郝琳说:“我怎么有点紧张?”
陈宗海说:“你紧张什么?她一个孩子。”
郝琳说:“谁知道……从照片上看,她和秀秀可不一样。”
陈宗海说:“从长相上看有点像她妈。”
婷婷进到了陈宗海屋里,一眼看见了郝琳。她的脸上现出了大人般的一种外交场合的笑,表面,而且夸张。
陈宗海让叫“阿姨”,她呌了;陈宗海又介绍“郝阿姨”,但只说了几句,婷婷一转身,出去了。
“甭管她。”陈宗海说,“反正一个孩子。”
郝琳说:“我怎么看她有点大大咧咧?和我一样。”
陈宗海说:“她可和你不一样。这孩子篶有准儿,说大了,叫有心计。”
郝琳说:“有心计好。她功课行不行?”
陈宗海说:“功课让人放心,在班里排前三名。”说完,陈宗海又神秘地一笑,“我说她有心计,你猜她一个人偷偷攒了多少钱?”
“多少钱?”
“有一天我翻她书包,想看看她的作业本。”陈宗海说,“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她的一张存折,上面整整存了五千块!”
此时,婷婷回来了,手里攥着一个小钱包,那钱包很新,好像刚刚楼下买的。婷婷给郝琳鞠了一躬,然后把刚买来的小钱包双手呈上去,说:“阿姨,这是我的见面礼。”
说完,她站了一会儿,又走了。
那钱包最多值五元钱。但婷婷走了以后,可让郝琳慌了手脚,她空身来的,只骑了自行车,包儿没带,钱自然也没带。但郝琳还是把自己的衣裳兜儿统统翻了个遍,最后翻出几十元钱。几十元,笑话,怎么拿得出手呢?
郝琳急得直跺脚,怪陈宗海亊先不通知她。
陈宗海说:“我也没料到这孩子有这一手。”又笑着说,“不要紧,我这儿有呵。”于是他拿出了钱。
不用叫,婷婷自己又回来了。
郝琳佯装从自己兜里掏出二百元整票,说:“婷婷,这也是阿姨的见面礼。”
婷婷嘴角笑了一下,接过钱,转身就要走。
“站住。”陈宗海命令,“没礼貌,也不知谢谢阿姨!”
“要谢也谢爸爸。”婷婷说,“因为这钱根本不是阿姨的,是爸爸的。”
走了。这里的陈宗海和郝琳满脸的尴尬。
好一个机灵鬼儿,好一个小人精!其实什么也瞒不了她。
陈宗海又是气、又是笑,郝琳这个人,却光剩下笑。
但陈宗海不依,如此让郝琳当面下不来台,他必须再去教训婷婷几句。
此时婷婷已没事人一样在客厅里看电视了。
电视正播放儿童mTV,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陈宗海走过去,坐在女儿身边:“哪有你这样?阿姨第一次见你……”
婷婷却不吭声,也不看陈宗海,只合着电视里的音乐摇头晃脑地唱:“……天上升起美丽的彩霞,远处是那铁壁铜墙。”她把“绿瓦红墙”故意唱成“铁壁铜墙”。
陈宗海生气:“跟你说话,没听见?”
但他突然发现婷婷眼里流出泪来了。觜里却仍在唱着:“……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陈宗海心头颤了一下,马上软了。他为女儿擦着眼泪,问道:“婷婷,因为什么哭?”
婷婷不哭了,站起来,去了卫生间,自己洗了脸,回来又挨陈宗海坐下。然后问道:“爸,你什么时候结婚?”
陈宗海说:“问这干嘛?装修完了就结婚。”
婷婷又问:“什么时候装修完?”
陈宗海说:“十月份,大概‘十。一’前后差不多了。”
“爸,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陈宗海说:“婷婷,如果爸爸的婚礼上见不到你,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果你能参加,对爸爸是个安慰,也是爸爸的骄傲。”
婷婷说:“我参加不过来。”
陈宗海奇怪:“什么叫参加不过来?还有谁那时候结婚?你们老师?还是你同学的家长?”
“我妈。”
陈宗海吓了一跳,完全糊涂了:“你妈?你妈还结什么婚?”
“因为她早就离婚了。”
“离婚了?和谁离婚?”
说婷婷有时大大咧咧,真是不假。她现在的样子像逗趣儿,如果是大人,便是玩世不恭:“和谁离婚?和那个牙医呀。”
“什么时候?”
“两个月以前呀。”
“那么,你妈又要和谁结婚?”
“赵国昌呀。”
“正经点,沒和你开玩笑,赵国昌是谁?”
婷婷颇有意思地歪起头:“赵国昌就是赵国昌呵,记不记得?他还送过我一个手机?”
陈宗海楞了老半天。然后深深地叹气。
他把婷婷搂过来,抚摸她的头,又亲了她的脸,说:“婷婷,原谅爸爸,行吗?向你保证,爸爸只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