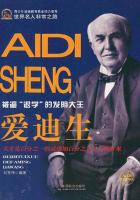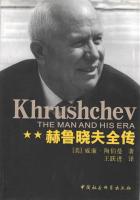在上海西爱咸斯路中段的大华酒家二楼,长年住着两男两女四个中年日本人,从衣着和风度看,男的像是新闻记者或作家一类的文人,女的像是阔太太或贵夫人,但他们却与纸笔书报无缘,成天忙忙碌碌,言行粗野下流。他们似夫妻又非夫妻,每个人各住着一进四间的套间,但若男女双方需要随时可以脱光衣服上床,实际上每人有两个妻子或两个丈夫。酒家老板虽然对他们的经商人的身份有几分怀疑,但见他们住进一年多来无损于酒家利益,也就从不过问,法租界的巡捕见他们受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和汪精卫的特工总部上海特区双重保护,对他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因此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原来,两个男的都是日本浪人,一个名叫狩野青一,一个名叫渡边山勇,两个女的都是已从良而又不完全从良的妓女,一个名叫合田贞凤子,一个名叫佐藤惠子。他们的任务是暗地侦探上海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军统组织,每月向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联络部领取相当于日军大佐的薪俸和一笔数字可观的活动经费。如果抓到一个证据确凿的共产党员或军统特务,至少可以获得两万日元的奖赏金。近几天,他们一直在侦探军统驻上海特派员罗梦芗的确切住址。罗梦芗是专员级特务,一旦抓到手,可得奖赏金十万日元,每人平均可得两万五千元,能够在日本农村买三十亩良田,可供八口之家享受较富裕的田粮之福。所以,抓获罗梦芗,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一月三日午饭后,他们四个人坐在狩野的住房里,研究如何尽快抓到罗梦芗。“刚才接到皇军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联络部长原田雄吉将军打来电话,他转告了松井石根司令长官的嘱咐,一定要在近三五天内把罗梦芗抓到手。原田部长说,松井司令长官讲了,把罗梦芗抓到手,十万元奖赏金一分不少。”狩野津津乐道,越说越兴奋,“希望大家多动脑子想办法,事情成功了,这笔巨款四个人平均分。”他手往自己的下身一指,“这回我若多得一分钱,就是钻女人胯部的这个。”他是为头的,过去的奖赏金他总是要多得一点。
狩野的最后一句粗野话,在这个非文明场所,好比铁锤落在棉花堆里毫无反响,因为他们说惯了也听惯了,习以为常。
“因为松井司令长官的限期是三五天,时间很紧迫,所以耽误诸位一点午休时间,汇报近一天多来的侦探情况,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狩野的嘴巴好比排污器,又排出一句脏话来:
“这回,就是他妈妈的罗梦芗钻到女人胯部去了,也要把他从阴道里抠出来!”
“罗梦芗很可能钻到女人胯部去了。”渡边微笑着说,“昨天晚上与特工总部的张国震先生喝酒,闲谈中,他告诉我,罗梦芗喜欢欣赏女裸体舞和半裸体舞。我考虑上海银月和明星两家歌舞团每场演出都有这个节目,就于今天上午十一点半赶到明星歌舞团,正好碰上演出结束,观众纷纷离开剧院回家。”他浓黑的眉毛往上一扬,“根据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个左胳膊挎着年轻女人的人很像罗梦芗,我马上拿出微型照相机给他拍照。拍完照,来不及注意他的轿车牌号,他带着那女人乘坐轿车走了。我赶紧坐上轿车跟上去,因为双方距离有一百五十多米远,一进入大街就不见他的踪影了。”他瞟了贞凤子和惠子一眼,“如果此人确实是罗梦芗,他肯定钻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胯部里。”
“你拍下的照片洗印好了没有?与原来掌握的照片对照对照,看你发现的那人是不是罗梦芗。”狩野兴致勃勃地说。
“我刚把底片冲好,你喊我开会,我就来你这里了。”渡边说,“我现在就去扩印一张。”
“你快去快来。”狩野吩咐一句。渡边走后,他从立柜里拿出厚厚的一本影集来,先看目录,很快在128面的“1212”编号中找到罗梦芗的一张二寸半身照。这张照片是一年前唐惠民提供的,相片背后有罗梦芗亲笔写的“惠民贤弟惠存,梦芗谨奉,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于武汉”等字样。
渡边拍的照片很快扩印出来了,照片上是个浓眉大眼,蓄一字胡须,头戴水獭皮冬帽,身穿呢料长大衣,脚穿封背式皮鞋,五十出头的男人。挽着他左胳膊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女人,眉清目秀,偏戴着一顶翻边呢礼帽,缎面旗袍上罩件浅色呢大衣,配以高跟毛皮鞋,显得雍容华贵。
“正是他,正是他!”狩野将两张照片反复对照和鉴别,高兴地说,“两张照片,时间相距三年,但脸型的棱角线条未变,你们看这眉毛,这眼睛,这颧骨,这腮帮,这胡须,都一模一样,正是罗梦芗!”
惠子从狩野手中接过两张照片看了看,说道:“现在,掌握到了罗梦芗的生活爱好就好了,我建议我们四个人分成两起,一起盯着银月歌舞团,一起盯着明星歌舞团,很快就可以把他抓到手。”
“松井司令长官给我的期限是三五天,如果近五天以内罗梦芗不去歌舞团怎么办?”狩野显得焦灼不安,“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是谁?是罗梦芗的姨太太还是姘妇,是妓女还是私娼?若能够了解这个女人的身份,也就可以找到罗梦芗的下落。”
“好家伙!这个女人我认识。”贞凤子望着照片惊喜地说,“她名叫徐俐娟,是个暗娼。”
“噢?你是怎么认识她的?”狩野急问道。
“说来话长。”贞凤子爽然一笑。
还是先从徐俐娟的身世说起吧:她是江苏无锡人,三年前毕业于无锡县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因姑父是保长,就在姑父那个保的国民小学任教。一个学期没干完,她嫌工资待遇太低,就不辞而别,流浪来到上海,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凭着自己的年轻美貌开始了暗娼生活。开初,门可罗雀,登门的嫖客寥寥无几。女房东年轻时干过这一行,言传身教,要她把自己的照片在报上登征婚启事为由把男人引过来。只要肉发出腥臭,还怕招不来苍蝇吗?半个月后,好色之徒纷至沓来而门庭若市了。不到一年时间,她就买了一座小花园洋房,雇了女佣、保镖和轿车司机,过着高级暗娼生活。按她自己的话说是:“门无杂宾,不干则已,一干至少可以吃喝一个月。”三个月前,徐俐娟带着保镖回无锡乡下老家,把母亲接到上海来为她管钱财。回来时,在火车上与到常州搞侦探的贞凤子邂逅相遇。徐俐娟见她热情,贞凤子见她大方,很快就打得火热了。一个小时以后,从昆山车站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她们见徐俐娟那娇嫩的脸蛋,撩云播雨的秋波,迷人的笑容,甜蜜的樱桃小嘴,高耸的乳房,楚楚动人的腰肢,浑圆的臀部,好像馋猫见到鲜鱼,禁不住垂涎三尺。其中一个见贞凤子与徐俐娟母女同坐在一个三人座位上,就指着徐俐娟的母亲和贞凤子说:“请你们两人让位,我们要陪这位姑娘坐坐。”徐俐娟母女俩已明白了他们要干什么,吓得诚惶诚恐,她的保镖就坐在对面座位上,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变得胆小如鼠,连哼也不敢哼一声。倒是贞凤子还有点胆量,当一个日本宪兵伸手拉她让位时,她“啪”地一下打落了他的手,然后愤然起身,手指他的鼻子,用日语厉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那人也用日语回答:“我们先陪她坐坐,再请她跟我们到乘务员的休息间睡一觉,你管得着吗?”另一个马上接腔:“你老了,我们不喜欢你,你吃醋吗?哈哈!”他一手拉住贞凤子的胳膊一拖,“走走走,知趣些!”想不到贞凤子连给他几记耳光,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你们知道我是谁?”随即把身份证伸过去,“你们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那挨打的只向身份证瞟了一眼不敢接。另一个怔怔地接过去一看,大吃一惊,这贞凤子是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邀大佐级侦破员。于是,两个日本宪兵连连点头哈腰做检讨和赔不是。因此,两天以后,徐俐娟为了感谢,也是为了进一步巴结贞凤子,使自己今后在上海有把保护伞,把她接到忆定盘路五十八号家里丰厚款待。因为贞凤子比徐俐娟大二十四岁,徐俐娟拜她为干妈。几天后,徐俐娟又与母亲来到贞凤子的住地,将一批金银首饰送到她手里。
“我们四个人真他妈的时来运转了,有了贞凤子与徐俐娟的特殊关系,等于十万元钱到了手!”渡边欣喜若狂,“我提议,我们三人每人少得一千元,让贞凤子得两万八千元,怎么样?”他手在贞凤子脸颊上捏了一下。没等狩野和惠子回答,贞凤子手指渡边的脑袋,学着狩野的腔调说:“这回我若多得一分,就是钻女人胯部的这个。”同是一句话,经贞凤子这么一发挥,倒引起狩野和惠子哈哈大笑。下午两点二十分,贞凤子携带一斤人参、两斤干荔枝和几斤苹果,叫了辆出租汽车来到徐俐娟家里。徐家的女佣热情地把她接下车来,帮助她提着礼品,陪同她去见徐俐娟的母亲张淑英。张淑英比贞凤子大十岁,她喊张淑英为“姐姐”,张淑英喊她为“妹妹”又感到不适合,就以“亲家”相称。
“你看你亲家,买这么多的好东西来,这就倒礼了!”张淑英尽管穿着藏蓝色毛哗叽全襟衣服,右胸处还别着个好看的胸花,仍然掩饰不了乡村农妇的纯朴本质。“亲家你是俐娟的干妈,这些东西由俐娟买来孝敬你才顺礼哩!你看,真是!由你送给俐娟,这怎么行呢?”她感到过意不去。
“这些东西是我买来孝敬姐姐的,理所当然,很顺礼哩!”贞凤子从女佣手中接过茶,亲亲热热地挨着张淑英坐下来,“俐娟在家吗?她近来还好吗?”
“在家,在家!还好,还好,托干妈的福!”张淑英也不讳言,“俐娟的所作所为,亲家你是知道的,为了弄钱,图个享受。”她把女儿的行为看成是正常的,话语中无丝毫酸楚感情,“近一向,她被一个老头子缠住了,那人一连几天都住在这里,只今天上午要俐娟陪他去明星歌舞团看了场歌舞。那人无论如何要跟俐娟结婚。俐娟不肯,认为结婚受约束,不自由。再说,那人年纪跟我差不多,五十好几了。亲家来了好,你给俐娟做做主吧,她可听你的话哩!”
“姐姐!对俐娟的终身大事,我们为母亲、为长辈的可以与她交换意见,但不宜干涉过多,主要是她自己拿主意。”贞凤子情意切切,“你说是吗?姐姐?”“亲家说得在理!”张淑英乐呵呵地说,“那你跟她交换交换意见。”“好,好。”贞凤子说,“这个男的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人?”“唵!取了个怪名字,听俐娟说,叫什么萝卜香。”张淑英说,“说他是军统里的一个大官,有钱有势。哦!我抽屉里有他的名片,我拿来给亲家看看,他是不是名叫‘萝卜香’。”
贞凤子接过名片一看,此人正是罗梦芗。顿时,仿佛她手中轻飘飘的名片,猛然变成了沉甸甸的一叠日元。两万五啦,好家伙!她心花怒放,一腔热血往上涌,脸上一片玫瑰色。她极力抑止自己的感情冲动,再将名片看一遍,见上面的职务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专员级特派员。”下边的地址,与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一样,她知道,其他都是真的,唯独住址是假的。
她把名片退还给张淑英,笑着说。“姐姐!这个人名字不叫‘萝卜香’,叫罗梦芗,的确是个大人物哩!”
“那亲家你就劝劝俐娟吧!让她从个良,结个婚,也是船行千里终有岸哩!”张淑英欣喜地说着,望望墙上的555牌圆钟,“噢!下午三点了,让亲家久等了!他们也该起床了,我上楼去把俐娟叫来与亲家见见面,说说话。”
“好。”贞凤子沉思一会,“姐姐就说你有什么事找俐娟商量,有罗梦芗与她在一起,不要说我来了。”张淑英点点头,迈着她那双先裹后放而变得尖不尖,短不短,长不长的脚上楼去了。
楼上与楼下一样,也是五间房子,正中一间为客厅,东边两间分别为徐俐娟的书房和卧室,西边两间是客房。书房里有上千种图书,有象棋,有钢琴,但这些东西长期受到冷落。嫖娼者来,也无心思玩琴棋诗画,只是肉体上的接触和性欲上的满足。其实,徐俐娟建立书房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以表示自己是个懂琴棋诗画的青楼名流,而抬高身价多弄钱。
徐俐娟的卧室布置,颇用了一番心计,跟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招蜂引蝶的魅力和肉感。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是十分柔和的浅蓝色,南北两个窗户垂着薄如蝉翼的浅绿色窗帘,床上铺着翠绿色的床单,被褥是翡翠色的杭州织锦,连地毯也是绿茸茸的,加以房间里喷射出一股最能刺激神经的芳香气味,人走进来,仿佛走进神话世界,立即产生一种艳遇着一群笑女裸体的神秘感和兴奋感。徐俐娟站在卧室里,她的肌肤显得特别嫩,特别细,特别柔软,特别光滑,更何况,嫖客一来钱到手,她还挑逗地卖弄风骚,不断地向对方献出温柔的微笑,飞出迷人的媚眼,送过甜蜜的亲吻来,身临其境,面临其人,纵使是个阳痿患者,也会激动一番。
现在,徐俐娟和罗梦芗已经起床,两人紧挨着坐在皮沙发上,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吸着高级香烟提神。“时间已过去五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后天可以跟我经香港赴重庆举行婚礼吗?”罗梦芗用平淡的语气,掩盖着内心的急切贪婪。
“何必硬要用结婚这种可怕的形式束缚我!你什么时候需要我,你什么时候来就是。”徐俐娟淡淡一笑,“你一来,不管我身上爬着哪个男人,我马上推开他让你来。”
“唉!那到底是露水夫妻呀。”罗梦芗伸手把她抱过来,“我想要你每天晚上都躺在我的怀抱里。”
“让我再好好考虑几天。”徐俐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