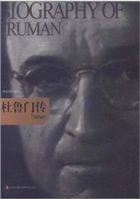“还要考虑几天?”罗梦芗急不可耐了,“你嫌我老,五十六了,是不是?”“那倒不是。”她说,“这可以用你的身份和地位,用你对我的爱,缩短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那你一定是嫌我有一妻两妾和十二个子女?”他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也不是。我知道,你会把一颗心全部掏给我。”她还他一个吻。“那你为什么还要考虑几天?”他问。“罗先生!我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啊!”徐俐娟缓缓起身,掀开南边的窗帘,无意识地向窗外望了望,又走回来,柔情地站在罗梦芗面前,“我若嫁给你,就会无情地结束了诗一般的,轻松的,自由的,愉快的,超脱的浪漫生活,过着刻板的,沉重的,单调的,苦闷的,可怕的监狱式生活。”
男女间搂搂抱抱,抚抚摩摩,睡睡玩玩,全好说,说到结婚,徐俐娟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徐小姐!”罗梦芗也站起身来,“你如果认为我是理想的丈夫,那么,你嫁给我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甜蜜感,充实感,安全感,自豪感。”
“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只让一个男人独占花魁,对这个女性本人是极可悲的,对众多的男性是极不公平的。”徐俐娟又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拿来一支香烟叼在嘴里。
“你还不感到满足?”罗梦芗赶忙擦燃火柴为她点烟,“与你睡过觉的男人还少吗!”“照你自己说,与你睡过的女人上百人,难道你感到满足了?”她吐出一圈圈烟圈。“我有了你做我的妻子,我非常满足了,而且永远满足!”他说。“可你五十六了,我才二十,人生享受才开始呢!”她沉重地喷出一口烟雾,“不懂得享受的人,白活了一世,是蠢驴!而真正懂得享受的人,却又太苦太苦了!所以,还是做蠢驴好。我这么一想,又十分懊悔我不该读到简师毕业;须知知识完全是人类的思想束缚,书读得越多,越做不了蠢驴!”
“既然如此,我马上就走。”罗梦芗喟然长叹一声。本来,以他的权势要得到徐俐娟并不难,只要他努努嘴,军统上海区的特务们一出面,手到擒来。但是,“捆绑不成夫妻”这句话深深教训过他。他先后用捆绑的办法娶过四房姨太太,其中有两房同居都不到一个月就逃跑了,没逃跑的两房也是同床异梦,不存在有丝毫的爱情,这使他认识到捆绑的结合,还不如逛妓院那样可以自由挑选,何苦?“我走后再不来你这里了,而且将永远离开上海。因为我在上海就会想到你的存在,就会受到种种不可名状的精神折磨。”一股强烈的失恋痛苦,从他心底冒了出来。这时,有人轻轻敲门。“谁呀?噢!是妈!您有重要事找我?好,我马上就来。”徐俐娟扶罗梦芗坐下,“你休息一会,我很快就来陪你。”“等你半个小时,你不来我就走。”他很气馁,又像在赌气。“何必这样呢?”徐俐娟走了几步又顿住脚,“好,也许还不需要半个小时我就来了。”她走下楼来,在母亲的卧室里见到贞凤子,又惊又喜。“哟!今天是什么风把我的好干妈给刮来了!”她亲热地挽着贞凤子一只胳膊。
“近半年来,中国人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宪兵司令部侦探缉拿共党分子和好战分子的任务也日益艰巨,所以将近一个月没有来看望姐姐和你了!”贞凤子有意回避抓军统特务的事。
“俐娟你看,你干妈带这么多的好礼物来,看你怎么谢你干妈。”张淑英说完,仿佛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坦然地坐在皮沙发上不吭声了。
“不用谢,不用谢,一点小意思,不足挂齿。”贞凤子快人快语,赶忙转过话题,“刚才姐姐告诉我,有个名叫罗梦芗的军统要人向你求婚,你答应了没有?别不好意思的!这样吧,到隔壁客厅去,跟干妈说说心里话。走!”
“你们不用走,让我走!”张淑英没有意识到贞凤子有意要回避她,“干妈待你胜亲妈,什么话都可以对干妈说,俐娟!”张淑英走后,贞凤子急切地问:“你同意罗先生的求婚啦?”
“干妈!我不会同意。”徐俐娟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女人,一旦她的家里出现了丈夫,她的家就变成牢房,她本人就变成了囚犯。所以,一提起结婚我就毛骨悚然。”
贞凤子也是个放荡不羁,追求性解放,玩弄男性,至今没有正式结婚的女人,笑着说:“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她顿了一会,“只是罗先生是军统要人,你不答应他的要求,只怕后患无穷啊!”
“那倒不怕。他刚才对我说,我若不答应,他马上就走。还说,他为了避免对我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痛苦,将永远离开上海。”徐俐娟不以为然地说。罗梦芗马上就走?将永远离开上海?贞凤子暗暗一怔。她沉思一会,说道:“也许是罗先生一时赌气吧,他十分爱你才向你求婚,势必不到黄河心不死。俐娟呀!依干妈预料,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那可怎么办?干妈!”徐俐娟心慌意乱,一时没有主张。
“你真的不爱他?真的不愿意与她结婚?”贞凤子把她搂在怀里。
“真的,真的!我赌咒,我发誓!”徐俐娟正经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做我的父亲还有余,我的确不爱他,的确不愿意与他结成夫妻!”
“那好吧!你设法稳住他,不要让他走了。”贞凤子想到白天在法租界抓人会引起许多麻烦,“晚上十点左右,我要驻沪日本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把他抓走。”
“好!我一定稳住他。”徐俐娟沉思一会又说,“军统会不会来找我的麻烦?”
“不会。”贞凤子说,“一来军统不可能知道姓罗的是在你家里被人抓走的,二来连姓罗的本人也不知道你与驻沪日本宪兵司令部有什么联系。”她想了想,又对徐俐娟进行必要的嘱咐。
徐俐娟送走了贞凤子,赶忙上楼来稳住罗梦芗。“罗先生你看,只二十五分钟我就来到你身边。”徐俐娟含情脉脉地把戴着手表的左手腕伸过去。罗梦芗没有看她的手表,只瞟了她一眼,警觉地问道:“你和你妈送上轿车的那女人是谁?你喊她为干妈?”徐俐娟怔了片刻,知道罗梦芗刚才从南边窗户向下窥视过,沉静地说:“上海实业洋行的经理太太。她与我妈从小一起在无锡乡下长大,两人很要好,一直以姐妹相称。因她没有女儿,非要我做她的干女儿不可!”“噢!我听到了,她喊你妈为姐姐。”罗梦芗深信不疑。“干妈待我可好哩!她一直关心着我的终身大事,多次劝我从良,找个理想的丈夫,有个好的归宿。”徐俐娟说,“今天又是为这件事来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别看她是干妈,可比我妈还操心哩!”“她给你做红娘来了?”罗梦芗很敏感,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是的。”徐俐娟郑重其事地点了一下头,“是干爹在大学任教授时的学生,现在也是个洋行经理,那人比我大十岁,一年前丧偶,前妻为他留下一个八岁的男孩。”她满嘴谎言,但说得像真的一样。
“你同意啦?”罗梦芗想到自己除了大学文化,其他方面都不如她说的这个男人,仿佛正听一场八级地震即将发生的预报,眼看一切美好的东西将会毁于旦夕。
“如果没有罗先生闯到我生活里来,我也许会同意。”她用媚眼挑视他,“近两年来,什么样的男人我都体验过。但我觉得,先生与我才是天作之合,我们的大小、长短、深浅恰到好处的和谐与协调。所以,不论是你还是我,在满足床上需要时感到特别舒服。”
“你是怎样回答你干妈的?”罗梦芗一颗心仍高高地悬着。
“我说我已与你定下来了。”她嫣然一笑,迷人极了。
“我的妈!我的娘!你永远属于我了!”罗梦芗浑身一酥,两膝一软,扑通跪在徐俐娟面前。
体态、长相的美,加上年龄优势,是女人征服一切的锐利武器。
有人说,女人像块处女地,男人想在上面怎么犁就怎么犁。作这种比喻的,大概是身上充满着粗俗气息的下里巴人,文人认为,女人的裸体像一本空白稿纸,男人可以在上面创做出许许多多优美而灼热的抒情诗篇。罗梦芗这一辈子纵欲贪色,在这方面有独特见解。他认为,赤身裸体的女人像一架音质纯美清晰的多音组钢琴,男人可以尽情地在上面演奏出千变万化,而又情真意切,悠扬婉转,奥妙无穷的动人曲调来。
此时此刻,是晚上九点四十分,罗梦芗正在跟徐俐娟演奏他最欣赏的曲调。看他那着迷的神色,仿佛他的身躯已经融化在他演奏的曲调中了。徐俐娟则不然,她真的像架只能发音而无知觉的钢琴,躺在床上听任他怎样摆弄。她正在等待着那个她盼望的,然而又是胆怯的、不安的时刻。
徐俐娟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十点差五分,她母亲敲着门喊道:“俐娟!你和先生起来一下,驻沪皇军宪兵部队和法租界工部局联合查户口的来了。”“好!我们马上起来。”徐俐娟早有思想准备,显得很镇静,“妈,您下楼去休息吧,官方查户口的事不用您管!”
罗梦芗先是一怔,心头一紧,本能地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紧握在手里,听说是司空见惯的查户口,很快镇静下来,但想到自己的户籍立在白克路,又有点心慌意乱,把嘴巴伸到徐俐娟耳边,悄声说:“我的户口不立在这里怎么办?”
“不用慌!一切由我来应付。”徐俐娟也把嘴巴伸到他耳边,“这家伙交给我保管,拿在你手里反而惹麻烦。”她从他手中把手枪拿过来,把它锁在抽屉里,然后转过身来开门。
从门外走进来两男一女三个人。两个男的是狩野和渡边,都穿着日本宪兵制服。女的就是惠子,她穿着浅棕色呢料大衣,冒充法租界工部局的人员。“请问,你就是户籍簿上面写的徐俐娟小姐吗?”惠子指着徐家的户籍簿问徐俐娟。
“是的!我是户主。称我女士吧,我已经结婚了。”徐俐娟手指坐在皮沙发上抽闷烟的罗梦芗,“他是我的丈夫程世盛先生。”
“他真是你的丈夫吗?”惠子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怎么你家的户籍簿上只有你和你母亲、女佣、男佣(保镖)和司机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她把户籍簿退还给徐俐娟。
“我们才结婚两天,他的户籍立在白克路七十八号,还来不及转过来。”徐俐娟早有准备,回答得很自然,使罗梦芗暗暗钦佩。“请程先生出示身份证件。”惠子很像威严的法官。“自由职业者,《武汉时报》驻沪记者程世盛。”罗梦芗把假记者证递过去。
惠子看了看记者证上的照片,又故意把目光停留在罗梦芗那肥胖的脸上,将他审视一番,才把记者证退还给他,然后冷笑一声,说道:“你不是什么新闻记者吧!”
“是新闻记者,一点不假。”罗梦芗一怔。“请先生查阅最近一个时期的《武汉时报》,那上面有他的好几篇通讯和新闻,署名就是程世盛。”徐俐娟胡编一顿。
“署名用的谐音‘陈仕胜’。”罗梦芗担心对方真的要查阅报纸反而弄巧成拙,想到他的朋友陈仕胜在《武汉时报》当副刊主编,经常写文章,赶忙补充一句。
惠子从提包里拿出今天上午渡边在明星歌舞团门口为罗梦芗和徐俐娟拍的那张照片,给罗梦芗看了看,又给徐俐娟看了看,然后冷冷地问。“这是你们的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