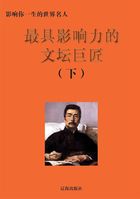“晚餐我弄几个好菜,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庆贺庆贺。”陈舜贞也欢天喜地。她年已半百,身体开始发福,但以大使夫人身份来东京之后,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倒也轮廓均匀,显出几分富有性感的曲线。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倒退的民族素质,像紧箍咒似的箍在世界上最大的黄皮肤人群头上。为了在世界民族之林守住赖以为生的一席立足之地,一反礼仪之邦的高尚品德,虚伪和欺骗成了手中战无不胜的法宝。从理论讲,这样做是犯罪,至少是不道德。可是,在这个世界里,理论在实践面前却是那样一文不值。弱者如此,强者为了获得更加优越的生存条件,玩弄起虚伪和欺骗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就是如此。其实,历史的进展从来不考虑什么道德问题。大凡人类从来就是使用硬的软的,明的暗的,合理不合法的,合法不合理的,名正言不顺的,言顺名不正的,等等各种手段,获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而生存的吧!既然如此,那么,相反,对弱者不应该批判,而应该为之大唱赞歌。
然而,细细想来,这又是什么逻辑?可悲可叹而又可怜的人类啊!
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松冈来到首相办公室,向近卫汇报。说他收到重庆政府外交部的电报,川樾茂的确到了重庆。没等松冈说完,近卫就急切地问:“重庆的电报还说了些什么?”
“他们提出是否以川樾茂君为代表,就日华停战问题举行会谈。”松冈说,“同时要求我们释放许世英。”
“看来,还得继续坚持我三年前的第二次对华声明说的,今后日华停战和谈不以蒋先生的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微皱着眉头,思绪万千,“我们给重庆的抗议电报,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有!刚才接到铃木君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重庆已派专机由章友三护送川樾茂和顾继武抵达香港。”松冈满意地笑着。
“铃木君请示,章友三要求护送川樾茂和顾继武来东京是否可以?许世英是否马上释放?”
蒋介石接到日本的抗议电报之后,想到有川樾茂和顾继武的现身说法,准会使南京与东京之间出现一场狗咬狗的激烈斗争,从而加速南京政府的灭亡,于是顺水推舟,马上派专机由到过东京的章友三护送他们来了。当然,也害怕日本飞机的轰炸,不过这已不是主要因素。
“同意章友三把他们护送到东京来,最好下午就来。”近卫权威地说,“可以马上释放许世英,要香港领事馆给他理发、洗澡和换一套新衣服,然后把他交给章友三,再由章友三安排他回重庆。”
下午四点四十分,松冈派外务省书记官角田尤太郎随车去追浜机场把川樾茂、顾继武和章友三接到外务省接待处。在接待处,松冈单独接见川樾茂。他听川樾茂说自己是被汪精卫集团关押的,审讯他的就是顾继武,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个小时之后,近卫从松冈嘴里得知这一情况时,仿佛晴天一个霹雳,惊得他恍恍惚惚、昏昏沉沉。究竟谁是真谁是假?事关重大,不可马虎。近卫决定晚上由松冈出面,把褚民谊、董道宁和影佐叫来,与川樾茂、顾继武和章友三当场对证,看到底谁是真金谁是沙石。他大概从首相身份考虑,不便直接参加,但想到这场面一定如同阅读一部惊险小说一样味道十足,又很想直接听听。于是,他带着秘书牛场静坐在外务省小会议室里面一间房子里,为了听得清楚,门不关,只把门帘放下来,活像皇太后垂帘听政。
晚上七点,一场唇枪舌战即将开始。坐在小会议室的除了对战双方各三个人以外,还有松冈和他的女秘书美静子、书记官角田。房间里有着临战前等待信号弹发出的那种宁静。对战双方表面上都显得很镇静,脑子却紧张得要命。
松冈首先讲话,他说:“川樾茂先生的被关押四个月,南京方面一口咬定是重庆干的,重庆方面一口咬定是南京干的,究竟谁是谁非?为了使问题水落石出,今晚来个三头六面,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好,下面请受害的川樾茂先生先说。”
“我的不幸,是汪精卫先生他们一手制造的。”川樾茂哀叹地说,“我被关押之后,有两个中年人审讯我,让我坐‘老虎凳’受刑,强迫我向帝国政府拍电报,要挟政府立即停止所谓对中国的侵略。审讯我的两个中年人,那为首一个现在就坐在这里。”他手向顾继武一指,“就是这位顾继武先生,南京政府的社会部次长。”
与会者一齐把眼光投向顾继武,只见他不阴不阳地微笑着。是苦笑?是怪笑?还是奸笑?大家等待着下文。
川樾茂接着说:“营救我的是重庆政府的军统特工人员。到了重庆才知道,就是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先生和赵君理、徐直诚先生。我当时戴着脚镣手铐,行动不方便,是徐先生把我从后门背出去之后再上车的。”他手指章友三,“这些情况章先生很清楚。”
“很清楚,我很清楚。”章友三连连点头。
“章先生当时在场?”松冈问。
“我当时不在场,是陈恭澍先生对我说的,与川樾茂先生说的完全一样。”
章友三说。
“顾先生!”松冈阴沉着脸望着顾继武,“川樾茂先生说的是不是事实?或者说有没有出入?下面请你发言。”
“川樾茂先生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是军统的人,也没有在场,我无权发言。”顾继武仍然微笑着,“现在就川樾茂先生说的第一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他的不幸是汪先生他们一手制造的,那么请问:你有人证吗?有物证吗?”他鄙夷地望了川樾茂一眼,“其次他把矛头对准我,说以我为首,什么审讯他,什么让他坐‘老虎凳’,什么强迫他拍电报,根本没有这回事。”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骚动。
“根本没有这回事?只能说明你在抵赖!”川樾茂面有愠色。
顾继武也不生气,沉着应战,“众所周知,川樾茂先生是汪委员长的好朋友,是受南京政府尊重的好朋友,如果我审讯他,让他受刑,我不怕汪委员长治罪,我不怕掉脑袋?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道我吃了豹子胆!”他神态自若,语调恳切,“至于说我强迫他拍电报,要日本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天大的笑话。请问川樾茂先生,骂贵国侵略中国的是些什么人?是共产党分子,是重庆政府中的主战派和好战分子!”他冷笑一声,“恕我冒昧地说一句,可能是川樾茂先生的神经有点不正常!”
“不准你侮辱我的人格!”川樾茂既无人证,又无物证,感到有口难辩,脸憋得通红。他镇静下来,想了想,说道:“请顾先生不要反口,这些问题,前天晚饭后,你当着我的面都承认了的,并一再向我请罪,要我原谅你。”
“我还是那句话,根本没有这回事!”顾继武矢口否定。
“有军统赵君理先生在场,你抵赖不了!”川樾茂说。
“除非你买通赵君理为你做死证。”顾继武一言顶了回去。
“你无法抵赖,顾先生!”章友三从皮料提包里拿出三页纪录稿,得意地在手上挥了挥,“这是昨天,也就是元旦下午,军统戴笠副局长审讯你的记录,你在上面签了字,白纸黑字,你抵赖得了吗?”他起身将纪录稿递给松冈,“请外相阁下过目。”
大家又把目光投向顾继武,只见他神态安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松冈聚精会神地将纪录稿连看两遍,起身走到顾继武而前,指着上面“系我招供,情况属实。顾继武,一月一日下午六点。”等字样,问道:“这是你的笔迹吗?”
顾继武不慌不忙地偏过头去,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看了好一阵,连连摇头:“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的笔迹!外相阁下若不相信,请拿纸笔来,当场对笔迹。”他在签字时早就在笔画上做了翻案的准备。不过,当时是准备有朝一日回南京后在汪精卫面前赖账,并没有想到与川樾茂对证。现在,他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暗暗高兴,继续说:“至于所谓纪录稿,我不用看就知道上面写了什么!的确,昨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到六点,戴先生审问过我。他先是来软的,说只要我出面作证,证明我审讯过川樾茂先生,承认我对他用过刑和强迫他拍过电报,让我当重庆市长,还说这是蒋委员长的意见。”
又是一阵骚动。
“我不依,戴先生就给我一顿拳打脚踢!”顾继武神气起来,“而我,仍然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两手一摊,“唉!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川樾茂先生为什么与军统一个鼻孔出气?”
房间里的骚动更为强烈,美静子和角田交头接耳,在低声嘀咕着什么。“谁跟军统一个鼻孔出气?你血口喷人!”川樾茂恼羞成怒,脸上一片猪肝色。“好吧,现在对笔迹。”松冈要角田拿来了纸和笔。
顾继武那神色,仿佛正在参加书法比赛。他接过纸笔,按同样的内容连写三遍,是一手颜体字,而纪录稿上面的签字却是潦潦草草不成体。经过松冈和美静子、角田一番反复的鉴别,虽然没有当场宣布,但一致认为纪录稿上面的签字不是顾继武的笔迹。
“川樾茂先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松冈也怀疑川樾茂被军统收买了,投在他脸上的目光是惊讶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汪精卫先生他们不愿意停战和谈,更不愿意重新与蒋介石先生合作,就采取关押我的这种卑鄙手段制造混乱,妄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川樾茂说得理直气壮,但精神上已经败降,“恳求政府派人去上海和重庆进行调查,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听从政府怎么处置我。”
“我负责向首相阁下转告你的要求。”松冈向大家扫了一眼,“在座诸位先生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几句。”影佐正正鼻梁上的眼镜,“我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过去的一年,我与川樾茂先生好比长在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瓜,我们俩都在中国遭到不幸,而且又都是受政府的派遣,就日华停战和谈去中国遭到不幸的。我遭到不幸在前,是去年六月中旬,川樾茂先生在后,是去年九月底。可是,我比川樾茂先生更惨,军统妄图毒死我,我差点死在重庆。我住了四个月医院,你坐了四个月监牢,彼此彼此。然而,我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还留下了后遗症,经常头昏和恶心。从这一点说,川樾茂先生比我幸运。我们俩的遭遇是偶然的吗?是巧合吗?都不是!而是蒋介石先生仇恨大日本帝国,反对日华停战和谈的必然结果。我可以断定,如果政府还派第三位使节去重庆和谈,其遭遇可能比我们俩还要惨!因此,我希望川樾茂先生不要轻信重庆方面的花言巧语。”
“我才不轻易相信人家的花言巧语哩!”川樾茂反感地瞪了影佐一眼。
“好,这个问题我不多嘴了。”影佐不与川樾茂争辩,马上转过话题:“我受政府的派遣,具体与汪先生,与南京政府的首脑们打交道已经三年了,我对他们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对日华停战和谈,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这一点,在汪先生公开场听的屡次讲话中,在南京政府的许多文件中,处处可见,真是屡见不鲜。这一点,我们的近卫首相阁下和松冈外相阁下心中最有数,无须我多讲。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今晚的辩论会到此结束。”松冈说,“双方的发言,已由美静子女士和角田先生纪录在册,由他们整理好以后呈报近卫首相阁下。究竟谁是谁非,请首相阁下定夺。好,请川樾茂先生留一会,其余诸位先生请退席。”
现在,小会议室里只剩下松冈和川樾茂两个人。川樾茂正在思考着为什么单独把他留在这里,近卫幽灵似的带着牛场从里面房间走出来,使他一惊。刚才双方的辩论,无须送纪录给近卫看,他什么都知道了,谁是真谁是假,他马上可以做出结论。川樾茂越想越紧张,尤其是近卫见到他,连个招呼也没有打,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也明白了近卫对今晚双方辩论所持的态度。他惶惑不安,也感到很委屈。他很想再看近卫一眼,但没有这份勇气。这时候近卫的面孔一定严肃得可怕,他想。
“川樾茂君!对于你在中国不幸被囚禁四个月,我代表政府向你表示同情和慰问。”近卫的语句陈如美酒,但语气淡如清水。
“谢谢首相阁下。”川樾茂礼节性应酬一句。
“但也有必要向川樾茂君严正指出,你身为帝国的使节,这次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吃惊,令人痛心,也令人遗憾!”近卫横眉立目,“你必须以诚实和忏悔的态度,书面向外务省检讨两个问题:一是你四个月前为什么要拍回那分有辱帝国的电报?你为什么那样怕死?人家让你坐一会‘老虎凳’你就屈膝投降了?你身上的武士道精神到哪里去了?二是你是怎样被重庆收买的?你身上的武士道精神又到哪里去了?”他望了垂头丧气的川樾茂一眼,“不妨如实告诉你,内阁五相会议成员看了你的电报,都非常气愤!当时,陆军相东条君说:‘要是陆军中有这种可耻行为的军官,我非枪毙了他不可’,海军相及川君说他在上海任舰队司令时,有个名叫阿川田文的海军少佐被军统抓去,舰队司令部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却写了悔过书回来了。及川君先要他背了武士道精神的基本点,然后把他的手枪交给阿川,让他自杀了!因此,我奉劝川樾茂君,你必须诚恳地检讨自己,以求得五相会议对你的谅解。到时,我与松冈君也好为你说话。”
“是的,只要川樾茂君老实认罪,我与首相阁下一定为你说话。”松冈附和着说。
“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啊!”年值花甲,当了三十八年外交官的川樾茂,这回却彻底败在顾继武手里,他扑通一声跪在近卫和松冈面前,放声痛哭,只有大喊冤枉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