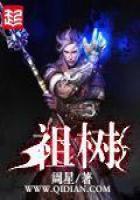时间刚过晌午,热闹的七霞镇上,午后的时光并没有普通小镇那么惬意,嘈杂,忙碌的日子因为人渐渐的开始变多而开始了。
“随客来”这块招牌挂了有十几年了,对于这个镇上其他的十几家客栈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客栈很年轻,但是客栈的老板却真的很老,大小也是一位老板,衣衫当然不会像普通人家那么朴素,满脸的褶子却是再怎么华贵的衣服都弥补不了的;老板伛偻着身子正坐在水井旁的小石凳上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大儿子在前面的柜上噼里啪啦的打着算盘,老婆子和小儿媳妇去集上卖菜了,小儿子正在前厅擦着桌子,等着招呼客人。
客栈不小,八九间客房,两间通铺,后面有一个小院儿,小院内有一口吃水的井,在院子东北角有一排木桩隔起来的马厩。想来当时,首辅杨大人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小住过的。
今天镇上的几家大点的客栈都被一个客商包下了,听说是西胡的商队,老板想着,那些蛮子又来赚大未的钱了;通铺已经有一间住满了,客房都还空着,老板看了一眼东北角的马厩,想来今年的学子们都不怎么勤勉。
老板正走着神,小院的后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面向清秀的少年牵着一匹枣红马缓缓的走了进来,少年身着轻纱长衫,刻意高挽的发髻非常明显,背着一个行囊,马背上却没有随身携带的书箱,老板打量了一眼少年,笑呵呵的问道:“客官,您是住店啊还是休息啊?”
老板的文化让少年一阵错愕:“我说我是来打尖的你信吗?”
老板的脸上的褶子顿时堆到了一起,露出几颗“金灿灿”的牙齿上前要接过少年手中的马匹,“它认生,我得先开导开导它。”少年婉拒了老板的好意,自己牵着马向马厩走去,老板跟在少年的后面开始问道:“这位客官,您是从南来还是从北来啊?”少年把马栓在了马厩里,从马厩边上抱了一些草料放在了马槽内,掸了掸身上的风尘,笑道:“从南来!”
“那客官肯定是要北去了!这刚刚开春儿,北地还是很冷的,客官穿这么单薄,却怎么也不像是北去的!”老头儿引着少年上了楼梯。
“那您看我是往哪里去的?”
“看您的穿着打扮,怎么都像是去京城大试的学子,但是你又和别的学子不同;别的学子进京大试大多都随身带着书箱,家中富足的也会随身带着书童,你说你又是自南来;我开了十几年的店,这还是头一回拿不准你这样的客官。”老板带着少年来到了楼梯边的第一间房,把少年引了进去。
房间不奢华但是却很整洁,少年把包袱放下,给了老板两贯大钱,“你帮我弄点吃的,我一路赶来还没怎么进食,帮我烧点水我要洗个澡,钱不够您吱声。”“好嘞!那你休息啊客官!”
老板接过大钱,高高兴兴的下楼烧水去了。
少年躺在床上,看着客栈的房顶,自言自语的说道:“这老板倒还挺有意思,书箱?我倒是忽略了。”
七霞镇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几乎是北地的学子;那支西胡的商队还没有到七霞镇,但是商队的当家早就遣人来到七霞镇,将几家比较大的客栈都包了下来,这么大的手笔在七霞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西胡的商队每年都来,这些有钱的蛮子早已成为七霞镇上有名的过客。
有名的过客还没有到来,不知名的过客却先来了。
一袭白衣配白马,杨庆之一路可是多多少少出了些风头,六子的马车随在杨庆之的“滚滚烟尘”之后,嘴里的面馍还在六子嘴里牢牢的咬着,嘴里的涎水已经积了“一潭”,嘴边的面馍却早已不复起初那么“白净”。
石制的牌楼,看不出岁月的斑驳,俊朗的少年,还没经历时间的洗礼,一人一马一牌楼,是一幅画,后面是咬着面馍的六子和车里的管家。
下马如上马似得卖弄风骚,只有六子知道自己少爷这样飒爽的身姿的的确确是天生的,少年手握马缰,轻抚了一下马的鬃毛,白马高兴的晃了晃他的大脑袋,然后跟着前面那个和他穿一个颜色“马甲”的人走进七霞镇。
街道之中人来人往,两旁的吆喝此起彼伏,完完全全的一副市井模样,不理会扒手们又摸走了谁的钱袋,不在乎摊位后面的胡同多么的脏乱差,至少此番景象很朴实,很贴切。
“吴爷,为什么我总感觉这嘈杂的街道虽然热闹,但还是缺点什么?”六子悠悠的驾着车,管家坐在车排的另一边。
“缺个能说会道,好奇心不满足的年轻人。”管家根本就没有看坐在那边的六子,嘴上却狠狠的挖苦道。
“吴爷,你真的不觉得缺点什么吗?”六子也没看旁边的管家,直勾勾的盯着走在前面的杨庆之。
“你说缺啥?”管家终于也拗不过这个嘴碎的少年。
“缺咱们少爷啊!”
“响!!!这声马屁拍的响!你看少爷就牵着马在前面走呢,你赶紧去,五步之内肯定能摸到马屁股,你赶紧去拍,只要少爷的花儿不受到惊吓,你准能拍的让整条街的人都侧目!”
后面越是热闹,前面的少年越是显得安静;杨庆之知道,后面的管家和六子也知道,甚至全临川县城的人都知道,杨庆之这位当朝首辅的独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未曾几时,杨庆之的名字在临川县城也是家喻户晓,而这“显赫”的名声却一点也和他显赫的父亲沾不上半点关系,全是自己平日里慢慢积累的。
可是中秋之后,杨林给他去过一封信,让他准备来京备试,最后不忘告诫他路上低调,切不可生出是非。虽然七年之间和父亲几乎没怎么见过面,但杨庆之记事早,所以他听父亲的话也就早,这是一个很久之前就养成的习惯,他从来都不悖逆他父亲的意思,当然,事实也证明很多时候他父亲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虽然没有刻意的要求杨庆之要这么安静,但是杨庆之了解自己,一旦稍有放纵,便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不怕,但只要有违背父亲意思的可能,他就不会去做,所以他一路小心谨慎,连六子都看不过去了。
客栈的招牌有些旧了,但是客栈的房子从外面看还不是特别显陈旧的,没有临街,“随客来”迎来了他第二位客人。
老板的大儿子正在“噼啪噼啪”的打着算盘,店再小账本也要精细,看来这位少东家还是挺认真负责的,小儿子看到有人进来了赶紧上前招呼。
“客官,住住住住住,住店?”
杨庆之看着这个有些结巴的店小二,心里生出一些好奇的感觉,但忍住一丝丝笑意,回道:“嗯,住店。”
“就就就就就,您,一,一个人吗?”
杨庆之不忍心为难这位结巴的小二,而且一路奔波,早已没有心思与这个有趣的小二调笑,立马说道:“我们一共有三个人,两匹马一排车,我要两间房,最好挨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紧挨着楼梯的那间。”
小二怔怔的听着杨庆之说完,老板的大儿子还在算账,似乎没有帮着自己弟弟招呼客人的意思,也可能是算账算的太投入了,反正没有理会这里。
“好嘞!”从进门到现在,这店小二兼二少东家只说了两个连贯未停顿的词语“客官”,“好嘞”,杨庆之久不出门,不知道其实所有的小二只要会这两句就能在这普天之下的“小二届”立足!
领着杨庆之来到后院,小六和管家还没有安顿好马和车,小二就先领着杨庆之上了二楼,杨庆之跟在小二的身后。
七年之前他跟随母亲来过这里,他对外面的门面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小院儿,这木质的楼梯,小院里的水井,他都记得很清楚;他总能记得那晚的残月不是很亮,但是星星却是前所未有的明,母亲抱着他坐在院子的石头墩子上,给他讲故事,又像是在叮嘱他,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给他讲完故事后偷偷的抹泪,但是他的记忆中,那是和母亲相处的最后的时光。
小二和杨庆之来到挨着楼梯的房间,杨庆之从怀里掏出一小锭银子交予小二,吩咐道:“给我们准备点吃的,不用太多,我们只是打打尖,烧点热水,我想洗个澡,银子先存柜上,你多支五个大钱,我赏你的。”
小二拿了钱也没多说,自己下楼去了。杨庆之笑了笑,缓缓的推开了折扇房门。
虽然已经过了七年,但是屋里的陈设没有什么变化,屏风上的那朵红花还是那么鲜艳,桌子的边边角角有些刮擦,当初一夜未合眼,屋里的所有细节都在心中留了下来,小凳,窗框,还有床,都和当时和母亲一起在这投宿时一模一样,只是,母亲此时已不会再看到这里的景象了。
看着屋里的陈设,心中多少有些五味,有了五味也就免不了杂陈,故地,旧物,一应场景都和当年一样,只是床笫间多出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