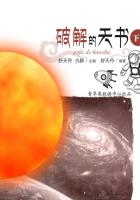在塔普洱困,我们能买到一些饼干。好几天除了能吃到肉之外,我品尝不到任何东西。我一点也不讨厌这种新食物,但我感觉“它”在分享我的艰苦经历。我听说,英国病人有特殊的肉类菜谱,但他们很少能一直坚持吃这东西,甚至即使这种肉类能治愈他们的疾病。但高卓人,他们几个月不吃别的东西,就只吃牛肉。据我观察,他们吃的肉的很大部分是脂肪。他们特别不喜欢干牛肉或者那些刺鼠的肉。也许,对他们的菜谱的叙述可以这样说明:他们像别的只吃肉类的动物一样,能跋山涉水到很远的地方,而不需要补充其他食物。有人告诉我说,一些高卓人,他们自己说的,在追赶印第安人时,可不吃不喝。一天晚上,我们在福克兰群岛的乔伊索海峡的西南半岛上夜营。这个峡谷确实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但很少能找到柴火。高卓人,让我吃惊的是,很快就找到近期被兀鹰杀害的小牛骨架,用以燃烧,所生的火如同炭火一样热。高卓人告诉我,在冬天他们经常杀掉一头牲畜,用刀把肉刮干净,然后用骨头直接烧烤这些肉做晚餐。
拉普拉塔人
在圣达菲,我因为头痛而困在家两天。一个好心的老妇女,给我介绍了许多奇怪的药方。通常的做法是:在每边的太阳穴贴上橘子叶或黑石膏。一种更通常的做法是把豆粒切成两半,弄湿,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片。在太阳穴上贴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移动豆片或黑石膏被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只能让它们自行掉落。有时,有人会问一个头上贴两片的人:“请问,这是什么?”他会回答:“我前天头痛。”
乌拉圭人
在马尔多纳,我们睡在一个废弃的农村房子里。在那儿我发现我拥有2到3件奇宝,特别是一个口袋型罗盘,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每一户人家里,他们都要求我展示宝贝。在罗盘和一张地图的帮助下,我能指出各个地方的方位。这激起了他们对我的最大敬意,认为我是一个优异的陌生人,知道任何我没去过的地方的任何道路(方向和路在这个开阔的国家里意味着同一件事)。在一所房子里,一个年轻姑娘卧病在床,请我去向她展示我的罗盘。如果他们的惊讶越大,我的惊讶也就越大:发现这些拥有上千头牛以及巨大草场的人竟是如此无知。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可以由这个国家很少有外国人到访来解释。
有人问我太阳或地球是否是移动的,北方或西班牙所在的地方是更热还是更冷;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更多的人对英格兰、伦敦、北美的概念模模糊糊,认为它们是同一地方的不同名称。但那些见识稍多的人知道,伦敦和北美是不同的地方,但连在一起,英格兰是伦敦的一个大镇。我带来了独创性的火柴,并咬燃了它。这是多么美妙的奇迹啊!一个人用他的牙齿点火,以至于他们会集中起一家子的人来一起观看。有一次,一个人用一美元换我的一根火柴。
在拉斯米纳斯的一个村庄,我早上洗脸时引起了很大的围观。一个商人离我很近,询问我一个英国人“极其与众不同的做法”——在甲板上我们为什么留胡子(他从我的向导那里听说我们是这样做的),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寻找住宿起来很方便的房子,在这个国家是很普通的习俗。他们对罗盘以及别的魔幻般的东西很惊讶,还有我的长长的旅行经历,我收集到的碎石,收集到的昆虫,以及无害蛇的毒液,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是我的优势。对于他们的友善,我也回报了他们。我想我好像是在生活在中部非洲的民众当中写作,虽然东方的班达人不会因为此类的比较而感到高兴,然而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在去里奥·尼格罗的梅赛德斯的路上,刚到一个牧场,我们就请求作一下休整,顺便去睡一觉。牧场主是这个国家里最大的地产主之一,拥有牧场方圆10里格之多的土地。牧场主的侄儿负责经营,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逃跑的陆军中尉。考虑到他们的状况,他们的对话就很让人发笑。就像往常一样,他们对地球是圆的感到很惊愕;而且,很难让他们相信:如果挖一个足够深的洞,就能从地球的一边到达另一边。然而,他们听说过有个国家一年中有6个月处于黑暗之中,而另外的六个月则白光耀眼,以及那里的人既高且瘦。他们对英格兰的马和牛的价格和状况很感兴趣。当他们知道我们不用套索抓捕动物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叫起来:“呀,呀,呀,那么你们肯定就只用流星锤了。”一个封闭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这个中尉最后说,他有一个问题要问我,如果我能非常客观地回答,他会非常感激。这问题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人是否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我回答道:“从魅力上来说是。”他说还有另一个问题,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女人们是否都戴有这样的大梳子?我认真地对他的疑惑进行了确认:不。对于我的回答,他们绝对是非常高兴的。这个中尉叫起来:“看,这个见过世面的人说确实是那样,正像我们以前所想的,现在我们能确认了。
我的对梳子和“漂亮”问题的回答让我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招待。
中尉硬要我睡在他的床铺上,他自己则睡在条子上。
在梅赛德斯,我问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干活,一个严肃地回答是昼日太长,另一个说他太穷了。在这个国家里,马产业和粮食产业的繁荣是对其他所有产业的阻碍。这里有很多的节日,并且,那些节日只有在月亮升起时才开始。由于这两种原因,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哥伦比亚,也在其他地方,我注意到很多人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很感兴趣。对于他们的代表,居民们并不要求他们受多高的教育,我听到一些人对哥伦比亚代表们的优点进行讨论;我也听说,尽管他们不是生意人,但他们都能写自己的名字。从这一点看来,他们认为那些非常讲道理的人应该被选上。
智利人
我必须对每一个智利人那与生俱来的礼貌表示敬意。我可以说说一件偶然的事件,我确实对此事感到高兴。在门多萨附近,有一个个头很小但很胖的黑女人,骑着骡子迷失了方向;她的甲状腺肿得非常大,几乎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会逃离别人的眼睛。但我的两个智利同伴几乎是立时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方式,脱帽表示歉意。
在欧洲,这是低等或高等人向一个地位低的可怜人或穷人显示礼貌的方式。
我对这个国家的地理勘察和解释通常在智利人当中引起惊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他们信服我不是为了矿产而来。这,有时确实挺烦人的。我觉得解释我的职业的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们对于地震和火山有多关心?为什么在智利有山,而在拉普拉塔没有?这些直白的问题立即吸引了很多听众,让他们沉静下来。然而,一些人(像生活在100多年前的英国人)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无用的、不虔诚的,他们相当满足于上帝造山的解释。
智利矿工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喜好。他们要在几近荒芜的地方待在一起几个星期,在喜庆日子去乡村。他们一点儿也不张扬、放肆和奢侈,他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有时也赚点钱,然后,像水手获得奖金一样,试着多快能把它花光。他们过度饮酒,买大量的衣服,几天之后,又身无分文地回到寒碜的住所,在那儿,他们干活努力得像野兽。他们的这种粗心率真,不假思索,就像水手一样,显然是一种类似生活模式的结果。日常的食物是人家为他们准备好的,他们没有关心、用心的习惯,而且同时,自然而然的惯力和各种现存安排也不会使他们拥有思考的习惯。在另一方面,在康沃尔以及英格兰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允许买卖部分的矿脉,因而矿工们不得不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思考,因此这里的矿工就特别聪明,言行举止也很得体。
智利矿工的穿束很特别,可以说是生动如画。一些黑色厚羊毛毯制成的长衬衫,戴着皮革围裙,然后由一根亮色腰带在腰间绑起来,裤子很宽,红布制成的小帽子很紧地扣在头上。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穿束的智利矿工,他们在抬一个矿友去埋葬。四个人抬尸,步伐很快。在尽全力走了大约200码之后,又有四个人来替换抬尸者。这些替换之人是早先骑马走在前头的。就这样,葬尸队一边哭喊着,鼓励着,一边往前走。从总体上看,这是最奇怪的丧葬习俗。
海德船长对这些人力扛夫从最深的地矿里扛东西作了很形象的描述。我得承认,我原先认为他所描述的有些夸张了,因此我很愿意借此机会来体会体会其中的一个负荷,我随机地挑出一个;当站在负荷上面时,就把它从地上背起来,我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个负荷差不多是197磅,一般说来,算是轻的。这些矿工从矿洞下沿一条陡峭的路上来,所搬运的路程上下垂直距离有80码;其中有一段的路非常陡峭,更大的一部分有台阶,沿之字形路径斜斜而上。根据规定,除非矿井深达600码,否则工人是不允许休息的。
平均负荷一般比200磅要大很多,我确信,一个称重过的300磅的重量,也从最深的地下被搬了上来。在这个时候,矿工一般一天搬20次,从80码深的地下搬上一般是240磅的负荷。他们有时被雇用来砸碎矿石,选出铁矿。
这些人,除非发生了事故,否则始终是很健康的,精神状态也很好。他们的身体不是很粗壮,很少吃肉,差不多一周一次。虽然知道他们不是被强迫劳动的,但看到他们从洞口出来时确实很让人震动,他们的身体向前弯,两只脚呈弓形,肌肉在抖动,汗水从他们的脸上流淌到胸膛,鼻孔朝前伸,嘴角有力地向后拉,呼吸非常急促。脚步蹒跚地走到矿堆,扔下矿石,调整呼吸两三秒后,擦了擦眉头刚冒出来的汗水,又快速地下井了。在我看来,这是个极好的例子,能说明劳动这种习惯,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将使一个人学会忍受。
西班牙人
一天,我们在亚奎尔金矿的时候,一个德国自然历史证物搜集者,名叫雷纳斯,与一个老西班牙律师碰到了一起。他们的对话确实很搞笑。雷纳斯说西班牙语,那个老律师误以为他是智利人,雷纳斯问他,对于英国国王派出一个搜集者(指的是我)到他的国家搜集蜥蜴、甲虫和碎石,有什么想法。这个老绅士严肃地想了想,然后说:“这不好,有一只猫待在这儿,没有人这样富有以至于派出这样一个人去捡垃圾。我不喜欢这样,如果我们的人也去英格兰做这样的事,你不认为英格兰国王会很快把他驱赶走吗?”这个老西班牙人,从他的职业上看,是属于受过教育的更加智慧的阶层,而这个雷纳斯两三年前在圣费尔南多的一座房子里留下了一些会变成蝴蝶的毛虫,由一个女孩喂养。毛虫谣言在这个城镇传开,最后牧师们和总督一起协商,认为这是很异端的,因此,当雷纳斯回去时,就被捕了。和我们一起沿普拉纳河而下的船长是一个老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待了很多年了。他承认他非常喜欢英国人,但他强烈坚持,特拉法戈尔之战,是西班牙收买的舰队舰长们获胜了,而唯一的勇敢行动也是西班牙海军将领所做的。这让我相当震惊,这个人希望他们的同胞被想成是最恶劣的背叛者,而宁愿不是技术不好或懦弱。
塔希提人
在塔希提,没有比和塔希提人在一起让我更高兴的了。他们神色温和,远离野蛮,也显现出正朝着文明方向迈进的迹象。普通人在工作的时候,上身基本赤裸,看起来像是很有优势一样。他们很高,肩很宽,身材匀称,像体育运动员一样。他们不需要任何准备,他们的皮肤,比起欧洲人的皮肤来,更能让欧洲人赏心悦目,这种特征相当突出。白人和塔希提人一道游泳,前者就像是一种作物被园艺师漂白了一样,而塔希提人则是很精致的黑绿色。大多数的塔希提人都会纹身,纹身沿着全身起伏的曲线会显得非常雅致,这就有了十分优雅的效果。
一些普通的纹身,虽然细节不同,有点像棕榈树掌。它从背部中心起纹,雅致地在左右背上起伏,许多老者会在他们的脚上纹上一些图形,就像袜子一样。这种流行元素,已经逐渐过时了。女人们和男人们一样,既在背上纹身,也在手上纹。从各个方面来说,她们的地位比男人低多了。在去山上的一次远足中,我们的目的地是希尔奥卢山谷,在那里,维纳斯山巅的河流倾泻入海。在几条溪流的汇合处的岸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平地野营过夜。塔希提人,几分钟之内就建立起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然后生火,煮我们的晚饭。
他们在一个树干的凹槽里,一直摩擦着一个钝头的树枝,他们的动作好像是为了把凹槽弄深,直到木屑燃起,我们也得到了光亮。一种特别的白而轻的木头就是为这种生火目的准备的。火在几秒钟内就着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种方法,那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但至少我成功地钻木取火了,我引以为豪。高卓人在潘帕斯草原用了不同的办法,找个有弹性的树枝,大约八英寸,用胸部顶住一头,另一头顶入树干洞里,然后迅速地转动拱起的树枝,就像木匠师傅使用转柄钻一样。
生起火来之后,塔希提人会捡几个板球一样大小的石头,放在点燃的树枝上;大约10分钟,树枝就烧光了,石头也变热了。他们早先就已经在树叶里包裹好了牛肉片、鱼、成熟或未成熟的香蕉和海芋头,把这些绿叶包放在两层滚烫的石头之间,然后在上层石头之上覆盖泥土,不让烟和蒸汽跑掉。在大约1小时零1刻钟之后,所有的食物都烧烤好了,非常香。现在把这些绿叶包放在香蕉叶上,用椰子果壳做杯子,饮用山泉,我们也就享受到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澳大利亚黑人
一群数量众多的土着,叫做白考克图人,当我们在乔治王海峡居住的时候,恰好前来访问。这些人,就像居住在海峡边的人一样,受到大米和糖的刺激,总想开狂欢会(或叫大派对)。当天变黑之后,他们开始使用一个盒子,用以把他们自己染上白点或白线。所有都齐备之后,大篝火开始发出亮光,妇女小孩围成一圈。
白考克图和乔治王岛的人举行的是不同的派对,一般来说,他们经常会在开派对时互相唱答。
他们的舞多种多样,或者侧跳;或者像印第安人一样列队,跑入一个空场地。与此同时,他们还会用力地跺脚。他们有力的脚步,伴随着一种咆哮,伴随着棍棒敲击,不仅一起摇头,同时也一起伸手臂,扭身子。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粗鲁的场景,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看到一个黑女人和孩子们却看得津津有味。也许这种舞最早的时候代表了一些行为,比如战争或取得胜利等。有种叫做食火鸟的舞,男人们像鸟的脖颈一样弯弯曲曲地伸出手来。另一种舞,男人模仿袋鼠吃树叶的样子,有时蜷起身子,假装要向袋鼠投梭镖。当两个部落混合在一起时,他们跳得连地面都抖动了起来。天空中回响着他们狂野的呼叫。每个人都高度亢奋,这群几乎裸露的人,在闪烁着的火光的照射之下,丑陋而和谐地移动着,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节日狂欢景象,就像其他的低等野蛮人一样。但是,我想,火地岛的人没这样亢奋,也没这样放松。在跳舞过后,所有的人绕成一圈,吃煮好的大米和糖,所有的人都欢欢喜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