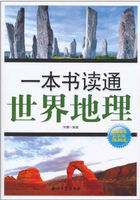“皮毛珍贵,可做衣帽,我这里配种养殖,幼鼠发育到3个月即可配种,生长快,繁殖力强。一年可生产二胎,每胎产6~14只,长春的养殖总公司负责收购。”
“本钱呢?”
“一对公母海狸獭我花100元购进,一年四季都可配种、分娩。平均每只生产10只,协议一只以40元收购,除去饲料开支,也能挣300块。”
我便问:“饲料喂什么呢?”
“这种动物很广泛,很随意,野菜里的蒲公英、芦苇、蒲草,蔬菜里的萝卜、白菜、菠菜,农作物里的玉米、白薯、马铃薯都行。特殊补助饲料可以用牛奶、豆浆。”
“如此说,我也能养海狸獭么?”
“毫无疑问,能养猪就能养海狸獭。”
前面出现了曙光,我的信心增强了,问:“路程太远了,我还得到东北购进么?”
“你想卖多少?”
“顶多三五对儿。”
“值不起呀,”吴天明说,“我这里购进了五十对儿海狸獭,大部分已经配种了,下个月就要生出小海狸獭了,估计陆续生产会有几百只。你拿去一对,先试验试验吧。”
不能这样简单,我问:“多少钱?”
“秋后算账,先赊着。”
吴天明有风度、有境界、有情谊,秋后才交钱,赊着账让我做实验。账是要还,我只怕欠款有利息,问:“秋后是不是100块钱?”
吴天明说:“挣了以后当然要还100块钱呀!插一句,如果生不下小海狸獭,我一分钱不要,算赠送。生了10只,收入400元,归你。”
天下掉馅饼,我要念阿弥陀佛了。
装车的是两名青年,场内雇佣的。我不认识,吴天明说,一个是妻子的侄女,一个是妹妹的儿子。
我问:“不是外人,都是亲戚呀!”
吴天明说:“同样每月给50元的工资。”
“为啥不从咱们村里雇人呢?”
“我有老观念。”吴天明说,“前几年,我们经常讲,社会上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雇用本村里的乡亲,我就怕人家认为雇用的都是被剥削者,我成了剥削者,说不清楚啊!”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哲学。印象是剥削者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垄断,无偿地占有没有和失去生产资料的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被剥削者没有生产资料,或只有少量生产资料,艰苦劳动的成果大部分或者全部被他人无偿占有的阶级。吴天明不简单,考虑周到。
我说:“今天讲剥削和压迫,我也说不清。”
“经过了多年教育,我知道剥削。”吴天明说,“按这个标准,容易区分。假如我是东家,来干活的就是长工,乡亲们来评价,我就是老地主了。
对亲戚关系的孩子们不见外,自拉自唱,没有闲言碎语。”
社会观念变化无穷,吴天明实行新旧杂糅。他统筹谋划,得心应手。如今不时兴上纲上线了,讲人人自由,不强求,不强迫,以人为本。
我的家里有了一对海狸獭,增添了风景。
贾贵福、贾子龙闻讯后,前来观赏,受到启发,说:“我们也该试验试验啊!”
吴天明的党组织关系还在村党支部,每月参加“党日”。我不是共产党员,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通过广才、老茂、美英等人的渗透和互相补充,生活会的情景大概如下:
贾广才说:“吴永强写了入党申请书,这孩子不错。思想解放,助人为乐,在县里的表彰会上还受到了奖励,够条件。我也可以当介绍人,下面大家议论议论。”
吴天明说:“应该慎重,永强还年轻呢。”
孙老茂说:“永强出身不好,确实要慎重。虽说不讲家庭成分了,但是不是受影响?”
王美英说:“不受影响。贾顺波前几天不是参军入伍了吗?原来家庭成分是富农,不受影响。”
“在承包责任制贴小字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广才不成熟’。”贾守保检查自己说,“今天广才提出永强申请入党的事,他的话有见识见解,我表示同意。先让永强当积极分子吧。”
吴小淑说:“永强引进了草莓,就是功劳。朝阳上周回家时就说过,广才是接班人,将来永强是不是接班人,值得考虑。”
大家各抒己见,党内的事,谁谁是否入党,我袖手旁观,视而不见,当做耳边风。接着,广才说到发家致富的话题:“天明五叔是老党员,办了养殖海狸獭基地,是致富新方向。以身作则,也要带动村民。”
“嘿,我咋带动呢?”吴天明说,“我不当村干部了,领导不了别人。”
贾广才说:“党支部也领导不了咋致富,从宗旨上说,我们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遇事同群众商量,带领广大群众前进。”
“五叔有什么想法?”吴小淑问。
“贵福和子龙找过我,也想养殖海狸獭。”吴天明说,“我准备带他们到长春跑一趟,看看效果。”
孙老茂说:“你们当个领头羊,我也想跟着跑啊!不巧无本难取利,我拿100块钱手也紧。”
王美英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说:“我家买得起海狸獭,资金不是问题。
平时红卫不爱种地,我看让他养殖海狸獭也许闯荡闯荡。”
“我不想养殖海狸獭,”贾守保说,“想在责任田里栽果树。上学的时候,我学过课文《狐狸和葡萄》。狐狸已经两天没有找到食物了,它又饿又渴。忽然,它看见远处院子里的架子上挂满了一串串的葡萄,于是它急忙跑过去,只见又圆又大的葡萄挂满了架子。狐狸迫不及待地跳起来用爪子去抓,可是架子太高怎么抓也抓不到。海狸獭与狐狸差不多,我怕上当。”
庄稼人有庄稼人的策略,这是泄气的话,不赞成养殖海狸獭。贾广才说:
“我们的生活会,要少说多干。我有个想法,为了支持这个举动,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捐款,负责运输费。”
显然,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吴天明说:“我五十多岁了,也被气氛感染了,党籍入了四十多年,我没有什么贡献。如今挣了一些钱,剩下干什么?
干脆,我拿出一千块钱,解决运输费和购进费。”
有钱真牛啊!一跺脚,颤三颤,吴天明震动了搓绳寨。吹皱一池春水,泛起波浪涟漪,发家致富终于有了门路,前景灿烂辉煌!
海狸獭来了么?
我也难以预料,需要主动到长春购进。谁去?吴天明挑选我和红卫同去。
其中的缘故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说清楚。自己琢磨,也许我曾出过远门到海南岛育种,有行程经验;红卫年轻,机警灵活,万一遇上坏人便能一显身手。要不,为什么贵福和子龙或老茂不能偕行呢?
我们风尘仆仆,傍晚到了长春,住宿在旅馆。吃罢饭,我和天明、红卫在光复北路大街溜达,逛逛大都市。
我们看到了一座建筑,门口的牌子,写着“伪满皇宫博物院”。红卫说:
“我们进去看看啊!”我摇头说:“不能随便,要买票呢。”天明五叔听了一人一句话,毕竟他是主人公,就说:“买票怕啥?我们看不到北京故宫,有机会去看看这伪满皇宫。”
进入博物院,讲解员介绍: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皇宫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居住的宫殿,溥仪用于办公、处理政务、举行大典有勤民楼和同德殿;用于供奉列祖列宗的有怀远楼;用于举行大行宴会的有嘉乐殿、清宴堂;另有书画楼、中膳房、洋膳房、御花园、假山、防空洞、游泳池。另外,溥仪一共有五个夫人,第一位就是“皇后”,叫婉容,达斡尔族人;第二位是“淑妃”,叫文绣;第三位是“祥贵人”,姓他他拉氏,后来改为姓谭名玉龄;第四位“福夫人”,叫李玉琴;第五位是1962年结婚的,名字叫李淑贤。
人们大都讲势利,旧社会傀儡皇帝比老百姓强,一生娶了五个妻子,新社会特赦释放也比老百姓强。
参观后走回旅馆路上,红卫说:“看了几所房子,没意思。知道这样,我不如在这儿练练瞄准呢。”
吴天明说:“你去打几枪,我和永文在旁边看看。”
原来,街上有游戏,是用气枪打气球,瞄准击破。在五分钟时间,十个气球全部消灭的话,不花钱。如果剩下一个气球击不中,花一毛钱,剩下两个气球击不中,花两毛钱。
红卫打了10枪,只有一个气球没有击中,九个都“嘭”了一声,仅仅花了一毛钱。他很得意,说:“我小时候用弹弓打麻雀,是高手。有了战斗机会,我还能当解放军神枪手呢。”
回到了旅馆,自然歇息。在家里睡得是土炕,舒服又安稳。旅馆里竟然是弹簧床,被压得松松软软,身体难以得到有效支撑,睡不着觉。
失眠了,我想到了溥仪。旧社会太黑暗了,三岁的孩子坐上龙椅,全国人民不得不叫他是“万岁”。被打倒了,他竟跑到东北当满洲国皇帝,卖国求荣,效忠日本,当了汉奸,占了这么多楼,这么多殿,有权有势啊!抗日战争胜利了,楼殿怎么不拆毁啊!是不是当做证据,控诉教育这小子为虎作伥的罪恶?逮住了他,应该千刀万剐,多亏共产党宽大,将他特赦了。
关于“特赦”,我查了字典,“特赦”的含义是对某些犯罪或者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罚的措施。李淑贤的职业是护士,怎么嫁给他呀?据说,那年溥仪是56岁,李淑贤是37岁,相差19岁。况且溥仪生理性无能,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我总不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孙老茂至今还打着光棍,难道不如溥仪么?
哦,溥仪曾经当过皇帝,老茂仍然是老百姓。问题出现了,如何对待?
老茂如果当个村长、镇长,没有李淑贤,也有张淑贤、刘淑贤、王淑贤、赵淑贤,即使不叫淑贤,如我的妻子一般叫秀丽,也同样有张秀丽、刘秀丽、王秀丽、赵秀丽。人的待遇不分好坏,只分高低,大概这就是标准。
胡思乱想,一个闪念又出现了。
闪念来自源头,因为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里,我看到有一座青石,上面由江泽民主席题写了“勿忘‘九·一八’”几个字。对我来说,“九·一八”
勿忘不勿忘,无关大局,一生中缠绕的是“勿忘六·一四”,那是1945年农历五月初五,阳历6月14日我的诞辰。溥仪与日本有关系,我与日本也有关系。开明宗义,既然我承认了自己是野种,自然感慨良多了。
祖国是母亲,东条英机侵略了中国,森木太郎奸污了我的母亲。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于绞刑,森木太郎却来访问看望。我有了疑问,结论怎么解释,尚没有人说过。我到底有了污点还是有了荣光?
清早起来,我们踏上了返程。
半路上,肚子饿了,在名叫望夫石村的城镇用餐,我们还到孟姜女庙看了看。走了108级石阶,殿门前的柱上有一副楹联,写的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我觉得意思是“海水”天天早晨出现,最后落下去;“浮云”经常出现,最后消失了。有人解释,读法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
原本很简单,却变得复杂曲折,“朝”是“潮”,“长”也是“涨”,混淆了。
谁相信?
老百姓用不上咬文嚼字,回到家乡,首先是分派海狸獭。谁家分几对,事先预订了,少的有五对儿,多的有二十对儿。自愿养殖海狸獭的有五十多户,购进了280对儿。我预定的是十对儿,二十只海狸獭不多不少,算中流。
原定红卫家也是预订十对儿,忽然有了麻烦。因为贾朝阳升任县政府副县长,小淑和红卫可以“农转非”。农转非就是由农业粮转成商品粮。两天之间,就有了这种政策,红卫当然不能养殖海狸獭了。办好手续后,小淑的职业从湾子乡卫生院到县医院当护士,红卫到工商管理局当临时工,负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行为的服务和监督管理。
家家都在变,人人都在变,不足为怪。
红卫的机遇让人羡慕,有利无害。贾朝阳是男子大丈夫,媳妇和孩子沾了光。
秀丽知道了,感慨说:“人的命,天注定,想比也比不了,你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
我苦笑着说:“依我说,老百姓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呢。”
“啥字?”
“加个小——小老百姓。”
“是啊,老百姓确实是小老百姓,不是大老百姓。无权无势,不挨饿受冻了。好听的是说国家的主人,那是戴高帽子呢。”
我说:“主人的主,去掉上面的点儿才好。正着写是王,倒着写也是王。
九叔天佑曾经说过,董仲舒评价,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
“九叔还是有文化,你多向他请教请教。”
“我知道,蜜蜂里有蜂王,扑克中还有王牌呢。”
秀丽说:“蜜蜂是嗡嗡叫,玩扑克是消磨时光,我该做饭了,你也该去喂海狸獭了。”
32.韭菜三结合
吃完早饭后,我没有书看,窗台上有一本《新华字典》。这是大亮用过的,念书时的学习工具,被抛弃了。
家里养殖了海狸獭,我便翻了翻,查一下“獭”字的解释。
写法的模样与“癞”差不多,“癞”读作“lai”,“獭”读作“ta”,为啥癞蛤蟆不叫獭蛤蟆呢?
思忖间,秀丽说:“我泡上豆子了,上午磨懒豆腐。敬儒二婶家有小磨子,我搬不动,你去借来。”
小磨子是磨懒豆腐的工具,摆在簸箕里,用手转动,豆子变为豆浆。
我问:“大亮干啥去了?”意思是让大亮去搬小磨子。
“又去打台球了呗!”
“小伙子光玩儿,不像话。”
“像话了该咋的?地里的庄稼耪了,让他干啥?学了数理化,不如好爸爸,人家红卫上班了。”
秀丽的话是现实,我不如贾朝阳。好坏不是空话,在于孩子的前途。我说:“不是学了数理化,不如好爸爸,而是学得胆子大,当了企业家。”
秀丽说:“别辩论了,小磨子不长翅膀,飞不到家里。”
我沉默了。
把握时机决定了成败。贾敬儒如果不逃到台湾,便会穷困潦倒,受到批判。改革开放踏进国门,待遇有了根本变化。贾敬儒跑到台湾岛是经历的造就,他办了手续,从台湾移居到了搓绳寨。甄寡妇不是寡妇了,应该改叫富婆。令人高看一眼,顶天立地,撑起了门户。不过,人们背后仍然叫甄寡妇,当面显得尊重又客气,脸上多了笑容,换来甄氏的微笑。
我出门走到大街上,想到了海狸獭、癞蛤蟆,秀丽又说到懒豆腐。唉,中国文字太复杂。獭、癞和懒,都离不开赖。干脆都是赖,也说得通。海狸赖,意思不是依靠在海里的;赖蛤蟆,意思不是青蛙;赖豆腐,意思是不用卤水,不是真正的豆腐。
走进贾敬儒的院子,贾敬儒正在拿着大扫帚扫院子。我说:“二叔,喜欢干净啊!”
“《朱子家训》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我家里要磨懒豆腐,使使小磨子。”
“在墙角呢。”贾敬儒说,“永文,坐会儿吧。你看,墙上标语上有一个简化字,我还不认识。”
标语是前几年写的,“不怕牺牲”的“牺牲”,写成一个“西生”,我说:
“这是1977年的简化字,是‘牺牲’,‘西生’这样的写法已经废止了。”
贾敬儒说:“繁体和简化各有利弊,简化字省事,台湾仍然是繁体字,台湾都是繁体,写成‘台湾’,太麻烦了。”
我问:“二叔,你在台湾住在啥县?”
“桃园县。”
我说:“这名字好,谁都知道桃园,歌曲里还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呢。我们的独莫县名字别扭。”
贾敬儒说:“有点别扭。历史形成的,说起来也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叫独莫吗?”
我摇摇头。
“据说,独莫是契丹的一位将军,占领了此地,修了独莫城,民国年间才有了独莫县。”贾敬儒说。
我问:“‘独’的意思我知道,独具慧眼。可是,那个‘莫’呢?含义是没有、不要,怎么用这个字?”
贾敬儒果然知识渊博,解释道:“独莫,不是汉语,那是契丹语的音译。
对少数民族的名字都是音译,成吉思汗、班禅额尔德尼也是音译。”
我频频点头,不服不行。
二婶甄氏插话说:“我也认识几个字,我知道,人民币上还写了‘中国人民很行’呢。”
人民币有一元,五元,十元,上面注明有“中国人民银行”,怎么叫“很行”呢?“银行”怎么读作“很行”?
我叹了口气,说:“二婶文化太低了。”
甄氏说:“中国人民当然很行,毛主席说过,人们站起来了。上面有了‘很’,有了‘行’,我认识。”
我终于明白了,“银”和“很”相似,“行”有两种读法。甄氏二婶虽然认字了,却理解错了。
我说:“不是很行,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机构之一,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贾敬儒说:“嘿嘿,你二婶没有文化,惹出笑话了。文字的复杂,‘银行’和‘很行’就是验证。”
甄氏却不服气,反而说:“不叫银行,即使叫很行也中。人民当家做主了,钱叫人民币,当然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