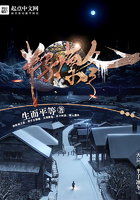风逍依旧过着早出晚归偶尔抽出时间处理公文的日子,他喜欢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逛一逛,也喜欢坐在酒楼茶坊里听一些江湖游侠指点江山,他不逛画舫,不喜赌博没有狐朋狗友,没有纨绔作风,他总是很安静,在众人眼中语气说他是天赋卓绝家世显赫的世家子,还不如说是秉圣人礼仪的柔弱书生。有人轻叹,风家后继无人啊!或许在他们心中,他的低调安静与那些遛狗斗鸡胡作非为争勇斗狠纨绔比,是一种无能呢!你可以不是个好人,但你不能不会武功;你可以不会吵架,但你不能不会动手,百姓眼里,风公子的为人太过柔弱了。
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稍稍改变了城里百姓对这位郡守公子的看法,风公子在这件事上展露的果决与狠辣让一些城里的公子哥好几天不敢出门,证明了风公子不是个空有天赋不会武功的软蛋,而且他还让百姓们心里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天气晴好,风和日丽,对一帮公子哥来说,此时文能调戏良家妇女,武可以外出打猎踏青。钱三元钱公子在一帮公子哥当中也是响当当的一二号人物,他当然要担得起他的名头,一大清早,太阳还没升到头顶,他纠结了一干恶奴护卫,赶着马走出了大门。当时街上人不多,钱公子心情又急切,于是马速就稍快了点。钱公子一个没留神,险些撞飞一个挑着担的老人,那时马人立而起,坚硬犹如铁铸的马蹄就从老头头顶划过。
钱公子一个漂亮的‘身轻如燕’翻身落马,老头被吓倒在地,好半天没回过神。钱公子也不是那种无恶不作的恶霸,他暗骂了声晦气就上马准备离开。
要说这事也不过是个小事,偌大的泗北城,像这样的场面太多太多了,就是运道差了被一蹄子踩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哎!怪就怪在那时风公子正坐在临街的窗边,他看到这一幕,也不多说,翻身下了楼,立在大街,硬生生地用手挡住了已经在狂奔的马儿。啧,那马浑身皮毛乌黑乌黑的,又高又壮,跟小山似的,而风公子又那么单薄,可就是一步未退地用一只手,只用一只手啊把马拦下了。那马估计是废了,接着风公子只是手一伸再一缩就将愣怔的钱公子拽下马来,单手拎着他,一步一摇地将他拎到了郡守府,钱家的那些都是个恶奴痞子,遇到个娘儿们敢上去扒衣服,遇到比钱公子还厉害的风公子哪敢管,不自觉地让开了条道。
“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穷酸老头穿着穷酸衣服,一手捋着稀疏胡子,一手一拍惊堂木,洋洋得意如是说道。
不过小小说书先生手只有缚鸡之力是没有话语权的,几把白花花的片刀一亮,他正义凛然接着道:“那风公子将他一步一步地拎到了郡守府,大家也都知道,那郡守府差不离是个空房子,风公子也没换人,将钱公子扔到大街上,自己从衙门里拿出了一跟杀威棒,二话不说打了他三十班。我的天,那场面,那声音,老头子是一生难忘啊。”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没有欢呼,没有叫好,人群很快散去。老头子难得慷慨一回,没有收钱,只用手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眶。他们都没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在这样的世道里,他们太容易感动。
他默默收起了自己的吃饭家伙,浑没觉得他故事里的主人公正在他故事里的主人公就在他们头顶处喝着女儿红。桌子上咕噜噜落上了几枚铜钱,抬头一看,刚才亮刀的几个煞星的背影消失在街道上的人群里。
时间就是这样平淡的过去,风公子的做法只能算是一抹清凉的风,轻轻一带就过去了,他们或许偶尔还会咀嚼一下,但他们还是在这样的世道里生活:要拼命赚钱,要不然会被赶出城去;要拼命练武,要不然会被别人笑话,再被人打得满头包;要远离那些公子哥儿,他们打死你只要赔点钱,划不来;要小心翼翼,也要有武夫血性;要敢怒目金刚,大多数时也要女儿低眉……压抑,欢心,痛苦,喜乐,人间芳菲掺血。
景元历八月十八,平平无奇的一天,需要做活的一天,可以纵马奔腾嬉戏玩闹的一天。本来是这样,但太阳突然蒙上了乌云。
正午时分,烈日炎炎,天地似乎变得白茫茫一片,不能见物。街道上少见人踪,只有丝丝缕缕无穷尽也的扭曲热浪不断从地面上升起,犹如群魔乱舞。
推着酒车的老张艳羡地看了看那些或朱红或镀银的大门,对旁边和他干同一行当的老王说道:“这鬼天气真真他娘的见了阎王,我真想砸了这车好回家冲个凉水澡。”
“得了呗你嗨,你也就敢嘴里说说呐,你以为你是那些不用交租交税的老爷啊,房钱一旦三月没还你老就去喝你那凉水去吧,管你喝个饱……哎,我说老张,你那儿子是在广晟吧?那可得花不少银子。”
老张矜持地把他的老脸笑成了花,“唉唉唉,我那宝贝儿子也忒不争气,怎么就考进去了呢!害得我这老头赔着命去养他上学。”
老王还不知道他的性子,赶忙打断他的嘚瑟:“呦呦呦,还喘上了,信不信我把这话给你儿子说道说道,他立马辍了学来挑扁担。”
“你敢!”老张浓眉倒竖,一股悍勇之气跟着升腾而起,老王耸了耸肩,嗤笑着撇嘴。不久也叹道:“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平,那些世家老爷们啥都不干,也不用交税,白拿着郡里的银子,不愁吃喝,还练着上品武功……他们不就是老祖宗捞到了个爵位么,都不知道去他爷爷的多少年以前的伯爵子爵了!我们起早贪黑,拼命练武,也没有武功秘籍,到了也只能混着给他们打杂看门,当个护院或是有品家丁也得有点门路,还得看别人脸色。受不了鸟气出来混也就像我们两这样,大热天看有没有那些短命的赶路鬼买点酒弄点酒钱。我是看出来啦,老天爷是不公平的,那些老爷太太是老天爷大房生的,我们唉,就是那老天爷逛窑子时弄出来的杂种。呸!”
老张有几分书生气的眼睛眯了眯,抬头看了看太阳,喃喃自语:“天再热也会黑的~”突然,大地毫无征兆地震颤起来,老王一个愣神没把住把,将车翻了翻,顿时撒了半坛酒,他是又惊又怒,牙齿咬了又咬,虎目眨了眨溢满了泪。
老张站着不动感应一番,说道:“不是地震。”看到老王流了泪,他叹了口气,没去安慰,他拿什么安慰?
老王将车停好,绕过车趴在地上细细地吮吸洒落下来的酒,知道满嘴都是沙子才罢休。“呸呸呸”他边走边把嘴里的的沙子吐出来,一双眼睛又像刚才一样精神四溢带着痞性。
从极远处传来的震动虽然轻微并且和从地底深处传来的有所不同,但还是吓到了一些人。紧闭的深宅大院传出一阵阵惊呼和叫喊,老王快意地笑了。情绪是会蔓延的,恐慌更是如此,那些惊叫声眨眼间变成了轰轰声,随后更是变成像海潮扑打礁石的炸鸣,接着第一间大门开了,睡午觉的老爷太太也没顾上礼仪住在轿子里,衣冠不整地慌忙冲了出来。
一间间大门洞开,各色人物鱼贯而出,没有大乱时寻常百姓是不知道那一扇朱红大门里藏了多少山川,现在‘地震’一来,乖乖,那红的绿的公子小姐,白的青的各色小厮,美的艳的夫人妾婢真撩花了他们的眼!从天上看,街道两侧一条条河流潺潺流出,在街上搅成一个个小的漩涡,漩涡两两相连,变成大的漩涡,最后几十米宽的大街轰隆隆乱成一片。
人挨人人挤人,你哭我吵,全然没有想到如果真的是地震的话,也早该结束了。街道尽头升起了一面大红三角旗,一声“报
”字如春雷炸响,吵闹顿时平息,“急报!”‘河流’如被一枝树枝划过,一条缝隙从街头往街尾平移,缝隙中央一身穿青马褂的令兵,一手高举令旗,一手急抖马缰,骑着乌红俊马急速冲向风府,口中大喊:“急报,城门外出现大股军队!”
老张老王好不容易把车推到街边,正抹着汗,闻得此言老王咧着大嘴,露出两排大黄门牙,老张表现和一般凡夫俗子并无二致,大惊失色。好些女人才刚站稳,有的正拿着手帕擦着已称不上是香汗的腥液,有的拿着纸扇往脸上往往脖子上招呼,甚至把胸襟不经意地往外提了提,然后对着里面可劲摇两下,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她们脸变得比雪还白。
慌乱中女人有种强烈的惯性,如果此时有人尖叫出来那说不定这股声浪能吓外面的敌人一吓,而此时城池里的人恰恰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所以女人们也都紧闭着双嘴。由极热闹瞬间变得寂静而产生的巨大落差让气氛又多了点压抑。
人群不约而同地盯向风府,虽然强势无比的风将军走了,但他们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那个冷酷的身影曾经带给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对希望寄于他人的感觉感到羞耻,却还是难以避免。没有人出来,一阵阵鼓声“咚、咚”地响了起来。鼓声低沉,远远激荡开来。
“破军鼓!”
“是破军鼓。”
“点将台,破军鼓。这是全城军士集结令!”
“唔,太严重了吧!”
“一定可以打赢的。”
“风将军不在,可以打赢么?”
在城外巡视的,在城内巡逻的,在沙场操练的,执行公务拘拿犯人的……士兵与将领从四面八方赶去风府,然后像巨兽吞了小鱼被风府吞了进去,无影无踪。
日头正高,在士兵集结最初的兴奋过后,看到半晌没有动静,城里百姓再次焦急起来,人们苦苦地忍耐着,但焦灼的天气与人一样是在燃烧的,用度秒如年来形容他们的心理却一点也不为过。
终于在他们一致认为是他们忍耐的极限点时(之前有很多次),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风府轰隆隆压向众人,那声音是“是”!紧接着就是士兵涌出风府的整齐的脚步声。起先是举着枪的士兵,那银光闪烁的枪林与泛着幽光的兵甲给人强烈的感官冲击,每四人一列,有人数了数,约莫三千人。接着是骑兵,坐骑清一色红发乌蹄脖颈上长着鳞片的鳞马,士兵手持红绫长矛、身披黑色重甲,威严厚重。鳞马最初是蛟与马的杂种,后来由专人配种,适合行军作战,大约一千骑。最后是身穿各色衙役服装的士兵,他们人数最少,只有三百人,而且他们的队伍虽然整齐却显得散漫,但百姓无人敢小瞧他们,他们是风将军从江湖中笼络的武林高手,最差劲的也是二流好手。百姓们对这些事知道的门清,领头的几个穿着红衣戴黑帽插三羽的捕头是一流高手,后面穿着绿衣戴黑帽插一羽的是二流好手,至于三流好手要么在前面的行军中,要么还在风府打杂嘞。
拥挤不堪的人群随着士兵们全部离开后变得更加拥挤,他们要跟着他们出去看看,虽然不能出城门,但离着近一点也是好的。也有些比较聪明的,就跑到有十一层的揽雀楼去了,在那里,将将可以看到城外停留的那一波无边无际的黑潮。其实揽雀楼十一楼已经被几人包了下来,不过一根筋的百姓们听到他们的名头也没有跟他们吵,因为他们是天机阁的,城里的人丢了鸡鸭鹅可以找他们,被偷了万两白银可以找他们,算姻缘可以找他们,买凶杀人他们同样来者不拒,代价只是答应替他们办一件力所能及自己也愿意的事。没有人知道他们建立这个势力的目的是什么,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只知道大图太祖打江山时曾与天机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真正让他们甘心退下去的原因不是这个,开玩笑,在泗北城有个风府谁能一手遮天,而是楼上的几个答应了免费替他们报道战争实况。说实话,要让他们看打仗他们大多数是看不懂的,由别人看说不定还能顺带讲解何乐而不为呢?
中年人盘膝坐在虚空上,一手支着下巴,一手拿着酒坛,看着身下的两军对垒,李不闻在揽雀楼十一层,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与世故获得了为坐在椅子上单薄的书生模样的人研磨的资格。李不闻其实心里是很惊讶的,因为揽雀楼除了书生还有好几个凭自己的多年的眼力判断出属于那种岳峙渊渟深不可测的厉害人物,可他们却心甘情地分列四周站着。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天机阁规矩的森严,一方面也能看出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的不凡。
风逍站在藏书阁楼顶,泗北城只有风府十二层的藏书阁高于揽雀楼,不过,风逍站在这是看不见城外的,他也没打算望城外,他坐在桌子前,陪自家叔叔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