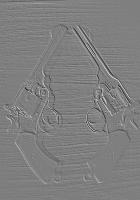不甘寂寞的陈独秀,出狱后仍想再干一番事业,然而,命运之神好像专门同他作对似的。他从南京到武汉后,北大学生、国民政府教育次长段锡明、陈钟凡向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推荐他去教书,而王抚五又是他的好友,当即应允欢迎他去武大任教,他拒绝了,并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建议他去美国。他也拒绝了,他说:
“鄙人决不去美国。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像我这样的人物,国民党正式批准让其出国赴美,成功机会绝对没有的。”
托派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摆脱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愿意。他说: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这个身份。”
一条又一条出路被他堵塞之后,他不禁万分感叹,问苍茫大地,出路何在……
时局发展到1938年下半年,日军日益逼近武汉,形势十分险恶,日机轮番轰炸武汉三镇,造成一片惨景。
陈独秀正好住在武昌被炸区附近,每次轰炸,他和夫人潘兰珍就像在南京监狱时一样,老夫少妻紧抱着躲在客厅方桌之下。空袭之后,他目睹日机屠杀中国人民之惨状,怒火中烧。日本飞机、炸弹炸掉了他们这对老夫少妻庭院的平静生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从武汉又迁都重庆,随之大批难民又蜂涌重庆。此时,陈独秀的故乡安庆,亦已沦陷,他的养母谢氏及其三子陈松年一家,已先行入川避难。武汉告危,战火燃至眉头,他不得不改变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时邀他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文字学的主意。他在致贺松生的信中说:
“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
陈独秀四海为家,浪迹人间,多年的政治生涯从工作以至衣食住行,大都是由党的组织给予安排和照顾。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均无须他为衣食住行操劳,有吃有住有车坐,还有秘书为他服务。然而,他离开了党的组织,就如同断了脊梁骨。1927年他潜回上海后,秘书黄文容离开他到郑超麟部下工作去了,中央再没给他派秘书。身边少了秘书这根拐杖,他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没人张罗吃饭,他就饥一顿饱一顿;没人催他换衣,他就不换,衣服穿得既脏又臭,也不知道脱下洗洗。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自己糟践得胡子拉碴,蓬头垢面,让当年西服革履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现在一切事无巨细都得自己过问料理,许多事都还得靠朋友帮助解决,离开了朋友,寸步难行。他的夫人潘兰珍缺乏主见,一切都听从他的,对于她来说,精心照料陈独秀乃是她的天职,她对陈独秀可说是无限忠诚,默默奉献,无一点怨言。陈独秀几经人间沧桑之后,对“决计入川”思前想后,慎之又慎,并再三征询友人的意见。
一天,他应邀参加一次宴会,适逢当年支持国共合作的民主人士章伯钧、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等在场。故友相见,难免寒暄一番。席间章伯钧问陈独秀:
“仲甫先生,你积极宣传抗日,各界人士欢迎。当前武汉形势恶化,不知仲甫先生有何打算?”
“伯钧先生,积极宣传抗日,乃是鄙人应尽的微薄之力,也是一个中国人应做的事。鉴于武汉之形势,鄙人决计入川去重庆,在抗战大后方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伯钧和钦岳先生,你们看怎么样?更望能得旧友的支持和帮助,重庆那儿人生地不熟。”
“钦岳先生,仲甫入川,你看怎么样?”章伯钧问周钦岳。
“仲甫先生入川,鄙人表示欢迎。”
“仲甫先生入川,请钦岳先生多方关照。”
“鄙人一定关照,吃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鄙人可以负责。明日鄙人回川,都作安排,届时望仲甫先生电告行期,以便迎接。”
“谢谢!承蒙关照。”
“不过,有一点我想提请仲甫先生注意。”
“什么?请直说。”
“陪都重庆,各方要员都聚集在那里。希望仲甫先生入川,要多加小心,不要从事政治性的活动或发表政治性的文章,安心休养、治病,做你的学问就是了,免生是非。”周钦岳说。
“我不反对各方就是了。”
这样,陈独秀在朋友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才于7月初,携夫人潘兰珍,告别生活将近一年的武汉,搭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包的专轮入川了。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的罗汉,也随船而行。
这艘轮船由于是四大银行包船,沿途码头不停靠。虽是逆水行舟,但比其他客轮航速快得多,不日就停泊在朝天门码头了。早已迎候在码头的《新蜀报》、《新民报》的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张彗剑以及好友、黄埔军校政治教员高语罕等,登船迎接陈独秀及其夫人潘兰珍,并请他们夫妇乘上迎候在那里的汽车,绕道山路,在上石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前停下。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他们夫妇寓居在楼上。次日晚,朋友们设宴为他们夫妇洗尘,陈独秀对朋友的热情款待甚为感激。
重庆对于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有很多不适应,尤其是那七月的酷暑闷热,更令他难忍,对病体不利。加之夫人热得中暑多日,他心中更觉不安。日本飞机连连空袭,四处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大后方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再加上陪都重庆,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表示以抗日为重,不反对蒋介石,但国民党对他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感到非常沮丧。
一天,他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去医院看病,沿途碰到几个盯梢的便衣特务。气得他连病也不看了,半途返回。躺在床上犹气愤不已。他痛彻肺腑地感到重庆的环境还不如武汉,真想插翅飞离山城。可是,眼下举目无亲,又寻找不到适合的地方居住,到哪儿去呢?这乱哄哄的时代,哪有他立足之地!每每想到这些,他总是连连叹息……他甚至认为,还是蹲在监狱好,不愁吃喝住,也无须到处飘泊不定。
正当陈独秀在山城不知何去何从,焦急不安,一筹莫展之时,一天,他突然意外地接到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皖白山人邓石如后人邓仲纯先生寄自江津县的来信。
他拆开信一看,字里行间充满了友谊、同情。信中写道:
仲甫兄:
欣悉你己提前出狱,并于日前来渝,鄙人及家弟季宣为你祝贺!
当前,国难当头,日本猖獗,江津毗邻陪都重庆,在此避难的安徽同乡很多。你我都是同窗好友,同时已有多年未见。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女士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待抗战胜利,我们同返故乡。我们盼等你及嫂夫人的到来。
陈独秀对形影难离的潘兰珍,平日少言寡语,大多的时候板着面孔,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而潘兰珍却一味夫唱妇随,她懂得老先生做事稳重,三思而后行,她只是个妇道人家,哪懂得世面上那些事。同时,她这些年来跟随陈独秀辗转飘流,多少也见过些世面,也接触了不少社会名流,她越来越感到老先生是个神秘而名气很大的人物,他到哪儿,哪儿都有朋友帮助他,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这样,她内心深处越来越崇敬老先生,对老先生的情爱,也越来越笃深。陈独秀看去俨然像个老夫子,其实内心在这选择新的生活去向之际,他十分尊重她,对她有着深深的爱。他带着征询的口气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邓仲纯先生邀请我们去江津,那儿安徽同乡人很多,你说江津去不去?”
“老先生,阿拉父母早已去世,家里已没人了。阿拉自嫁罢侬,就与侬相依为命,同生死。既然侬问阿拉,阿拉当然要说说阿拉的想法了。”潘兰珍深情地说。
“兰珍,快说,你的想法怎样?”陈独秀迫不及待地问。
“据阿拉看法,既然侬的好友邓先生一番好心相邀,目前国难之时,无处可去,重庆这个地方侬又不习惯,去江津避难,也是蛮好嘛。”
“兰珍,你说得对,同我的想法一样。就这样定了,你看行吗?”
“老先生,侬已拿定了主意,何必还问阿拉?”
1938年8月3日,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夫少妻,终于告别那日子实在难熬的山城重庆,再度溯江而上,乘上自重庆到江津的“民惠”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