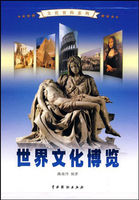到了宋元时期,壮族论理道德开始出现系统化趋势,从而为后来壮族传统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出现了一些壮族伦理道德的经典。比如,大约形成和完善于宋元的《布洛陀经诗》作为壮族的“百科全书”,也较能体现壮族伦理道德的系统化特征。而流传于红河水流域的《盘同古》,乃是壮民在婚宴夜晚唱的歌,其主要内容就是“借用婚筵向亲朋好友,尤其是青年后生,讲述壮族祖先盘和古再造人类的故事和婚姻的来由,教育青年人要珍惜婚姻之幸福。”[19]其二,出现了一些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文人士人。唐宋时期,壮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不少地方设立了府、州、县学乃至书院,一些富家子弟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撰写或留下了不少文章,使我们今天能对当时的壮族思想窥见一斑。比如,唐代中期的韦敬办、北宋时的冯京等都是他们的代表。到明清时期,经过改土归流后的壮族地区,在伦理道德与中原进一步接轨,尤其产生了被称为壮族“道德经”的《传扬歌》。《传扬歌》在壮话中叫“FwenCienz。Yiengz”,它用质朴的民歌语言唱说了壮族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从社会到家庭各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长期以来,壮族人民广泛传唱《传扬歌》,以它作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作为人们处世的准则和评理断事的依据。《传扬歌》是壮族伦理道德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和结晶。历史进入近现代,壮族地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传统道德规范,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政治等方面。此时,壮族文人学者的数量和水平也有了新突破,他们不少人着书立说,阐释自己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甚至出现像黄朝桐《我的道德观》这样的专着。
以上就是壮族伦理道德的发展简史。应该说,壮族伦理道德的演变轨迹,也是男女关系及社会地位沉浮变化的过程。在壮族伦理道德由无到有的过程中,以布洛陀和姆六甲为代表的男女两性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壮族伦理道德所要调整的对象,有女性的也有男性,甚至以男性居多,比如对“好相攻击”恶习的制止等。随着阶级社会和剥削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壮族论理道德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更多地变成了男性,而它们所调整的对象也更多地是女性,那些直接涉及女性的专门道德更是如此。比如,经诗《解婆媳冤经》所要叙述的,就是“先前媳妇妖,过去媳妇浪”问题。当然,壮族是一个女性文化比较突出的民族,即使在总体上不利于女性的伦理道德发展时期,类似韦敬办“庶男杰壮,妙女更极”的思想也还是相当多的。到了近现代,壮族论理道德中体现男女平等的意蕴就越来越多了,如吴凌云的“男女平等,共享太平”,左右江革命时期的“男女共受教育”等。
二、壮族道德规范与两性义务对等
伦理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规范,是对人们之间应尽义务的一种规定。从性别关系来说,一种伦理道德如果对男女双方规定了相同或相似的义务,那就体现了平等原则,否则就是不平等的。壮族有着较为突出的女性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着较多男女相同或相似的规定。
壮族是一个崇尚勤劳节俭的民族。因为壮族是稻作民族,稻作的复杂性决定着不论男女都必须努力参与劳动。比如,《传扬歌》认为,勤劳是最重要的美德:“说千言万语,勤劳是头条”。因为“勤劳是泉水,长流不枯竭”,“持家靠勤俭,兴家靠勤劳”。即人们要学会做人,就要从勤劳做起;无论男女,只有勤劳才能得到人们的敬重。《传扬歌》还说:“每天懒洋洋,嘴巴比人馋,田里长野草,何处收新粮?”联系壮族社会“男逸女劳”的角色分工习惯,这里所指责的应主要是男性。而壮族女性由于“忙里忙外”,所以经常得到各方面的赞赏。比如,清初的刘新翰在《澄江劝农口号》描述到:“叱牛分秧去复回,绿蓑青笠绕江炜。长官亦是农家子,一见良苗开口笑。”这就表现出对男女劳动者的高度赞赏。很多壮族山歌也经常作出这样的倡导,比如:“妹妹爱我爱她,妹妹爱我会种地,我爱妹妹会纺纱。”而雍正时期的农赓尧在《村女赤脚行》、《山行口号》中,成功地塑造了热情、乐观、纯真的壮族劳动妇女形象;在《百鸟衣》、《达旺节》、《一幅壮锦》等众多民间故事中,妇女也是以勤劳、能干的形象出现的。当然,节俭与勤劳是相辅相成的,《传扬歌》有云:“夫妻一条心,勤俭持家忙,苦藤结甜果,家贫变小康”。可见,这是对男女的共同期待与要求。
壮族是一个崇尚顽强勇敢的民族。岭南恶劣的自然环境赋予壮族先民以顽强勇敢、富于抗争的民族精神和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在民间故事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一是与毒蛇猛兽做斗争的故事,比如《杀蟒哥》、《石良》、《水珠》等。在远古时期,岭南众多的毒蛇猛兽构成最大的威胁,因此人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奋起抵抗。《杀蟒哥》、《石良》里的大毒蟒“长十来丈,有大水桶般粗”,而勇猛健壮的壮族青年“杀蟒哥”挺身而出,经过生死搏斗,终于为民除了害;《石良》中的主人公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二是与妖魔鬼怪做斗争的故事,比如《人熊婆的故事》、《勇敢的阿刀》、《七鼻老妖》等。其中,妖魔鬼怪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动物,它们凶残而且狡猾,但最终还是被勇敢机智的勇士所制服。三是与自然现象做斗争的故事,比如《布伯的故事》、《候野射太阳》、《挨朱奴》等。其中,拟人化的雷王、十二个太阳、风公风母等,都给壮族先民带来过灾难,因此这些英雄才与它们进行殊死搏斗,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四是与反动统者做斗争的故事,比如《莫一大王的故事》、《岑逊王》、《侬智高的传说》、《逃军粮》、《宝葫芦》、《神医三界》、《财主和农民》等等。它们所赞美的形象,有的是带领人民反抗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英雄,如莫一大王、岑逊王、侬智高等;有的是与本民族财主、土司进行斗争的杰出人物,如农民、三界、达英等。以上所说的这些人物,都是“普遍性的人”即男性,他们无疑担当了壮民族勇于抗争的道德使者。当然他们不是孤独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壮族妇女也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比如,《月亮妹》中的月妹,为了给大地带来更多的光明而付出自己一生的追求;《妈勒访天边》的孕妇,为了给大家寻找光明和寻找“终极存在”,而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儿子的青春;《救月亮》中的玛霞,为了人类的光明幸福,敢于同自然灾害做殊死搏斗;《逃军粮》中的莎英,不仅用乳汁和鲜血哺育了义军,更用精神激励了整个民族。如果说这些都是故事里的人物,那么众所周知的班氏娘娘、瓦氏夫人以及太平军中的“大脚女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了。
壮族是一个崇尚恋爱自由的民族。追求自由、忠贞的爱情是壮民族恋爱道德观的重要特征,其中的现实表现就是“倚歌择配”、“不落夫家”、“男嫁女婚”等。可以说,这些场景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空间,使妇女发挥出更多主人翁的作用。而在众多的壮族民间故事中,很多青年男女成了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先锋。例如,《马骨胡的故事》说:驮娘江泮养马人家的姑娘阿冉,与彼岸的后生猎手阿列相爱,但贪婪荒淫的土司从中作梗。后来阿列勇敢地射杀了土司,与阿冉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样的爱情故事还很多,有《老三与土司》、《文龙和肖尼》、《仙湖泪》、《蝴娘》等,它们内容情节各有差异,但主题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反映壮族男女青年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体现出他们自由忠贞的爱情观。尤其在这类故事中,不少女主人公都具备美貌、勤劳、善良和忠贞不渝等形象,如长歌《幽骚》中的女主人公、师公唱本《唱秀英》的秀英等,这就表达出壮族人民对女性较高的道德期待和评价。
壮族是一个崇尚团结和睦的民族。壮族的稻作文化是一种具有安定、团结、和谐内涵的文化,梁庭望教授指出:“这种价值取向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20]。一是社会各成员的团结互助。《传扬歌》唱到:“壮家讲互助,莫顾自家忙”;“春耕待翻土,有牛要相帮,老少齐下田,挨家帮插秧”。平时要注意避免因小事而引起的摩擦:“莫争一株树,莫抢一兜菜,莫为鸡相吵,莫为狗伤人”。应该说,这种道德要求是没有性别分层的。二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和睦。《传扬歌》教导人们:“夫妻千千万,牢记在心间;花山成伴侣,结发情义长”。还说:“一家两夫妻,相敬不相吵;家事多商量,和睦是个宝”。显然,这种倡导与封建式的“夫唱妇随”是有很大区别的。《传扬歌》尤其强调夫妻的对等义务:既反对丈夫虐待妻子,因为“恶狗才咬鸡,蠢汉才打妻”;也反对“一藤缠三树,情义薄如水”,即妻子不能背弃丈夫。三是家庭各成员的敬老爱幼。《传扬歌》要求在家庭内部不仅要“儿女共抚育”,而且要“老人同敬养”。在《布洛陀经诗》里已经较多地出现了“孝”、“敬”、“礼”等概念,它们都是壮族家庭走向规范化的反映。而直至今天在生产活动中还普遍存在的“多饶制”,可以说就是壮族团结互助道德的现实表现。
三、壮族道德要求及两性角色差异
汉克斯指出:“代代口头相传的大众礼仪和规范设立了泾渭分明的性别界限,一般限制妇女出行和行动的能力,对那些违规者加以批评或惩罚。”[21]壮族的道德规范虽然有较多对男女双方一视同仁的内容,但就总体而言,尤其在封建专制盛行的时候,这种一视同仁是居于次要方面的,而占据主要地位的则是两性在道德义务上的不对等性。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是壮族生产方式自身演变的需要,也是“三纲五常”等中原封建伦理道德强势浸润的结果。
一是妇女对男人的顺从和伺候之德。本来,壮族女性是最具有追求自由的传统的,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改变和封建文化的影响,“妇人从人者也”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她们挥之不去梦靥。尤其基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为了将来做个贤惠媳妇,每一位壮族女性自儿童时期就开始按照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向着“伺候”的方向靠拢。雍正时期的壮族诗人黄彦坊在《女工咏六首·扯棉花》中写到:“寒闺隐隐一灯红,十岁姣娃学女工。玉手纤纤偏耐冷,扯棉声过竹篱东。”乾隆时期的颜嗣徽在《归顺直隶州志》中的描述更为直接:壮族地区妇女人人能织,并且“未笄之女即学织。”同样是这个年纪,男孩大多还是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呢!另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壮族学校教育是少数男子才可享受的权利,社会上根本不存在为女子开设的学校,即使有少数开明人士在家设塾延师教授自家女子,其教育内容也无外是《女诫》、《烈女传》、《女孝经》、《女训》之类,这不过是“顺从”教育的系统化而已。另外,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的道德要求,在解放以前的壮族婚姻中占据着相当的位置,比如壮族长歌《达稳之歌》、《达备之歌》就是对此所进行的控诉。
二是妇女必须进行“忙里忙外”的角色扮演。黄剑在《石窟一征》中说到:壮族“乡间男子多逸,妇女则井田、耕织、樵采、畜牧、灌溉、缝纫,无所不为。”这既表明壮族女性素有能吃苦耐劳的传统,也表明壮族社会赋予妇女较多的角色负担。对此,作为壮族的“百科全书”的《布洛陀经诗》,是通过或明示或暗喻进行了表达和肯定的。比如,《解母女冤经》叙述到:“一娘生九女:一女布不织,一女水不挑,一女纱不纺,一女机不摇,一女地不觅,一女田不种,一女榆木脑,一女愚终生;只有第三女,聪明又伶俐,还有第四女,真正成人才,能织七路巾,会织八路带,善织十路布,缝衣美自身。”可见,除了种田种地外,从事纺纱织布等也是壮族社会对妇女的性别角色期待,如果不会做、不愿做就会产生角色距离,而男子就没有受到这样苛刻的角色要求。作为壮族的“道德经”,《传扬歌》在“为妻”中也对妇女提出“忙里忙外”的角色要求:“当家贤主妇,种地是好手。缝补她手巧,老少不用愁。清晨她早起,睡眠她在后。”另外,《传扬歌》还对一些妇女作出了如下的道德评判:“妇人心眼坏,丈夫不想活。为妻不懂礼,老虎加懒猪。”还说:“妻不通情理,专毁丈夫名。闹得房顶飞,好比鬼进门。”显然,在“男子多逸”的背景下,这样的道德要求很难说是公平的。
三是男女“内外有别”的权利分配制度。从稻作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从追求和谐有序的文化传统来说,壮族社会是能够给女性提供较大的活动空间的。但是,随着生产模式的日趋多样、父权制的逐渐巩固,尤其是随着中原封建宗法思想的不断渗透,壮族地区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出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初步分离,从而给妇女的向外发展增添了障碍。壮族妇女历来勤劳能干,他们在两种生产中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内外有别”也体现在男婚女嫁上。经诗《解母女冤经》有云:“宁得一抓米,不愿留一女;有女儿须嫁,男儿家中放。”而那个外嫁的女子近十年未回娘家看过爹妈,直到落魄时才回来争财产,于是遭到爹娘的责骂:“女儿莫言狠,你若是男儿,任挑大笼鸡;你若是男儿,可接铜柄刀;你若是男儿,能种好田地,能继承家产,能用锅连灶,管父母地盘;你若是男儿,不远嫁他乡,你是女儿身,才挨嫁出去。”显然,男子外嫁女儿留家、财产由女儿继承,这种情况只能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与此相反,女儿外嫁男儿居家、财产由男儿继承,这在父权制社会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背离这一伦理道德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卫道士”的诅咒。
四是妇女必须做“守节烈女”的道德要求。应该说,贞洁和烈女等封建观念不是壮族社会“原生”的东西,甚至可以列入梁庭望教授所说的“与壮人传统有所乖违”[22]。然而,这些外来的道德观念一旦与壮族的“父权”势力相结合,反而显示出较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传扬歌》对不贞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为妻不知羞,贞节送他人。卖身给汉客,游荡废光阴。天黑下床去,偷汉摸出门。”而道光时的黎申产在《詹氏节烈歌·李星海刺史属赋》写道:“吁嗟乎,忠臣烈女事无殊,不二君兮不二夫。”他在《查氏一门节烈歌》的开头也写道:“杀身成仁称志士,古来几见奇男子?女子能成志士仁,同心难得如查氏。”在《王烈妇行·有序》中写到:“妇人不二斩,烈女不二夫。”据黄庆印先生考证,为烈女树碑立传之事,在壮族文人中是不少的。[23]不过,一些壮族男子自己却是不那么“贞洁”的,因为他们时常有纳妾、嫖娼等现象,所以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指出:“壮人有多妻俗”。可见,这种道德要求对一些壮族男子是不适用的。
(第三节)壮族的知识论与性别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