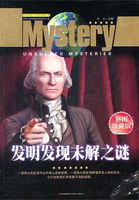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局面,禹在治服水患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书·禹贡》即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这就是说九州统一了,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故《左传》襄公车年说:夏统治者曾把其所统治的广大地区“通为九州,经启九道”。所以禹划九州,从一定的意义上,标志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民族——夏民族,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随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基本完成了。
三、夏民族从初型到定型的发育
民族的形成,特别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最初民族的形成,不是一步登天,一下子就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它可分为初型和定型两个阶段,从初型到定型有一个相当的发育时期。夏民族从形成初型到发育成定型,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启以后,发生了太康失国之事,即传说中的东方夷族后羿,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征服了夏民族。不久,后羿又被其亲信伯明氏的寒浞所取代。只是到了少康时代,又经过了许多氏族、部落的大混杂和融合,在夏遗臣靡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斟灌氏、斟氏余众的拥护下,少康攻灭寒浞,杀其二子,重建夏朝,夏民族才稳定下来。其间,大约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
夏民族从初型到定型的发育过程中,其民族特征也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稳定。
夏民族的共同地域,在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即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结合部,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其居住的中心则是在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不少考古学家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与上述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大致相符,最近公布的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发掘报告更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夏王朝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不仅是夏民族形成的标志,也是夏民族共同地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九州”后来又成了“中国”的一个代名词。
夏民族的共同语言就是“夏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所谓“雅”,荀子曾说过:“譬人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他又说过:“居楚而楚,居越而载,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由此看来,“雅”就是“夏”,而“雅言”就是“夏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口沿上,刻着20多种符号,是否就是表现夏民族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字,这当然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证明。但是,按照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所说:“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三千多年,但是,依照甲骨文字的体系相当完备的情况来看,如果说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还算是谨慎的估计。”于省吾先生在评价半坡文字时则更肯定地说:“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有了六千多年,这是可以推断的”。这样,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就很可能是夏民族的文字。
夏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主要表现在“以铜为兵”的灌溉耜耕农业经济上。如前所述,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夏王朝建立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内一件青铜残片的出土,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灌溉,《史记·夏本纪》云:“禹浚畎浍而致之川”。郑玄注:“畎浍,田间沟也”。《论语·泰伯》亦云: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矬李遗址中还发现有宽2至3米,深约1米的水渠。对于耒耕,《韩非子·五蠹》说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说明当时不仅有木耒,而且还有木臿作为翻土工具。《夏小正》中有“农纬厥耒”,一句,也说明当时的主要农具是耒。在河南龙山文化煤山遗址就有木耒工具痕迹出土,更有力地证明木制耒耜是夏民族的主要农作工具。所谓“耒”,《说文解字》说:“耒”是“手耕曲木”。即一根前端尖头弯曲的木棒,在耒的一端绑上一个石或骨制的耜头,就成为耒耜。耕翻土地时,以手持耒柄,以脚踏耜头,刺地而耕。所以夏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是“以铜为兵”的灌溉耜耕农业经济类型。这种农业经济类型。这种农业经济类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还必须辅以渔猎和采集。《尚书·益稷》所记禹治水时就说过:“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夏小下》中也记载了夏民族除农业外,还有畜牧、渔猎、采集等生产政事。
与此同时,大禹以治水开国的大量传说又证明夏王朝对水利灌溉是实行统一的治理和管理的。从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古代利用河流灌溉的国家,为了治理水患和管理水利灌溉,往往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古埃及把全国的水利系统置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两河流域的早期苏美尔城市国家就把兴修和管理水利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所以,为了统一治理和来之不易水利灌溉的需要,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土地分配制度,夏民族在“以铜为兵”的灌溉耜耕农业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实行了“井田制”。《大戴礼·夏小正》说:正月“农率均田”。为什么要在正月“农率均田”?就是洪水泛滥的影响,每年必须宝藏在洪水过后,春耕以前把份地重新分配一次,以确定疆界划分,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界”。又为了统一管理水利灌溉系统的方便,实行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的“经界”就得十分整齐划一,形成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所谓“井田”。吕振羽同志曾肯定地说:“《周礼》、《论语》、《孟子》等儒家的作品中,所说关于夏代井田制度、必有其历史的一点根源,断不是他们所能凭空捏造,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就很可能是夏民族表现为“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早期的“井田制度”。这种“井田制”把夏民族紧密地联结成一个稳定的民族整体。
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首先表现在对于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事听天由命的观念上。此即《论语·颜渊》中所说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宗教信仰上这种低级形式与夏民族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情况是相一致的。
其次,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祖先崇拜。众所周知的夏铸“九鼎”,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表示对祖先的崇拜,《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哀公元年又说:“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在鼎这样的国家重器上刻绘象征图腾的“物”就是表示不忘祖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九鼎”不仅是夏王朝的国家象征,也是夏民族的民族象征。不仅如此,《论语·泰伯》还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这就是说禹自己吃得很差,却把祭祖宗的祭品办得很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由于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产物,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所以这里所称的“孝乎鬼神”,大约就是对祖宗先世的崇拜。因此,《礼记·祭法》中就说:“夏生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再次,反映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又集中反映在《夏小正》上
《夏小正》作为一本观象授时的历书,其从土地制度、社会生产结构到生产技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夏民族从事农业、畜牧、渔猎、采集的社会生产面貌,围绕着上述四项生产活动,又记述了物候、气象、星象、动植物等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夏小正》是关于夏民族的一部“百科全书”。
再次,《礼记·表记》中所说的夏民族“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蔽、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则反映了夏民族纯朴、厚淳的民族性格。
此外,夏民族尚黑色,不仅衣服喜用黑色,办丧事出殡也在黄昏,烧土为砖附于棺材四周。夏民族喜以山为衣服的纹饰;喜戴“毋追”和“收”式的帽子;生活用具我用陶、木和石制成的“明器”;祭社的牌位喜用松木;岁首为农历一月,“年”称之为“岁”。凡此风俗习惯之种种特点,都表现了夏民族猢的民族风情和风貌。
(第二节商民族的形成)
继夏民族之后,第二个敲开民族大门的是商部落。
一、商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
商民族最早居住在今山东半岛,属传说中的东夷集团。自认是玄鸟所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考,王亥的亥字,甲骨文上端所从,先为鸟,次为崔萑,最后为隹。从祖庚到武乙,五六十年间,亥子从象形到字化,由繁到简,由鸟到佳,无论从鸟从佳,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都象是一只鸟,其发展演变演变之轨迹,一清二楚,因此,王亥之亥从鸟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确证远古时商是奉鸟为图腾的一个氏族部落。
相传商的始祖契,为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即《史记·殷本纪》所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卵生的神话传说表明当时还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据历史记载,帝喾即舜,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故商尊舜为远祖。《礼记》·祭法即云:“殷人禘喾”;《国语·鲁语》亦云:“商人禘舜”。甲骨文中商民族的先世也叙到“夋”。“夋”就是喾或舜。商与舜的这种关系,表明契时正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
但是,由于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所以商部落“无定处”,,“不常厥邑”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至相土,不过3世,前后5迁,即契居蕃,昭明迁砥石,双迁商,相土再迁泰山下,又迁回商丘相土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商部落逐步安定下来。故相土后至汤建商王朝,虽经13世,但又迁徙3次,即帝芒三十三年,由商迁于毫,孔甲九年,殷侯由殷又迁回商丘,汤再由商丘近于毫。这时商部落的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这就是驯养牛马作畜力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故《管子·轻重篇》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表明商部落生产工具的改进。要发展农业,必须重视治理水患,兴建水利。史载冥治水而死,成了商部落的禹,而为后世隆重祭祀,下是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从王亥子上甲微以后,商的祖先都以干支为名号,说明他们已有比较精确的历法,反映商部落的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与此同时,商部落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牲口槽;“牢”是牲口圈。“立皂牢”即表明商部落的畜牧业从游牧发展到定居放牧了。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些情况都说明男子在氏族公社的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表明商部落大约在相土时已从母系公社过渡到了父系公社的时期。
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得商部落很快地强大起来。相土时,就乘夏王朝太康失位之机,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方的势力,控制了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商部落地域的扩大和商族商裔对相土功绩的追颂,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氏族、部落首领在战争中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战争正在“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这样,奴隶就会出现,阶级就会产生,氏族公社制度的末日快来到了,商部落在开始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中,迎来了商国家和商民族的诞生。
二、商民族在原始社会的崩溃中形成
就是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的历史条件下,商部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一方面是氏族首领的选举制度变成了世袭制(父子世袭或兄弟相继),促使了国家的诞生。历史上记载的冥的儿子王亥在进行贸易时,被北方有易氏部落杀死,并夺取了王亥的牛群。而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世袭了商部落的首领。在甲骨卜辞中不仅上甲微受到隆重的祭礼,连王亥也被尊称为商祖亥。从上甲微到汤的七代中,商部落的首领逐渐具有了国王的权力,使商部落的氏族公社组织逐步转变为国家机构。
在这里,首先是商部落的氏族贵族们转化为“侯”。“侯”最初只是所谓“射侯”之意。因为“侯”是古代行射时用兽皮或布做成的靶子。《周礼·天官·司裘》就有“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记载,所以《韩非子·八说》:“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而在原始公社末期,射箭是贵族最重要的本领,商部落首领选派射箭本领最好人人建国畿外,守卫边疆,名之为“侯”。这种“侯”在甲骨文中还有的被称为男、子、伯、公等。拿男来说,从甲骨文的字看从田从耒,表示它是氏族公社内善于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氏族贵族。这都是商部落氏族公社组织逐步转化为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是商部落的巫史转化为宗教官。原始社会和巫史,懂得一些天文气象医药知识,会占卜符咒,在氏族公社组织中,充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后来,随着商部落首领权力的不断扩大,这些巫史利用占卜符咒,假借不愿意,骗取信任,遂成为正在形成中的商王宗教官,甲骨卜辞中称之为“御史”、“卿事”、“夷”、“尹”等。掌握神权的这种宗教官,同时掌握着文化知识,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例如辅佐汤灭夏桀的重要人物伊尹,就是出身于掌王祭祀之事的小臣。由此可见,巫史向宗教官的转化,是商部落氏族公社组织逐步转变为国家机构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转变中,汤对商国家的最后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灭了葛国后,连续灭了夏王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韦、顾、昆吾等国,军威大振,正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与夏会战于鸣条,夏五桀败逃而死,夏朝亡,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兴起。
另一方面是商部落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的转化,促使了商民族的形成。首先是商部落内部氏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步步扩大,使得原来氏族赖以维系的血缘纽带逐步废驰。有些氏族成员纷纷离开氏族原来的土地,或者到新开垦的地区云,或者同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杂居。其具体情况现在虽然已很难考释清楚,但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代共有62国记载,使我们可以想见个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分化、瓦解之时,国与氏族几乎为同一东西,一国即等于一氏族,一氏族即等于一国,这62国虽然未必就是夏商以前实际存在氏族的全体,但却是一个起码的数目。对这62个氏族,我们可以断定:除一部分是商部落分化出来的氏族外,其余大部分是与商部落不同血缘的氏族,例如有扈氏、冥氏、斟氏、戈氏、褒氏,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就是属于夏民族的一部分。另外,我们知道,在商部落的发展中,从契至汤曾经8次迁徙。在这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又必然会与夏民族以及其他血缘的氏族部落逐渐杂居起来,“亥宾于有易”,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