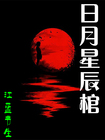(第一节夏民族的形成)
茫茫中原大地,浩浩黄河和长江流域,是谁最先从原始人们共同体的丛林之中突破出来,进入民族的大门呢?是源于炎黄集团的夏部落。
夏文化脉络的考古发现,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特别是近年来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发掘的突破性成果,一下子把笼罩在夏王朝和夏民族头上的迷雾拨开了。
据报道,在登封县告成镇西面约半公里处,当地群众习惯叫“王城岗”的地方,发掘出来了两座距今约4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遗址。两座古城东西相连,城墙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的。古城内残存有夯土筑成的房屋基础和储藏东西的地窖。在房屋夯土基础内,发现了埋有作为建房“奠基”的许多大人和小孩的牺牲者,并出土了大量当时人们使用过的陶器、石器生产工具和古箭头、骨箭头、蚌箭头等武器,以及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件青铜器残片。不少考古工作者认为,登封王城岗的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遗址。早在1979年徐中舒先生就认为: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就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夏史已见曙光”那么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的发掘就是夏史光芒的四射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探讨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了。
一、夏民族形成前夕的社会形态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炎黄集团中的一支——夏部落进入了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这就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即氏族公社制度瓦解,阶级出现,国家和民族处在孕育这中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夏民族进入河、洛流域后,氏族公社制度开始瓦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阶级的出现。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又可以成为当时社会阶级产生和对立的历史见证。例如在临汝煤山遗址的一个意向竖穴墓里,竟发现有觚、爵、等专用酒器和贝、玉、松绿石等21件随葬品。但是,在另外一些墓葬中,仅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在矬李遗址的同期文化层的墓葬中甚至找不到一件随葬品。这些差别巨大的墓葬,有没有头骨或下肢骨的墓葬,甚至在灰坑中还发现了跪伏的一具人骨架,这些无疑都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同样,近年来在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城堡内发掘的几个筑有坚硬夯土的坑中,发现了包括男女性成年、青年和儿童的结构完整而姿态很不自然的骨架,一个坑少者2具,多者7具。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这些埋有人骨架的夯土坑可能是大型夯土房基的“奠基坑”。无疑坑内死者的身份,也都是奴隶。又如,洛阳矬李遗址发现的两座墓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号墓埋葬的是一个生前被剁云双腿的男性,二号墓是一个被砍了脑袋后埋葬的男性,两者均无随葬品,可见,那时的奴隶确实是可以任意杀戮的。这一切都表明:夏史的曙光已照射到国家和民族的大门口了。
在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急骤变化的时候,以夏部落为核心的炎黄部落联盟也开始发生了质变前的量变,以夏部落为核心的炎黄部落联盟也开始发生了质变前的量变,其表现不是部落联盟首领的变质。众所周知,早期部落联盟的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联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敌对部落的侵袭和掠夺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盟由各部落首领组成议事会作为权威性的组织,主要应付对外的部落战争,同时也处理联盟各部落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黄帝与炎帝组成部落联盟时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到了尧、舜、禹时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联盟成员之间的平等已被联盟首领的权威所,最突出的事实就是尧、舜、禹在部落联盟中的首领地位,并不是真正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而是他们凭借武力争夺来的。我们先来看尧的首领职位是怎样得来的。《淮南子·本经训》载:“逮尧之时,凿齿、九婴、大风、封,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寿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断修蛇于洞庭,擒封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尧的部落首领的位子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再看舜的首领职位又是怎样得来的。盛传因舜贤,故尧让位于舜,其实当舜作尧的助手时,尧就不放心,“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而舜一旦羽翼丰满便凭借武力取代了尧的首领地位,《韩非子·说疑》称:“舜偪尧”;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上行下效,“舜尧”,故禹也演出了“偪舜”的闹剧。历史上不少文人学士赞不绝口的“禅让”制,其实是已经向国家和民族的大门迈进的部落联盟首领手中的一块遮羞布,《列子·杨朱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祈百年。”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于是,阶级的出现,部落联盟首领的变质,就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和第一个民族即将诞生了。
二、夏民族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
相传夏后氏在进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人们生活在氏族、部落的狭小世界里,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同氏族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完全受血缘关系的支配。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传说中为黄帝后裔的夏后氏,姒姓,共12个氏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氏族组成为一个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原始血缘的大部落。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的。”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质变的主要标志。正如《越绝书》卷十一所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故《史记·封禅书》云:“禹以九牧之金铸九鼎”;《墨子·耕柱》亦云启派蜚廉铸鼎铸鼎于昆吾。昆吾在今河南濮阳西南,是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产铜中心。更引人注目的是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出土了形制和器种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其中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锛、铜椎等,有作兵器用的戚、戈,还有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铃、箭头、鱼钩等。在二里头还发现有铸铜手工业作坊的遗址,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坩埚碎片,以及铸铜用的陶范残片。而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内四期的一个灰坑内发掘出土的一件无可置疑的青铜器残片,确切地表明,相当于夏王朝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已经使用青铜器了。这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历史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对于夏民族的形成有意义的是: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大禹时期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发展,也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基础的形成。
这时,更有意义的是水井的发明。据《经典释文》引《周书》云:“黄帝作井”。《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穿井”。《世本·作篇》也云:“化益作井”,宋衷注说:“化益,伯益也,尧臣。”可见水井的发明大约在禹治水以前。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遗址又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在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水井一眼,“形制竖穴,平面为椭圆形,直径1.7米,深6米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发现水井,在偃师灰嘴又发现一种长方形水井。很明显,水井的发明和使用,可以使人们摈弃江河日用水源,向纵深开阔的地方聚落定居生产、生活,这在一定的条件和程度上,必然促进夏部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定居下来,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迈向精耕细作。之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实际的意义,对夏部落在向夏民族的过渡中形成稳定的共同地域也有特殊的意义。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交换和贸易成为可能。在二里头的一个土坑内一次就出土了12枚贝,在另一些二里头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仿海贝式样制成的小巧耐用的骨贝和石贝。很明显,在二里头出土的贝,以及玉和松绿石等,都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等方式从外地引进的。对照古代文献,汉朝的《盐铁论·错币》中就记载:“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钓鱼、刀布。”由此可见,夏王朝使用的是以贝为主的货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它反映了夏部落在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族形成特别有意义的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这就使剥削成为可能,氏族公社里出现了贫富分化,而导致阶级的产生。例如,在有关夏王朝发动战争的誓词中,就决定不愿为奴隶主去打仗的人处以“孥戮”。“孥”通“帑”,指子女或妻子。“孥戮”即或以为奴,或加以刑戮。这些可以处以“孥戮”的人就是奴隶。但是,本氏族、部落的人沦为奴隶,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在战争变成为正常职业的“英雄时代”,黄帝的后裔们对南方的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史载“尧战于丹于之浦,以服南蛮”。舜在与共工和鲧交战的时候,也不放松对三苗的控制,《韩非子·五蠢》即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道三年执于戚舞,有苗乃服。”禹时更是大举进攻三苗,他在出兵誓师在会上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于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在一次战斗中,禹射中三苗的军事首领,于是“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至使“子孙为隶,不夷于民”。三苗部落的人大多数被俘成了奴隶。
阶级产生的情况我在上一个问题里已论及,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阶级的产生对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民族形成究竟有什么意义?从原始社会崩溃的一般规律来看,这就是已经成了奴隶主阶级的氏族贵族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利益,把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这个情况的出现也是逐步的。早在尧时,部落联盟内部就出现了初步的分职。《淮南子·齐俗训》即云:“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舜时部落联盟的上层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职更为明确,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以舜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领导机构由28人组成,分司徒(民政)、司空(水利)、后稷(农业),工师(手工业)、士(政法)、秩宗(礼)、虞(山林水产)、典乐(文化教育)、纳言(内务外交)、四岳(参谋)、十二牧(督察)等11个部门。这时国家虽然还没有正式诞生,但却具有了国家政权雏形的框架。到了大禹之时,原始社会的崩溃加快了步伐,其标志就是城堡的出现。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城堡是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也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力的重要设施。《孟子·万上篇》就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也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前已提及,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还有河南淮阳县平粮台发现的规模比王城岗大4倍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遗址,不仅用土坯砌墙,有城门和门卫房,还有排水的陶管道,甚至还发现台建筑。这样,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所以,笔者认为:王城岗遗址以及平粮台遗址以及平粮台遗址的发现说明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也就是大禹时代,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古本《竹书纪年》所云:“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所云:“禹都阳城。”都表明这时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关“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这个机关就是国家。而在二里头遗址里发掘出来每边长约100米,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也进一步证明夏国家政权的存在。于是,“大同”之世变成了“小康”时代。禹传位于儿子启,“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宣告诞生。
恩格斯说:“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在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夏部落与夷人部落、羌人部落以及居住在河、洛流域的其他氏族、部落原有的血缘关系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意义,他们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杂居一代比一代厉害的情况下,进行着新的组合。尊黄帝为始祖的夏部落,与分别尊颛顼、帝喾、伯益、皋陶为始祖的蛮夷部落,以四岳为宗神的羌人部落等结成新的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征服三苗部落的过程中,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逐渐团结而为“永久的联盟”,由此“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军事上的胜利,奴隶的不断增多,氏族公社制从被私有制打破缺口,到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本氏族部落人员的流动迁徙,被征服氏族部落的强迫迁移,都不断地打破和瓦解了氏族公社的纽带——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开始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而且杂居得愈厉害,不同始祖的各氏族、部落愈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例如,早在舜时,这个部落联盟就发生过“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的事,说明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血缘关系的破坏早在进行之中。舜在对周围的氏部落进行征服战争的过程中,还“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对不同血缘的共工、驩兜、三苗、鲧等部落也进行分化瓦解,变其风俗。这样,各氏族、部落之间不断地相互融合,因此,到禹时,《左传》中所说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时的夏部落联盟,已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了。正如恩格斯所论述古罗马民族形成时所指出的:这时“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住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万国”就不是氏族、部落的籍别,而是地域的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