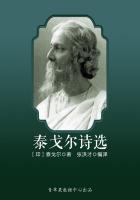但后来,因为得了吴冕藻女士的帮助和指导,有了伊的勇敢和勤劳,于是我又提起我的精神来干这马二先生的选业。我把我的选诗的条件降低:不要首首诗能提高平民的精神,只要能陶冶平民的性情也算满足了。于是我所注意的是诗的容易懂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希望我所选的诗能够使读了四册《平民千字课》的人一读就懂。悲哀时的痛哭,快乐时的欢笑,恋爱时的疯狂,被损害时的怨尤,种种在我所选的诗中所表现的真实的情感,我希望能引起一般平民读者的情感的共鸣。
我选这本《平民诗选》是很惭愧的。我虽然也受经济压迫而度过几个烧饼一天的日子,但我却并不曾替人们拉过洋车;我也曾经过抄写钢板而致手指肿痛的生活,但我却不曾为人们挑担而吐血;我也曾经过夹衣过冬的贫寒时期,但我却不曾尝过单衣在雪地里奔走的痛苦。到如今,我脸上已经戴起金镶眼镜,夏天身上穿绸衫,冬天身上穿皮袍,吃的是三餐白米饭;我的生活已经一天天贵族起来了,我选的《平民诗选》也许不是我亲爱的平民朋友所欢喜读的罢。但我的被损害而破碎的心,是经过无数的风霜雨雪来的,我把我的真心来选成这部《平民诗选》,也许不致于和我亲爱的平民朋友的心十分隔膜罢!
最后,我应该谢谢陶知行[行知]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仔细校阅了一遍,我更应该谢谢杨可大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拿到他教的平民师范班教授了一次,贡献了我很多的意见。我尤其应该声明的,是这本《平民诗选》大部分是吴冕藻女士选的,选好之后又蒙伊抄写一次。没有吴女士的热心和帮助,我决选不成这部《平民诗选》!
(附记)这篇序大概是一九二四年冬天做的。序是做成了,《诗选》也选成了,但后来《诗选》
也不知寄到哪里去了,从此竟无消息!呜呼!中国之事,大抵如斯!
一九二八,十二,二十,记。
《深誓》自序
我的几十首小诗,因了曙天女士不惮烦的替我编成付印,得传布在我爱的同时代的读者诸君之前,这在我个人,实在觉得荣幸而且羞惭。
因为我是青年,我的诗多半是歌咏爱情。我曾彻夜发狂地高唱爱之恋歌,在旷野无人的星光底下,清风为我而低吟唱和之音。然而我的恋歌,多半在清风明月底下消灭了。当细雨朦胧地从天空的浮云流到人间的时节,我的忧愁之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这痕迹,是深刻而不能磨灭的;虽然在慈善的太阳从林里庄严地上升着的时节,我也曾俯伏在阳光的脚底,高吟爱之颂歌。
我的青春一天天的逝去,我的容颜渐渐衰老,我的歌声也已经枯燥而且消沉了罢。我不能常常唱这样的恋歌,但如果人间爱之火永远不灭,我还想高吟几句,在我老态龙钟的时候。
我应该感谢在旅路上遇着的几个女郎!有的给我微笑,有的给我沉默,有的给我忧愁和疯狂。我不知道伊们现在是到那里去了。然而那些不灭的微笑,不灭的沉默,不灭的忧愁和疯狂,都在我的几十首小诗里永远留着不灭的影子。
《深誓》的读者们!假如你是理智化的学者,你是高慢的文学评论家,你是著名的高贵诗人,你是得意的老爷,太太,我希望我这本小诗不要陈列在你们之前。如果你们的眼珠看过我诗集中的一行,这在你们毫无所得,而在我则将得着讥笑和侮辱。那些得恋而欢笑的对对青年,那些失恋而悲哀的旷夫怨女,在你们的快乐声中,在你们的洒泪时节,我把我的小小诗集献给你们。如果你是欢乐,它决不在你的欢乐心中留下悲哀的痕迹;如果你是悲哀,它决不在你的悲哀心中种下欢乐的种子。
我应该感谢曙天女士——我的亲爱的伴侣!因为有伊帮助,我的小小诗集才能出现于人间。
一九二五,七,十三。
跋《情书一束》
年代久远,忘记是那一个皇帝时代的事了,总之,朋友Y君那时还在人间罢。一个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们俩跄跄踉踉地跑到东安市场去,在小店里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儿也渐渐和暖起来了。于是在市场上踱来踱去地想看女人,——看女人,这是我们那时每次逛市场的目的。
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又是那样冰冻严寒的冬天,小摊上虽然还灯火辉煌地,游人确已寥落可数了。那里有美丽的女人呢?我们俩踱来踱去的瞧了半天,终于连一条红围巾的影子也瞧不见。Y君很凄凉地说:“今晚的市场是何等灰色呀!”“哦,灰色!成对的此时大约都躺在红绫被里了。”我带着气愤的神气答。
总之,后来我们是混到小书摊上去了。Y君花了十吊铜子买了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他那时已经对朋友们挂起招牌想做强盗式的英雄了,虽然要做英雄是为了得不着女人的爱的缘故。我呢,因为袋里无钱,所以什么书也没有买。那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有一个青布硬壳套,Y君只在灯底下打开套来略略翻看了一本第一册上面的图画,便夹在肘下走了。但是,在半路上,Y君的一套《三侠五义》终于被我用强迫的手段夺了来。其间略有争斗,我记得还挨了Y君恶狠狠地打了一手杖。一手杖正打在背脊之上,当时觉得很痛,过了几分钟也就消失了。而且代价也真值得,谁也梦想不到那样一套旧小说内竟夹着几封蝇头小字的哀惋绝人的青年男女们的情书。
那些情书里的男女主人公是谁呢?何以夹在这一套旧《三侠五义》里?我虽然不是考据家,但当时为了好奇心所迫,也曾花了很多时间去考据,而结果仍是渺渺茫茫。
那情书上所署名,男的似乎是J,女的似乎是A。然而J是谁呢?A又是谁呢?我千思万想终于是难明白。我那时对于这些情书绝对守秘密,第一个要瞒着的是Y君。至于为什么要守秘密?理由此时也忘掉了。大约我那时把那些情书当作宝贝看待罢。乡下人得着宝贝是不愿意旁人知道的。而况那些宝贝明明从Y君买来的旧书里得来的呢?
我在夜阑人静,孤灯俦影的时节,偷偷地在灯下阅读那些情书:红色的信笺,上面点点的尽是痕迹。是泪痕罢?因为是用铅笔写的,所以字句也十分模糊了。但隐隐约约地总可看出青年男女真情的流露,和人世种种不幸的痛苦。
我青年时也蒙一两个女人爱过,但后来伊们都爱了旁的有钱有势有貌的男人,把我这又穷又弱的“丑小鸭”丢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感谢那些情书,消磨了我无数难眠的长夜。悲哀处流了一把眼泪,感动处叹了一声可怜。尼采(Nietzche)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那几封蝇头小字的红色情书,盖无一字无一句不是青年男女火一般热的爱的心中流露出来的鲜血呵!但那情书中的主人公J与A究竟如何结果?——家庭的顽固,社会的压迫,第三者的纠纷,我看了一些断片的情书,如何知道他们以后的渺茫的结局呢?
人生如朝露,Y君竟因肺病于前年夏间死去。冥冥中是不是有鬼呢?我不知道。自Y君死去以后,我心中十分悲伤。晚上也时常做梦,梦见Y君用手杖打我,痛得大叫而醒。有时我又梦见一位不相识的眉头稍蹙,身材瘦削的青年,与一位装束入时,娇小玲珑的少女,向我要求什么。因此神魂不宁,一病两月。病中,我知道是那些情书作祟,想把那些情书用火烧去。但燃了几次火柴,终于不忍下手。我因此又向冥冥中祷告,拟将那些情书誉清印刷出来,传之人间,定名为《情书一束》。
然而穷汉生涯,时间和精力已经整批的卖掉了。两年来我在一个古庙里替和尚们守菩萨当书记,每天要在七八点钟的时间坐在观音菩萨座下写蝇头小楷的《金刚经》。
晚上总是肩酸腰痛,卧睡不宁。心里也想把那些情书誉清出来,以期无负自己的祷告。然而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今年夏秋苦雨,古庙檐瓦多漏洞,我的竹箱搁在窗下,常为雨点打湿。W君说,“把箱子打开来晒晒罢。”
我对于W君的好意是感激的。然而这竹箱怎能拿出外面去晒太阳呢?我的确存了一个自私的心,以为将来这些藏在竹箱里的情书发表出去,一定要瞒着旁人,算作自己的创作。我的房里的财产,除了这一口竹箱以外,四壁空空,毫无可以隐藏的地方,所以那些情书也终于锁住箱里了。秋尽冬来,体弱血衰,不能耐冷。忽然想起竹箱里有一件十年前的老羊皮背心,或者可以御寒。取钥开箱,才发见摆在上层的那些情书已为雨点湿透,字迹模糊,不可阅读。而老羊皮背心则依然无恙,则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叹气数声,欲哭无泪。亦可怜矣!
呜呼那宝贝似的数十页情书已经为雨水所蚀,半隐半现矣。余乃立志就记忆和想像所及,一鳞一爪,为之整理就绪,以期青年男女之真实情感,不致无端湮没。刚拟就冬夜难眠之时,开始执笔,而京津战起,交通断绝,百物昂贵,困于油盐,时焦急而辍笔。茬苒两月,才整理出若干篇。名为《情书一束》,从两年前旧定之名也。
余年青时也曾弄过文学,其实也不过弄弄而已,并不是对于文学,特别喜欢。好像是Stendhal曾说起,他坐下来写文章就好像抽雪茄烟;我之弄文学,也正是抽雪茄烟之意,虽然我并不想高攀Stendhal般的文豪。做文章也许是我的A Refuge from the emptiness of Life罢。匆匆忙忙的随笔写成几篇东西,有的在朋友们办的报上发表过了,有的寄出去发表,忽然又被编辑先生退回来了,上面还用朱批批了“不用”二字。现在也择了几篇,发表在《情书一束》里。
至于读《情书一束》的人们,有的读得痛哭流涕,有的读得嬉笑怒骂;——有的拿它当小说读,有的当故事杂感散文读,有的当情书读,——放在抽屉里来常写情书给爱人时的参考;有的文学家与批评家或者蹙起眉头来以为这不是文学,这是艺术园里的一束杂草:都随他去罢。一二百年后或者有考证家出,引今据古长篇大论地考证《情书一束》,也许竟能隐约地考出《情人一束》中的许多主人公,如胡适之先生之考证《红楼梦》焉。是书即暂时无人肯买,将来也许竟能风行一时罢。然而未来的事,谁有那样耐心去管它呢?至于余贫穷人的希望,则在是书之能赶快印出,赶快买〔卖〕去,赶快多弄得若干金钱,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难而已。
一九二五,冬至节日。
罪过
衣萍兄:
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呀!——但是,衣萍,我应该恭贺你,你的小说能深深地刺入人心,这便是你的成功,无论所得的报酬是咀[诅]咒或是怨恨。
《情书一束》虽然只蒙你在京时给我看了一两篇你的初稿,而我所牢牢记得的,是你的作品,处处表现你的真实的大胆的描写,那便是你的人格的表现,虽然我到如今还不曾读到你的已经出版的《情书一束》。我总觉得我国现在流行的小说实在太灰色太乏味了,我们实在不需要那些文章美丽,辞句浮夸,粉饰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产品,我最爱那胆子最大的Gautier的作品,他将他理想中的妇女的美,妇女肉体的美,赤裸裸的绘出来。绅士们看了自然要惊惶跌倒。George mcore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坦白,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心理是病态,卑怯,爱女人。他似乎说所有的书,只要不讲女人,便不是书;即是好书也不是我们所爱读的。他说Hugo的著作便是个好例。
我现在要你把《情书一束》快寄我一册。Miss房仲民那册也请你从速派人送到她的学校里去。她喜欢读你的作品,比我盼望得更急。她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