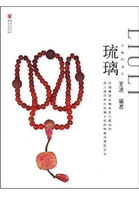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一)
“如果你的心已经交给电影,不可能再爱电视。”亦舒说。不,亦舒写。另一段,“在超级市场看到罐头刀会失魂似的走到前面,喃喃说:‘没有你怎么活呢?’”同样由亦舒所写。你没有读过《留英学生日志》?薄薄一小本,封面有一堆穿了毛衣和冷帽的小人在堆雪球。那个年代,离乡别井,她度过了一刀一笔走天涯的日子,“刀是罐头刀,笔是写稿笔”。
写稿的人,不可能不爱恨亦舒。将爬格子当填银行人数纸的人,更不会忘记亦舒——是她,教晓我们文章有价——一日有中文流行的地方,就不会饿死中文写的好(或者很差很差)的人。看,八万元奖金,西西鳌头独占了!而西西的确是写得很好的。
七三年,还是七四年?在尖沙咀的喜来登,我曾与西西及亦舒,吃过一顿茶。那一日,亦舒送给我一本《我之试写室》。但,我只记得束起头发,戴上眼镜的西西。亦舒不会看到这段文字,否则一定咧着牙齿,似笑非笑了。亦舒一定害怕自己的名字在茫茫人海中被提起,而且那么无关痛痒。
就像揭开八一年初版的《豆芽集》,我认定她写的是我:“陈认为一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月薪不应值四千元。但是学历与薪酬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做政府工。”
(二)
“看海是很吃力的,”亦舒写,“海水灰黑色,裸露,没有保护。”看海,亦舒形容“衣裤抖动有如疟疾——不如归去”。有一次,“在罗马竞技场吃冰淇淋,叹道:‘我爱它!’旁边的英国老先生起反感,他说:‘爱这个字,一生不应用得超过三两次,怎么可以吃个冰淇淋也用这么严重的字句。’”
从小便读亦舒,她写菲奥路昔,我便去买一条菲奥路昔,是的,爱虚荣心驱使唆摆,纵然不知道它原来有这么一个名字,只为了你让我穿过时的衣服,那不行。流行的东西不一定件件合胃口,但过时货品恕不招待,现在还穿宽脚裤?走不出去,如果没有钱,我会只买一条合适的菲奥路昔,星期一穿到星期六,星期日在洗衣机洗干净,星期一再穿,是的。
“朋友也一样,找不到好的,一个就够,星期一见到星期六,星期日休息一天,从头来过,你不能叫我见过时的人,确是势利。”
衣服从来堆山积海——是我,不是亦舒(?)。
昨晚收拾了几小时,旋即想起倪女史的牛仔裤哲学,非常的清者自清。一个做得不好,当会被取笑:过洁世同嫌呀,兄弟。(亦舒口吻。)
哦,《红楼梦》看不懂,起码应该知道亦舒的好处吧。
(三)
“熟稔会带来轻蔑,跟一个人太熟了,总不能给他应有的尊敬。有时候想,这样念念不忘Z先生,大概只是因为从没见过他在家洗碗看报的情况吧。”如此类推,皆因没见过他如厕、剔牙、挑鼻、放飞剑——亦舒都写过了。既然写得好,比后来拾人牙慧的更好,为什么不能以誊写和对答的方式,来飨读者?
一百八十九本亦舒著作,还未能称“全集”呢——少一个专栏,不能称为减产。数量媲美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喜爱的作家之一。凡是多产的写作人,必然是因为某处有人辗转呻吟:“哦,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才好?”阿加莎以侦探小说替一些人的枯棵生活吊盐水,亦舒呢,思想不保证“进步”,然而文字一定好。
好就是好,清脆、明快、干净、利落。
不过从没有拿过与文字创作有关的任何一项奖——当然,金庸若是排在领奖的队头,亦舒还是有机会的,假如她不介意一边凑女(带女儿),一边等。
但,今日的读者,最年轻的世代,只能读到味道大大淡化的小说,而且净写身外之物,“岂有豪情似旧时?”碰巧,与她的一本劲好睇散文集同名。
曾经有个笔名叫阿妹,人们却选择记住伊莎贝。
(四)
发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以及另一个人对他的爱……而,时间让我在重读《喜宝》的此刻,知道香港若有它自己的文学,亦舒堪称鼻祖。
这,当然纯属个人意见——只是:有什么意见不由个人出发真有一日集腋成裘,许多时候,也不外目光放远,将风景看在互惠互利的日后。
香港若有一枚至为自信的文学奖,应该是亦舒的。
这不关乎倪女士本人不在乎,或,有多少在乎——与其论上一条以利害关系排名的长龙,不如寄望每册小说的销售额,散文集最常见的一行:“读者眼睛是雪亮的。”哈哈,真是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就算读者真有眼睛,又有眼珠子,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
读者进步,一半由于作者进步,起码一半。
另一半,继续焚香供奉神情呆滞的写作人,或力不从心,或才华只属有限公司,她是上演拉牛上树,看得旁边的人们好不辛苦。
每次辩论她的江湖地位,文字界揸Fit人例必将“流行”加冕——谁是当家作主的,从这两只字见端倪,可惜他们尽管也写写写,那么那么地热爱文字,奈何文字魅力对待他们一似高窦猫儿,愈叫愈爱理不理,甚至,干脆掉头就走。
(五)
“我可否将你比喻作一个夏日?”老好威利的好处,粱实秋直译在他的一支笔下,但是真要领略到它的甜丝丝,还待片言只字地,重温亦舒。
我知道我知道,“亦舒”,欲罢不能,已经进入第四日——这一栏作者的签名,快改姓倪了。
然而,请你包涵我的沉溺,仅仅多那么一天,可以不?
没办法啊,初恋容或回不去,她那充满赤子之敏感的文字,一如采撷不完的野生花朵,要多少有多少。(插花焉用花瓶?稿纸也不错呀。)像“最近致力于晒太阳,每日一起床就晒”,然后亦舒的妈妈问要晒到几时,“在下指红木家私说:‘喏,那个颜色。’”不无斗气成分。根据亦舒,“老母对鄙人一切大大小小行为都有疑问”。
根据亦舒,她妈妈认定生为女儿便应以嫁娶为己任,看见一抽屉的原稿纸被写得空空,笑说:“本事也真有一点点,都填满了?”所以,回顾亦舒的不同阶段,不难发现她“恨”结婚——渴望,偏又因得不到而怨艾:“胡太开口闭口便是胡先生如何如何——‘胡说莱茵河怎样漂亮……’真诧异,都一九七八年了,这么年纪的女人,何必在丈夫口中听说莱茵河,跑去瞧瞧不就明明白白……”间接鼓吹了我帮基佬独立。
(六)
喜宝去买戒指,问:“你们店里有没有十卡拉左右全美方钻?”结果选到的一粒是九点七五卡拉,全美,切割完整,但是不够蓝。
那经理说:“姜小姐,如今这么大的钻石,十全十美很难的。”
你知道喜宝如何回答?
喜宝说:“我不相信。我要十全十美的。”
为什么?赤手空拳的一个人,竟然对生命的要求如此大口气?简单啊——“姜小姐,你是付现款吗?”喜宝抬起眼:“你们难道还设有十二年分期付款?”听,听,没有一句别人的说话不是在找她的碴子,就是在大洒金钱之际,丝毫不觉意气风发,反而酸了鼻,涩得舌头发麻——报复生命,以眼还眼,可以避免两败俱伤吗?好像不可以吧。
喜宝是谁?喜宝大抵是许多香港心灵的砌图游戏,或碎钻,所以才会相信“贪婪的病应由贪婪来治”——大总是比小的好,同时,目前只要拥有很多很多,便能填补有生以来的匮乏。
像喜宝——“抽屉只被移动一时,我已看见满满的一千元与五百元大钞……钞票与钻石又不一样。钻石是穿着皮裘礼服的女人。现钞是……裸女。”裸女自己的感觉是啥?藉住赤身露体而赢回来的诱惑性,沾沾自喜之余,不免也缺乏安全感吧。(七)
《喜宝》是一出大悲剧,男男女女锦衣玉食,但是将同名女主角计在内不下十数人,没有一个在该部小说之中善终——除非,遁迹空门或在精神病院的哺育之下尽把前尘抛却,也算求仁得仁。而,这一场情感浩劫,落在一位蒙难者的眼里,起因原来是“那次回家坐飞机我不该坐二等……我后悔得很,如果我坐头等,你(喜宝)便永远见不到我,这件事便永远不会发生”。
可见“穷,合该见鬼”,就是“佯装勒紧裤头”,又或者千金之女上演“微服出巡”,一样会严重出岔,飞来横祸。一九七八年人世未深的我,痛骂亦舒走火人魔,而此刻则十分十分懊恼:“明明是用香港人的语言来重写《浮士德》嘛,为何当日只有那些文字认我?我唔认字?”一切骂她物质主义的批评指摘,其实也是看弗懂。既然出生弹丸之地,自必要赚来一望无际的豪华大厅——对于贫脊与富足,香港人自备量度的一把尺,标准永远瞄住“安全感”。问题是,愈是大宅,愈不知道沙发与组合柜之外,空间要来何用?——独沽一味的唯恐无处安身,反而落得家徒四壁,心无宁日。
为“穷”,但从“要什么有什么”的角度下笔,而且作者的自我呼之欲出,而不像鲁迅先生般说教道学。我愿意相信她是当代香港文学佼佼,倪女士亦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