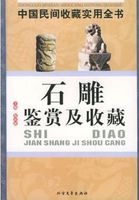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一)
郑裕玲的脸,也有过低调的时候。看过她在《花城》的演出,你才会明白何谓“一切都是历史了”。但是作为一部电影,《花城》的美,是属于美术指导的,银幕上女主角刺眼、养眼,功劳全归张叔平,甚至不是摄影师。时至今日,是那些发型、衣裙,又或唇膏眼影的颜色让我记住片中的郑裕玲,多过导演为她刻意经营的木独美。
你会说,推晚十年,同一角色,换了李嘉欣来演,岂非更佳?一来要美貌有美貌,要表情则属于“没有便是没有”,不像郑小姐般努力把精力克制,反而自然极了。如果没有《海上花》,上述当然只是个刻薄玩笑,但是侯孝贤的镜头下,的确印证了木美人的脸原来也可以有戏,或者,有些戏不一定要用眼睛鼻子来演。
而且,在众多的表演风格之中,女演员一直比男演员多了一个行当,或一点点的特权——为了不要破坏大众享受眼前的冰淇淋,她冷,是绝对合法的:像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像玛丽莎·白兰沁(Marisa Berenson),还有李嘉欣。纵然伊等也会(也曾)被人讥讽五官满分,演技零分,但是这些批评一样可以被人嗤之以鼻:阁下没有听过“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乎?
诚然,如果她的冷是不可能被解冻的话,大家就乐意把她遗忘。最近看《香港之星》,重睹尤敏的美,倒不是说她过时,却是由衷感觉到她身上铺着寒霜,如张爱玲所写:三十年前的月亮。
(二)
在某些事情上,我承认我是包拗颈,唱反调。你说尤敏美吗?我说:不,太完美了,太理所当然了,太像一幅人像画了——这都是看《香港之星》前的我;今天?眼界开了,口风自然不一样了。
在看这出名副其实地“眼睛吃大餐”的电影之前,脑海浮起一些以前不会想的事情——就算明明想过,也不容许自己承认。譬如说,我不是不知道尤敏很“美”,但是要我当众点一下头,认同几句,那便代表我屈服了,兼且不止向外来的势力弯腰低头,还要接受内心深处某一个被自己所瞧不起的“我”的胜利。
会是因为喜欢尤敏的那些“别人”吗?抑或应该归咎从他们的眼睛所放射出来的欲望?在某个年代,她是一卷月宫殿,而不知几多男生闭上眼睛,便会看见自己是一支毛笔蘸了墨汁,却久久不敢写下一笔一画。在类似的幻想之前,加上常常被拿来相提并论的叶枫和葛兰,尤敏自然更加“我见犹怜”——体形纤细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它是对强者的呼唤,而很少人会抗拒这份女性美德——也是“美”。
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女性美,如光环般戴在(别人所看见的)尤敏头上,我却视它为荆棘,连带冠下的弥赛亚都一并厌恶嫌隙。直至这次看《香港之星》,故事照旧围绕女主角不惜自我牺牲,为了成人之美。只是刹那之间,我看见在苦情和柔弱背后,一位深谙如何将“被看”细致把玩的女强人。
2000年4月27日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