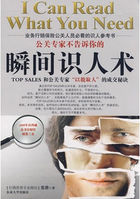作官的念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每人出生时下来都是赤条条的,无论教皇抑或影星。尊贵与矫饰都是后来的事情。
人生下来,第一件可做的事情只是放声大哭,这并非说他对作人产生了哪些顾虑,而是舍哭之外无由证明自己的生命。
在人的少年时代,则开始幻想如山的糖果,羽化成仙或与动物对话。总之,人随着社会的刺激和自己的需求产生了许多的欲望。
随着涉世渐深,欲望也渐多。
而实现自己的欲望,或尽快实现自己的欲望,是人们在有生之涯考虑最多的一件事情。
在这种思考中,需要一种优选,换言需要一种综合。
人因为衣食住行等各种需求的分门别类,欲望也跟着分门别类的。譬如千金之裘可御漫天风雪,满仓谷物就不怕明年的歉收。
于是有人单纯地积累财富,直到临死时仍拜托家人只可点燃一根灯草。这种人是吝啬鬼。有人徒然囤积粮食,甚至霉变。这种人叫土包财主。
然而聪明人诞生了,他们并不亲自制造或积累什么,只做一件事便足以丰衣足食。
如此妙事是什么呢?当官。
宋朝一个皇帝的胡言乱语流传至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云云。对读书人来说,这显然是谎言,不然饱读诗书的李杜、韩柳何以潦倒江湖呢?读书最多的教授和图书馆员们也从未因为读书而富起来。欺骗是一种诈术,然而骗人读书还算是一种比较光明正大的动机,虽然兑现不了。
此诗若改成“官中自有黄金屋”,庶几接近实际情况。当上一名公社书记,虽然未必在眼前矗起卜座黄金屋,但过日子总比普通社员要从容得多。
因为官所产生的权力又能产生一种优势效能,是对社会地位和生活资料的综合。
如果泛泛地论官,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好官与坏官,用百姓的话说是清官与赃官。这种好坏的标准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即对百姓的态度。
从政治学或行政学的观点看,官是群体组织的责任者,他手中握有的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职责。在形成网络的系统中,作为管理的中介或作为指令传达的枢纽,其职责必然受到来自各方的监督制约。那么,职责的完成在经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之后,只能得到称职与不称职的判断。既然如此,人们何以用好坏这种善恶标准来判断呢?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儒学观念笼罩的历史进程中,人,除了父母以外特别是离开父母成为独立的社会人以外,官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官的威望也与父母的恩情重合在一起,诸如“父母官”这种流传至今的叫法。在这种重压之下,庶民是无理可讲的,人生由生存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掌握在官们的喜怒哀乐之间。反抗多半是没有好下场的,那么人的全部渴望都只好寄托在当官者品格的善上。
在旧中国,官员最坏的品质莫过于贪,这如同女人最坏在淫一样。因为官员若贪,势必枉法,而草菅人命则是常事。贪者必欺君,必昧心,必鱼肉百姓。离财富最近的,不是商人,而是官员,不然何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对于一个贪官,他的能力与才干都很可怀疑,也可以说能力越强,越贪婪。这就揭示了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用能而用德来衡量官员优劣的谜底。
清代大儒戴远山诗云:
诗堪入画方称妙
官到能贫乃是清
清才能明、贪必至昧。在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之前,廉政必然是衡量官员的第一尺度。
面对官的威猛,既然不能取而代之,就只好努力作官。这不仅是综合物质财富的需要,也是人格尊严的延伸。
作官并不需要横溢的才华,这不是说可以昏昏噩噩,而要将才华之光掩于平易的外相之内。作官也无须力扛九鼎的臂力或发明电灯泡的智慧。既然叫官员就只做事务性的公干,具体事自有专门人才去操劳。
但官员要具备执行与决策两大本领,这是对上与下而言的。执行上峰指令须坚定不移,又依自家情形巧加变更,变更而不违上便是智慧。在决策时出语铿锵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契合,也是智慧。
当官还要善于协调和扬抑,这是对左右讲的。在同僚之间出众又不动声色,那么迎合上司的努力和联络同僚亲情的功夫就要一样付出,否则就被视为势力。要让部下竭尽全力,又不使彼等冒尖造成其他人的沮丧,这就要连打带拉,纵横捭阖,不费脑筋是不可以的。
与种田做工相比,做官充满了随机性,也可以称为风险。掌握别人命运者,命运又被别人所操纵。古来今往,因作官招致厄运者难以胜数,但人们对官场依然趋之若鹜,这也是一个人生的怪圈。
作一个好官并不容易,像作一名虔诚的朝圣者和殚尽心智的科学家一样需要献身精神。在封建社会,这样的官少而又少,因为做起来难而又难。海瑞的正直、包拯的公平、颜真卿的忠勇都未得善终。郑板桥、陶渊明以及阮籍一行人等,有心爱民,无力回天,只好用艺术化的姿态游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