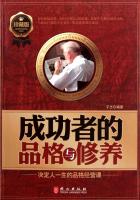天性诙谐的林语堂先生,曾对自己的道德文章拟了一副对联,曰“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宇宙文章”。冷眼一看,这话说得不够十分的谦逊。因为所谓谦逊这东西,不外是做到十里,说到五里,留个余地而已。但从林先生平生行状言之,他的确学贯中西,而且对东方与西洋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均能熟知。他当然也写过大量文章,不过那些文章是不是都属于“宇宙”这个范畴的,就在各自的出发点了。
然而除了林语堂外,深谙东西文化的人仍然不少。就现代说,称得上巨匠之誉的,还有泰戈尔。
虽然人们常称诗人泰戈尔,但他似乎已经从诗人的层面上升到圣贤的地位。所谓圣贤,不外是指某些人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心灵,与深邃的思想相融,与普通的民众相亲,与无限的大自然相合等等。
泰戈尔生于古老的印度,具体说是加尔各答。这一块神秘的土地饱浸从释迦牟尼以来的无数智者思想的熏陶,具有最纯粹的东方传统。他在《我的回忆》和《我的童年》这两本书中,写出他幼年即久久而静默地观察着色彩丰富的生活。他看到了什么呢?在蓊郁的阔叶树下,卖绿芒果和银手镯的人吟诵着悦耳的诗篇。
他的家庭属于名门望族,其父被百姓尊为“摩诃里都”(大圣人)。在这样的家庭中,他的默想得到了充分的伸展。
在他的少年时期,泰戈尔的父亲携他远游,最远到达喜马拉雅山。泰戈尔瞻仰了锡克教徒的圣殿——金庙。他还在旅途中感受了印度大地无限的深邃与单纯。在旅途中,他父亲向他讲解印度最古老又最具权威的两本书,《吠陀经》与《奥义书》,并学会了用梵文背诵。
这两本书的智慧是世人难以了解穷尽的,但无论对谁都具备开启心智的大用处。它们是佛的声音。
大自然开启了泰戈尔的眼界,佛法开启了他的心灵。或者还可以说,大自然和传统文化同时选中了他,因为佛陀也正是在大自然中觉悟的。后来,泰戈尔在长兄家暂住。他漂流在月色之下的恒河中,更加感悟出人与神之间说不尽的默契。在他二哥家,泰戈尔在西海岸面对浩翰的印度洋又汲取了无穷的灵感。18岁那年,泰戈尔远离故土,去英国的伦敦大学接触到了欧洲文明。在攻读诸如拉丁文等繁冗的功课中,他独独钟情于文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特别是莎士比亚的诗,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莎翁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主题:虽然没有胜利的希望,也已具备了拯救的力量,与泰戈尔的思想共鸣异常。
回到印度之后,他开始了诗歌、戏剧与小说的创作。在20岁至80岁这6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和《吉檀迦利》这些华美深刻的诗集,使他稳固地树立了世界级大师的地位。
在我们称他为诗人的时候,常觉得这称号有些单薄。他那源源不断的思绪又使人感受到一位思想家的丰厚。然而作为思想家的泰戈尔又不企图建立什么体系、申明与什么相对立、用什么作戒律。他身体力行替民众求自由、办教育的实践又使人认为他身上具备了许多神性。
在作家当中,这种现象是少见的。
一个人如果立志当作家,尔后经过努力成了作家,这情形并不少见。其道理同一个人立志当鞋匠终于当上了鞋匠无大的区别。可是,一个人发誓当大作家,而能够当上大作家的人都嗟乎少矣。因为大作家不止于是一个职业,更不止于是一种光辉的尊号。
他是人类灵魂的鼓手,这不是可以经过反复操练或选举而能成功的。
应该说,泰戈尔最初和最终关心的是宗教。这种关心是神与人的契合,是对生命的探索和赞美,是对民族自由和人性尊严的高扬,这是“立德”。而文学是泰戈尔无意之间的外相,这是“立言”。也可以说,文学是泰戈尔生命现象中有价值而不重要的现象之一。
泰戈尔生活的年代,恰恰处于印度为反抗英国殖民者而进行不断抗争的动荡岁月。国土广阔而民生忧患,美丽的大自然与到处可见的饥饿逼着泰戈尔从一开始就思考人类最本原的东西:生与死、自由与奴役、善与恶。
在战祸频仍的中国,一个关心宗教的人大多走向暴力,如设坛收徒,以方术奇巧聚啸起事。然而泰戈尔由宗教走向了诗歌,这是以爱为终极目标的思想活动。
青年泰戈尔最先接触的一个痛楚的问题是两极化:东方与西方,贫与富,高贵与卑贱,纷繁于单一。他认为西方的观念无非是将万物按着人的好恶列出喜欢与不喜欢的,而且“强行把它们拧下来”。
泰戈尔发现伟大常常见诸渺小、神性常见诸卑微之物,如草叶、花蕊、露珠甚至石头。在大自然中,他找到了神性和人格。
泰戈尔不遗余力地为印度各民族、各阶级的民众争取自由。他在圣亭尼克坦(和平之居)建立了一个孟加拉的教育中心,召集东西方的学者,教育无论贵贱的学生。
泰戈尔的诗歌是极富智慧又异常华美的。泰诗的整体倾向宁静而和谐、有学者说诗中所呈现的是“美学中的有神论”。在泰戈尔40岁的时候,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中的两人都不幸去世,自此之后,他成了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开始创作一种更富沉思性的诗歌,直至1941年(80周岁)去世。
他的作品最可一读的是《飞鸟集》,可谓千锤百炼,字字珠玑。
欧洲国家人士所推崇的泰诗是“吉檀迦利”,这部诗集由泰氏本人由孟加拉文译成英文,并在爱尔兰诗人叶芝等人的推荐下,荣膺19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本人是没有丝毫虚荣的。据他自己讲,把诗译成英文也毫无使人赏识的意思。因而当瑞典文学院的电报发来时,泰戈尔正在他创于孟加拉的一个山村学校中领着学生从森林归来。泰戈尔看过了电报,就漫不经心的塞进衣袋,没有任何感情上的波澜。
瑞典文学院对泰戈尔的得奖评语是这样写的:“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韵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这段评语写得极其拙劣,显出西方人的倨傲和对东方的无知。如果泰诗得奖是因为被译成英文和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这既有违于诺贝尔的本意,也是对泰戈尔的不恭。
泰戈尔并没有去领奖,虽然在几年之后,他曾到瑞典游历了一番。
泰戈尔最欣慰的是:在印度大陆的乡村,无论是赶车人、船夫和农夫都在吟诵着他的诗,但并不知作者是谁。
泰戈尔认为在有生之年成为“无名氏”自是极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