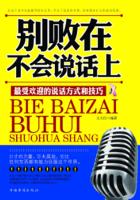应该说,歌曲的流行与不流行与内容无关。它既可以是严肃、悲壮的,也可以是轻浮甚至无聊的。
但流行歌曲最能反映时代精神,这一点是没有人怀疑的。
从社会学角度说,流行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覆被率高,即传唱的人数众多。另一个含义是不稳定性,即今天红极一时,明天可能无人问津。也是一种文化式快餐。
从音乐本身说,流行歌曲的词应该通俗上口,至少是容易被人理解的。当然,也应该反映人们的心声,包括希望、愤怒、迷惘或哀伤,也可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从旋律和节奏上说,应在音域、演唱技巧上适合大多数人唱,节奏明快。
这也是从形式上说的,并不牵涉内容。
从本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的走向来考察,其中既有严肃歌曲,也有无聊之作。
20年代在上海传唱的流行歌曲可以用黎锦晖的作品为代表,格调不能说是多么高昂的,也不全都是靡靡之音。我们可以想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十里洋场,这些歌唱出了一些哀怨、一些凄婉,可以听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式微之时的无奈。黎先生的有些作品,如《可怜的秋香》,也可达到上乘水准。与此同时,赵元任、黄自等先生的歌曲创作,不仅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开辟了先河,也为流行歌曲注入了活力。因为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音乐除了宫廷音乐以及民间小调和戏曲之外,并没有产生可以跟西方相比肩的音乐,无论从音乐理论、乐器(包括乐队)、记谱系统和曲式等各方面来进行比较。
中国音乐的腾飞时期是和聂耳、冼星海与吕骥等人的名字分不开的。而他们的作品多数又恰恰是以流行歌曲的方式使其创作达到全盛的高度。这些作品的名字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及贺绿汀先生的《游击歌曲》。《黄河大合唱》虽然具有声乐套曲的形式,但还是以流行歌曲的方式驰名于世。
这些歌曲是流行的,还因为唯其流行才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其主题只有四字:国难家仇。如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虽然是一首技巧相对复杂的独唱歌曲,也仍然藉着一种特殊的背景而闻名现代音乐史。这个时期的歌曲令人想起南宋的诗词,为了保家卫国而肝胆俱裂。当时在所有文艺形式中,最能反映众人心声也最能感染众人的,唯有歌曲。可以说这是仅次于刺刀的一种武器。
如果歌曲不是流行的,换言之,不是大众化的,就没有这种作用。
当时以《延安颂》、《解放区的天》为代表的作品,则反映出解放区军民愉悦的心态。作为历史而言,这种心态的留存和展观是其它方式如影视、小说诗歌的表现所不能比拟的。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流行歌曲的另一特点是:它是不拘于物质设备、人的文化程度、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文化形态。
它既是自娱方式,又是娱人方式。自娱可以满足自己,娱人可以进行传播。
建国以来,从周巍峙的《志愿军战歌》到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出新中国初创时期如日中升的气象,衬出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其中即使是政治(和政策)意念最强的如《社会主义好》(李焕之)、《歌唱祖国》(王莘)也是感情充沛、毫无虚饰的,是人们心声的自然流露。这时期的流行歌曲除了豪迈一派,亦有婉约之风,如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生茂的《马儿啊,你慢点走》、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等。还有谐趣风格的如《逛新城》(才生)、《新货郎》(郭颂)等等。
从建国到“文革”之间的17年,应该说是本世纪以来歌曲创作和传唱流行的第二个高潮阶段,即比当年抗战救亡时群起歌咏更加广泛和深入,当然与现时比起来(特别是传播手段)还显得单薄。这一时期流行歌曲的成功在于群众的心境与时代的走向相合,歌曲创作的主导旋律明朗又能够兼容不同风格,艺术上比较宽容。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当时国门未开,西方世界的音乐思潮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进入大众歌咏领域。对于创作者和欣赏者来说,当时的流行歌曲没有也不必要有来自港台、日本和欧美的参照系。换句话说,选择的范围只在国内歌曲作家各个流派和各种风格中进行,这情形如同抵制洋货和扶植民族工业一样,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最后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流行歌曲的创作和传播基本上没有商业性和工业性因素介入,即没有唱片、磁带和商业性演唱会的支撑,后者是现代流行歌曲的支柱,也是流行歌曲命运的真正操纵者。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中国的事情总是阴阳相生、正奇相辅的。如同绘画中大写意的泼墨和工笔画的纤巧相映,哲学中儒家的秩序和道家的超然相补,诗词中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和柳永的晓风残月相谐一样,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也以其豪迈和抒情的两翼向前发展。更准确地说,当时的抒情歌曲是作为豪迈歌曲的补充而存在的,是一种主仆关系。有趣的在于,前者的内容全是政治的,有些词就是完整的标语和政策条文,后者的内容是涉及爱情、自然风光和生活情趣的;前者多是进行曲式,后者多是舞曲曲式;前者旋律采用汉族音乐素材并吸收了西洋特点,后者多是少数民族民歌的翻版。还可以这样说,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和部分俄苏歌曲成了当时抒情性歌曲的主力军。如通福的《敖包相会》、田歌的《草原之夜》、洛宾的《亚克西》、郭颂的《乌苏里船歌》、苏联的索洛维耶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勃兰切尔的《喀秋莎》等等。
利用异国或异族的音乐来抒发本民族之情,这是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时下流行音乐中鱼龙混杂但仍然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其原因一是中国音乐并没有发育出西方音乐中富有理性秩序的丰富体系,如以三个三度音迭置的和弦构成的全音程、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低音伴奏、交响乐曲式和记谱系统。这是由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两朝闭门锁国形成的畸变。其二是以往的音乐素材多是可怜的宫廷舞乐和繁复的戏曲音乐,而真正可以成为流行音乐基础的民歌对汉民族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但这也显示了汉民族善于吸取异质文化营养的特点,唐代音乐的兴盛恰恰是胡人音乐一进入之后而形成的。
在“文革”10年当中,流行歌曲仍然存在,只是以毛泽东语录诗词歌曲、样板戏和少量高度政治化的创作歌曲为主。这是“文革”前期、中期和后期流行歌曲的走向。
如同中国人的善于生存一样,当时八亿人民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对于流行歌曲的渴求竟由样板戏唱段来释放了。用单一类型的戏曲(京剧)唱腔来充塞全民族的音乐生活,恐怕这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观。
样板戏作为京剧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尝试,其内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相合,艺术也是完美的。它造成的失误一在文艺政策只把它当成独生子,翦除旁类;二在其创作方法有失偏颇,只允许突出正面人物。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当时创作歌曲水准的低劣,人们转而唱样板戏来抒情,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正反角色的唱段,可供人们在各种情境下抒发心音。其中音乐较好的当属《杜鹃山》。
知识青年是当时流行歌曲的主要需求者。这个庞大的群落又以地下和秘密的方式传唱着五六十年的流行歌曲,尤其是爱情歌曲,当时被称为黄歌。这也说明流行歌曲的生命力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
从打倒“四人帮”至今日的15年中,流行歌曲可以说越来越流行,但很难划分什么时期了,因为它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
在刚刚打倒“四人帮”时,人们对流行歌曲的需求形成真空,旧歌已经无法代表时代,新歌尚未诞生。陕北民歌《绣金匾》等歌曲以旧翻新,一度流行。真正反映人们喜悦的是施光南的《祝酒歌》。
这使我们感到,流行歌曲不仅反映时代精神,甚至代表着时代,它如同一个个刻度记录着每一历史时期的前进速度。
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流行歌曲呈现了群体的繁荣。这时期的歌曲几乎都是温柔软性的,反映出入们走出严酷的冬天后对阳光绿叶的渴求与享受。作品大多明朗单纯,虽然也有大量的爱情内容,也是在五六十年代歌词上的进一步甜蜜化,糖份更多了,但还没有其它成份,如苦辣酸。作品有刘诗召《军港之夜》、施光南《在希望的田野上》、王立平《太阳岛上》,金凤浩《美丽的心灵》,王酩《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批歌曲开始,中国产生了一批批歌星,而以往的歌曲培养的只是歌唱家。
一首优美的歌曲《乡恋》(张丕基)开始用先锋的手法对流行歌曲演唱领域进行了探索,这几乎是一个信号,表明作为流行歌曲欣赏者的几亿青少年需要更丰富的音乐食粮。
接着,邓丽君的歌曲登陆,这如诺曼底登陆一样,成为文化和政治大事。当时大陆与港台已隔绝了30年,社会制度截然相反,但文化背景又绝对相同。所以人们毫无抵抗地臣服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
人们平时使用的含不雅之意的“流行歌曲”这个概念也由此诞生。
正如赝品比真品更先占领市场一样,在港台歌曲中先是香港歌曲进入大陆,虽然它比台湾歌曲的艺术水准、文化内蕴要浅薄得多。
邓丽君本人是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在中国大地是如何享有大名的,时代使然。她的歌曲如同日本影片《追捕》中之杜丘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瓦尔特的走红一样,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抗拒的显扬。人们在久渴之后,还对什么牌号的饮料以及井水、泉水有什么挑剔吗?朱元璋当年在饿昏之时,也曾将乞丐送他的只有几片青菜和豆腐的残汤钦命为“珍珠翡翠白玉汤”,终生难以忘怀。
这些香港歌曲对大陆听众来说唯一的价值是新鲜的感受,人们享受到了较好的配器手法和高质量的磁带录制技术。如同新鲜的不一定是好的一样,这些歌大多由日本作曲家创作,和30年代上海滩的格调一致。邓丽君唱的歌也可说是千篇一律,唱爱情并无真爱情,唱哀伤也无真哀伤。但这和邓丽君本人无关,不可用歌唱家来衡量她,她只是商业歌手。
这一时期对中国歌曲界来说,除了培养歌星,又诞生了流行歌曲生存的另一支柱:录音磁带。磁带的意义在于:只有工业支撑的艺术才具有市场价值以及商业价值。
至此,中国的流行歌曲步入了与外国同步的阶段:发行盒式录音带来实行歌星制度。当工业和艺术相结合后,流行歌曲的势头已经无法遏止了。
此时,东瀛的日本毫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其作用对流行歌曲的生存有如基石,他们的动作是向中国大量进口录音机。
录音机、磁带和歌星直至今天都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存在基础。这一作法向人们显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进口录音机如电击一般强烈刺激起国内的录音机企业,几经振兴,录音机在中国人的家庭文化消费中已占有一席之地。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录音机产量已达到2935万台。而有了录音机,就必须有大量的录音带相随。
所以说,流行歌曲的基础是工业,而不是文化本身。
在香港歌曲之后是台湾歌曲的进入,但香港歌曲并未退向后台,这是中国流行歌曲多元化的开始。台湾的校园歌曲是大陆中国人第一次听到的台岛歌声,以叶佳修的作品为主。如《外婆的澎湖湾》等等。后者的风格清新而亲切,反映出普通人的心迹,这对国内音乐界长期无法摆脱的虚饰之风自然是一种冲击。
香港歌曲的软性和台湾校园歌曲的清新相结合,似乎给国内作曲家以新的启示。他们在面对港台歌曲束手无策之余,振作精神创作了又一批流行歌曲。如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和《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等。
对中国流行歌曲真正起到爆炸性意义的事情是崔健《-无所有》的产生,它使歌曲彻底地皈依了真实,是首次由作词作曲者唱出真话的作品,又将中国流行歌曲引入了摇滚化阶段。
对流行歌曲采取不屑以至轻蔑姿态的不是听众,而是音乐界的某些权感人士。他们的动机在于一种使全民族音乐素养得以提升的义无返顾的责任心,但他们只从纯音乐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就难免过于焦虑了。
毫无疑问,流行歌曲在包括歌剧艺术、交响乐在内的音乐体系中显然处于最低档次。无论是内涵还是技巧都是如此。但流行歌曲存在的前提如下:
人们是需要歌曲来唱的。这些歌应该人人能唱,必须能够流行,否则人们无从唱起。
同时中国音乐界对流行歌曲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概念上的误区,比如将流行硬与严肃相对,流行只指大众化和短时期,与严肃和轻松无关。
另外音协的官员们又忽视了另外一个区别,即角色的置换。某些高级的声乐作品只能在音乐厅中欣赏。听众无法介入其中。而流行音乐则将欣赏者和演唱者融为一体,既可以听又能够唱。
比如本世纪被称为“黄金小号”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莫纳科(Monaco)和希腊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Callas)的演唱是全球最优美的歌声,但只能被欣赏,而不能流行。
从事所谓“严肃音乐”的音乐家似乎不必痛心疾首于大众音乐素质的堕落,最好的办法是扩大严肃音乐的阵地使之与流行歌曲共存。如果强行用燕窝鱼翅的营养来说服别人放弃青菜萝卜是一件徒劳的事。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卡鲁索(Caruso)、夏里亚平(Chaliapin)、多明戈(Domingo)和帕瓦罗蒂(Pavarotti)都为自己国家的声乐艺术赢得了荣誉。中国人理应有志气在这个领域争得一席位置,这比争夺流行歌曲的听众更有意义。
中国的流行歌曲进入了摇滚化的阶段后,使大量民歌素材进入了常规领域。徐沛东作为近年最“劲”的作曲家,就显示了这一优势。这不仅仅出于他的才华,还有时代所提供的工业基础、消费能力和传播手段。
对流行歌曲来说,在什么时候露面是至关重要的。当今中国人对流行歌曲的相识大多在电视当中,而中国的人均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这是歌星和作曲家最好的温床。作为第二传播手段的录音磁带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关资料表明,1988年全国发行了1亿2百万盒歌曲原声带,如果加上翻录的数字,便超过了2亿盒。又有资料表明,中国人听歌曲的磁带有75%是复制带,也就是说复制带与原声带的比例是4:1.在这样强大的磁带市场上,流行歌曲的存在的确是难以回避的。
现在流行歌曲的状况是港台与国内歌星并耀、洋味和土气并存。繁荣已经完全做到了,但引导和提高却远远不足。如今官方对流行歌曲的走向完全失控,只能查禁黄色与反动内容的作品,对其他只好听从市场摆布了。
从现今流行歌曲的情调看,几乎同时反映着现代人的迷惘、苦涩、甜蜜、忧伤、激动和希望。这也是一种时代情绪,反映出中国制订对外开放政策之后,经济跨入开足马力时期的种种回顾与展望。
不管怎样说,人们几乎天天要唱歌,那么永远要有一些歌曲在流行着。这正如威尔逊所说:“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