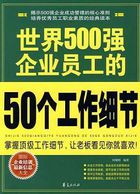1969年春节,天寒地冻,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学生来给教师拜年,教职工之间也很少往来。
春节刚过,宁大和附中的部分教职工被派出去搞“外调”(即到外地去调查被批斗对象的家庭出身、本人历史及其“罪行”)。部分教职工参加整党建党工作。
搞“外调”的教职工很辛苦,对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他们千里迢迢,取回各种证据。校领导对审核工作抓得很紧,也较实事求是。不久,被批斗的对象陆陆续续地被解除了群专。
家麟解除群专以后,被安排在政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他“本性难移”,一有空闲就继续研究他的逻辑学。
暑假期间,有一天,不知是谁从何处弄来一张《宫廷生育秘算表》。表中写明妇女生育的年龄,怀孕时间的推算方法。据说,只要按表中推算出来的时间去怀孕,想生男就能生男,想生女就能生女。开始我不太相信,后来听说某校教师就按此方法怀孕,结果如愿以偿。我有点动心了。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11月,林彪下达了“第一号令”,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备战,要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疏散到农村去。家麟不在疏散之列,允许回家。附中学生和教职工提前放假,什么时候复课,等候通知。
闲来无事,引起我再生个孩子的欲望。眼下我们只有一个男孩,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再生一个男孩为好。现在生孩子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有《宫廷生育秘算表》,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男孩。第二,闲居在家,怀孕和生产时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休息。第三,目前我们两人的工资收入,再生一个孩子可以养得起。当年生养一个孩子成本低,生孩子住院费用可以报销,孩子上学免交学费,定量供应的粮油和凭票供应的副食品都很便宜。第四,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大了,女儿10岁,已上小学;儿子6岁,明年就可以上小学了。再要一个小的,不会太累人。
1970年9月13日凌晨5点左右,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市医院诞生了。虽然没有如愿以偿,生了个女儿,但我还是很高兴的。高兴之一,顺产,母女平安;高兴之二,我们家添丁进口了,而且是一个哭声响亮,体重6.7斤的健康的小姑娘;高兴之三,作为母亲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生男高兴,生女也乐,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亲骨肉。
旭日东升,红光万道,7点左右,家麟就领着两个孩子,提着早餐和点心来医院看望我们。
家麟一进病房,放下早餐和点心就乐呵呵地问我:“生了?”我点点头。两个孩子飞快地跑了过来,站在我的床头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家麟看我很平静,可能已猜着三分,他没有问生男生女,只问:“还好吗?”
“《宫廷生育秘算表》不灵验,生了个女儿。”我抢先告诉他。
“我赢了!我赢了!”秋秋连蹦带跳地喊着。冬冬不服输地瞪着她。
“小声点,这是病房。”我让大女儿别大声喊,小声问她怎么回事。
“来医院前,我和冬冬用苹果打赌。我说‘妈妈肯定生个妹妹’,冬冬说‘不,肯定是弟弟’。看,我赢了吧,家里的苹果归我了。”她高兴地叙说着。
“你为什么说‘肯定是弟弟’?”我摸着冬冬的头问他。
“因为我喜欢弟弟。”冬冬把头一歪,撅着小嘴说。
“你为什么只喜欢弟弟,不喜欢妹妹?”我想了解小儿子的想法。
“弟弟可以当我的小兵,跟我一起玩打仗,还可以一起溜冰车。”冬冬坦率地说着。
“那妹妹也可以和你一起玩打仗、溜冰车呀!”我想扭转冬冬的看法。
“不行。妹妹娇气,一摔倒,就知道哭。”冬冬很认真地说着。
“要是这个妹妹很勇敢,不娇气呢?”我想让冬冬喜欢这个妹妹。
“那我就喜欢这个妹妹。”冬冬初步接受了这个妹妹。
我问秋秋:“为什么说肯定是妹妹?”
秋秋回答说:“因为我喜欢妹妹。妹妹乖、听话、不捣乱,可以和我一起玩,一起上学。”真有意思,小小年纪想法各异。
我问家麟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家麟面带微笑地说:“生男生女都是喜,母婴平安是最大的喜。”
“既然是喜,那你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我刚说完这句话,两个孩子飞快地跑到家麟身边,想知道爸爸将要给妹妹取个什么名字。
家麟想了想,拉着秋秋的手,对着她说:“那就从你的名字中偷一个‘红’字。”又用另一只手摸着冬冬的头,对着他说:“再从你的名字中劫一个‘向’字。”而后对着我说:“合起来,就叫吴向红吧!”两个孩子听了以后笑逐颜开。
“那就叫这个名字吧!”我是这样想的:向红,就是向着红太阳,向着红色政权,这个名字符合革命的要求,也是我当年参军的初衷,而且今后再不会因孩子的取名遭指责了。再说,这样的取名方法富含寓意。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画面,那就是,姐姐吴耀红站一边,哥哥吴向东站一边,妹妹吴向红站中间,姐哥各伸一只手拉着妹妹。意即姐姐和哥哥要多爱护妹妹,帮助妹妹;长大以后,3个人要相扶相帮,携手前进。
小女儿在育婴室,现在他们是看不上了。家麟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坐了一会儿,家麟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家麟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到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上了户口,吴向红就是公民了,可以买到供应的粮油和副食品等。下午,家麟把我们母女二人接回家中。
两个孩子听说妹妹回家了,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床跟前来看妹妹,他们从未见过刚出生两天的婴儿,可能觉得很稀奇,看得很专注,看得很入神。
我说:“你们仔细看看,妹妹长得像谁?”
“像我。”秋秋自信地喊着。小儿子看看妹妹,再看看姐姐,默不做声。
我问秋秋:“你说妹妹长得像你,哪些地方像你?”
秋秋又仔细看了看妹妹,说:“额头、鼻子、嘴、脸蛋都像我。”
秋秋说的没错,我看小女儿的眼线比大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线长,我想,将来她的眼睛会比姐姐的大。
冬冬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长相,他很少照镜子,可能连自己的眼睛、鼻子、嘴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冬冬经常在外面玩得灰头土脸的,回家以后你不叫他去洗脸,他不会主动去洗。他对妹妹长得像谁的问题不感兴趣。冬冬站在床边,一会儿摸摸妹妹的头发,一会儿拉拉妹妹的手。他可能以此表示对妹妹的友好,也可能出于好奇;刚出生的小娃娃竟然也有头发,胳膊这么短,手那么小……
小女儿很乖,能吃能睡,很喜欢笑,有时候在睡梦中还笑。她笑起来甜甜的,特别可爱。不管是有意识地笑,还是无意识地笑,笑总比哭好。我们希望她的笑能给我们带来好运,能给全家带来幸福、平安,能给她自己的一生带来灿烂。
当年,学校正常上课。我休满产假,就把小女儿红红日托在宁大一位老师家里,他家与附中家属院毗邻,这样,早晚送接和中间喂奶都很方便。小女儿满一周岁了,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断奶之后,我把她送到我的一个学生家长那里去全托。这家人姓张,住地质队家属院,离附中不太远。张大爷是地质队工人,张大妈是家庭妇女,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这家人对红红非常宠爱,把她喂得白白胖胖,壮壮实实的,因而红红还得了一个外号,叫“胖牛”。
红红满3岁,为使她接受学前教育,我就把她送到宁大幼儿园去了。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学习唱歌、跳舞、画画、识字。但宁大幼儿园只有日托,没有全托,家长需要每天接送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再辛苦也心甘。
红红入幼儿园不久,哥哥就送给她一把木头做的小手枪。假日里,她经常拿着这把小手枪跟在哥哥后面玩打仗。有时候跌到了,哭了,哥哥一声令下“革命战士不许哭”。她立刻不哭了。她还喜欢跟哥哥在树林里捉蜻蜓,在水塘边抓小鱼。冬天,她还喜欢跟哥哥一起玩溜冰车。她有点男孩子性格,喜欢跟男孩子在野外玩,不大喜欢猫在家里玩“过家家”。
1976年春,家麟被派往贺兰县参加农村工作队。不久,学校又派我和另一教师带领学生去贺兰县电机厂学工两个月。当时,革命工作第一位,各家的困难自己去克服。我只好把家交给大女儿,让她一边上学,一边管好家,带好弟弟。我把红红带到贺兰电机厂。上班前,我把她托在贺兰县幼儿园,下班再接回来。红红聪明伶俐,在幼儿园里,很快就学会了画向日葵、麦穗、镰刀和斧头。在电机厂里,因为她天真、活泼、能说会道,很受学生和工人喜爱。
1976年夏,宁大政史系组织工农兵学员去延安革命圣地办学。派家麟跟随学生去延安,负责学生的伙食管理工作。家麟平易近人,与学生相处得很融洽。有一天,家麟去逛百货大楼,在玩具柜那里见到一个穿朝鲜服装,扎个长辫子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不仅漂亮,还会眨眼睛。这在当年算是高档玩具了。家麟一向很节省,这次却慷慨解囊,给宝贝女儿红红买下来。家麟从未给大女儿和小儿子买过像样的玩具,这次给小女儿买这个玩具,算是破例。都说父母疼幼子,的确如此。
红红对爸爸送的这个洋娃娃爱不释手,有时还会抱着洋娃娃跟哥哥去玩打仗。她对这个洋娃娃很珍惜,上大学了,这个洋娃娃还摆放在她房间的书桌旁。
有朋友对我说:“目前,我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要什么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黑崽子(被专政对象的孩子),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家麟来宁夏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家麟来宁夏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家麟是个乐天派,他常对我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奉公守法,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总有一天会被社会认可的。”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家庭的纽带和欢乐,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为什么不要孩子呢?再说,孩子的未来长着呢!谁能预测?古人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将来不一定就不是阳光灿烂。